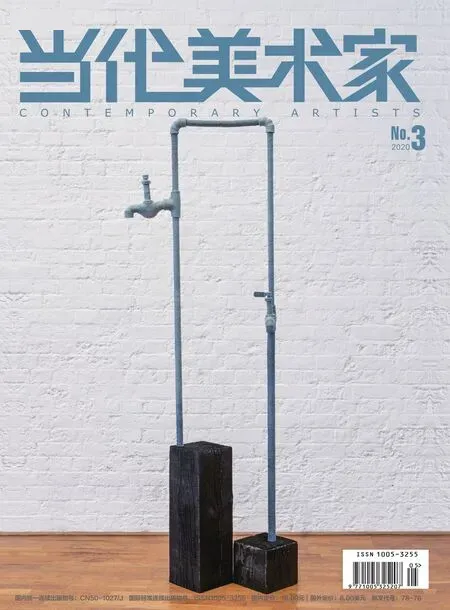“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糾纏:中國當代藝術十年動向
吳永強 Wu Yongqiang
過去十年,是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也是中國當代藝術在歷經市場化洗禮后分合重組的十年。在這十年中,全球化不再是一個修辭性語境,而是中國社會近距離接觸的現實。中國當代藝術也越來越深地卷入了全球當代藝術運作體系。在國內,雙年展、三年展模式愈益成熟,新的國際性展事接連涌現;在國外,中國策展人、藝術家以集體或個人的形式主動出征,力求發出自己的聲音。一邊是國際交流越來越頻繁,一邊是身份意識越來越濃厚。雖然同時藝術家的個體訴求持續擴張,創作觀念、媒材與語言繽紛多變,可是在眾聲喧嘩之中,仍然顯示出一些集體性動向。本文擬以“全球在地化”的視角,對這些動向作出把握。
一、碎片化與“后歷史”景觀
2016年4月,雅昌藝術網開設專題,通過訪談和組織專稿的形式,就2005—2015年中國當代藝術十年之變發表觀感。其起點選擇在2005年,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從這一年起,中國當代藝術品開始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創造記錄。從此,過去先后在英雄主義、犬儒主義等精神護身符下生存和繁衍的中國當代藝術,開始接受資本洗禮,與藝術市場發生了緊密的聯系。故這一年也被視作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元年”,它代表了一種轉變,標志著中國當代藝術走向了一種世俗化歷程,雖然其間因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而經歷了顛簸。2015年,雅昌藝術網所組織的專稿著重從拍賣市場、美術館、畫廊等外圍環境著眼,談到了過去十年里中國當代藝術與之俱變的狀態。當時,策展人、批評家何桂彥在訪談中指出:“中國當代藝術在2005年至2015年間進入高速市場化、資本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時期。”1如今,時間又過去了五年,再次回眸,我們認為,何桂彥答話中提到的幾個關鍵詞——市場化、資本化、去政治化——仍未失效,依然可以概括中國當代藝術從那時到今天的基本發展態勢。
照何桂彥看來,盡管受制于市場化、資本化的游戲,但是,中國當代藝術在創作上——尤其是在年輕一代藝術家那里——仍然呈現了新的變化,表現為:“自覺地遠離宏大敘事,開始向微觀化、破碎化、多元化發展。”2盡管這并非與創作者應對市場的策略完全無關,但何桂彥認為,就年輕一代藝術家而言,這更多地“與他們的知識結構、生存體驗,以及今天多元文化的價值取向有關系”3,因而仍可說是一種內生性變化,故此,何桂彥認為在其中可以找到“美術史的敘事”邏輯。何桂彥斷言:“像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那種線性的、二元對立的發展方式已經結束了。”4在最近五年,這個說法也繼續得到印證,因為青年藝術家們的創作的確難以通過聚焦宏大敘事和單一主角來加以線性地把握了,他們越來越以多元的創作主體,圍繞多樣性訴求,以發散的形式延展其存在方位。其結果是時間性的壓縮和空間性的擴張。雖然我們不敢妄言歷史終結,但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當代藝術史確實正在經歷一場“空間轉向”,空間性以壓倒優勢占據了其歷史維度。
如果說這種情況注定帶來困惑,不過,其困惑卻不會留給中國當代藝術本身,而只會留給書寫當代藝術史的人。這又恰恰表明,中國當代藝術所夢寐以求的“與國際接軌”似乎漸漸成真了。因為從世界范圍看,當代藝術本來就面臨著“歷史終結了嗎”的逼問。形勢正像漢斯·貝爾廷和安德列·貝登辛格所共同描述的那樣:“當代,而不是現代,已經變成風靡國際市場的一個詞語,因為它描繪了一種沒有邊界也沒有歷史的藝術。”5照他們看來,在當代藝術語境下,過去以西方藝術為主導的“世界藝術”(The World Art)版圖已經讓位于“全球藝術”(The Global Art)新地理。在這個錯綜復雜的全新人文地理版圖上,文化與文化、個體與個體之間不再以等級制構成關系,而是多元平等、異質并行和眾聲喧嘩。再沒有什么勢力可以占據時代的中心起主導作用,也再沒有什么東西是絕對新的。因此,企圖依靠幾個中心人物、代表性案例以及按照新舊之別來把握的藝術史敘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歷史讓位于地理,藝術進入了后歷史時代。
二、出征國際與身份焦慮
如果問:中國當代藝術與國際接軌只是靠了這種凌亂的“后歷史”狀態嗎?那么,我們怎么從全球藝術的背景色中區別出它的顏色呢?也許有人會說,既然都已經是全球藝術了,還有提這個問題的必要嗎?可是,假如世界各國各地的藝術都沒了特色,全球藝術豈不成了一鍋漿糊?當代藝術所主張的多元文化價值觀也未免自相矛盾了。過去,在“世界藝術”框架下,人們熟知一句話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話聽上去沒錯,但可惜它不過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辯護詞。因為所謂“民族的”,針對的只是第三世界民族,這實質上是要求他們留守在過去的傳統中靜止不動,而讓西方藝術獨步發展,并為西方人留下一塊欣賞異國風情的保留地。而全球藝術則意味著世界各民族、各地域藝術同步發展,共創異景。但是,困惑照樣留給了第三世界。因為當代藝術是西方藝術史邏輯演繹的結果,對西方世界來說是原生的,而對第三世界來說卻是舶來的。西方當代藝術早就發展了一套觀念,制定了一套規則,形成了一套手法,剩給第三世界的就是“玩不玩”的問題了。不玩是不可能的;要玩,則必須接受那一套觀念,適應那一套規則,運用那一套手法。此外別無選擇。
這就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原始處境。它將新舊和中西兩個問題糾結在一起,如難以擺脫的遺產從近現代藝術的背上一路傳遞到當代藝術這里。如果說過去我們還能借助與外部世界的距離感而鈍化其銳度,可在身處全球化語境的今日,卻是無法繞道而行了。
中國當代藝術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歷程而產生發展的,其間經歷了一個模仿和學習西方現當代藝術的過程。正如中國社會各領域一樣,這是一個必然出現而值得理解的歷史過程,它反映的是一個經歷過長期封閉的社會所涌起的現代化焦慮。可是,隨著中國日益融入世界,中國當代藝術也開始以各種形式登上國際舞臺之時,另一種焦慮便顯現起來,那就是文化身份的焦慮。這個焦慮關乎價值判斷,但其本身卻不是價值判斷的產物,而是一個經驗事實,一個所有后發國家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都不得不與其照面的文化心理事實,而尤以今日全球化時代為甚。但西方文化卻不必有此焦慮,因為盡管其內部也存在若干差異,但作為曾經的殖民文化,它卻是一個整體——過去它們是“世界藝術”的代言人,今天它們又是當代藝術的策源地——結果,文化身份的焦慮最后統統留給了第三世界。對后者而言,這是迫不得已的處境,但也成為其當代藝術生成獨立個性的條件之一。
我認為,要在五光十色的中國當代藝術現象中,辨出其十年來的發展調性,就必須了解其主要的問題意識。過去十年已經是中國當代藝術連續發展進程的第四個十年了。它在整體上更深地卷入了全球化旋渦。從展覽部分來看,不僅雙年展(包括三年展)在全國遍地開花,而且國內藝術界開始主動請纓,奔赴國際大展了。其中尤以集體組團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最為典型。2011年,當威尼斯雙年展創設平行展剛剛進入第三個年頭,國內當代藝術界便大軍壓境了,“據批評家王林透露,近5000位中國藝術家(團體、機構)在2011年投遞了申請。”6而由王林本人策劃的“碎裂的文化=今天的人?”便在這一屆雙年展上如愿現身。同時,由北京今日美術館、臺北最銘文化教育基金會、臺灣美術館聯合參與的“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也獲得了辦展的通行證。又熬了兩年,中國當代藝術界與國際接軌的愿望和以大兵團作戰的能量終于在隨后兩屆威尼斯雙年展上集中爆發了,并形成前后兩波浪潮,令平行展的發包方悲喜交集。2013年,蜂擁而至的中國軍團以“未曾呈現的聲音”“重探”“放大”“處境”“對望”“文化·精神·生成”“心跳”等一連串主題展,占據了當年平行展四分之一的體量。其中,由王林擔任總策展人、羅一平擔任中方策展人、格羅麗婭擔任意大利方策展人的“中國獨立藝術展:未曾呈現的聲音”,更是以匯聚150多位藝術家作品的陣容創下記錄。2015年,中國軍團興猶未盡,一口氣舉辦和介入了“山水社會——測繪未來”“氣韻非師”“尋常物的復仇(The Revenge of the Common Place)”(宋冬參展)、“一光年特別邀請展——中國繪畫劇場”以及“因地制宜”(劉小東個展)、“賈藹力”(賈藹力個展)、“‘通向地獄之路’:江衡個展”等9個群展和個展,再一次把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變成了中國人的盛會。不僅如此,在這兩屆展覽上,中國當代藝術家還陸續入駐肯尼亞、圣馬力諾和伊拉克的國家館,一時間喧賓奪主,傳為奇談。
這種現象說明,中國當代藝術盡管在創作上顯現出“微觀化、破碎化、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但在精神狀態上,仍按捺不住搞群眾運動的沖動。這是有傳統的,“85新潮”就根本上就是一場群眾運動。進入20世紀90年代,運動之勢漸趨沉寂,那是因為條件改變了,席卷全國的商業大潮分散了藝術界的精力。不過,到2005年后,當聽說中國當代藝術品在拍賣市場上創下了佳績,一場畫家回流運動又應聲而起,以至于畫家村、藝術區人滿為患,相當擁擠。這是其一,可不必再說下去。其二,這種現象反映出,中國當代藝術委實有一種尋求國際承認的強烈愿望,他們希望在一個代表“全球化”的集會儀式上亮出自己的面容,發出自己的聲音。其實,光是讀一讀部分展覽的取名,我們就能夠直覺到一種心結所在了——“未來通行證——從亞洲到全球”“未曾呈現的聲音”“對望”“山水社會——測繪未來”“氣韻非師”“中國繪畫劇場”“記憶與當代”(2017)、“中國·意境”(2019)——它們刻意地強調著自己的中國或亞洲身份,以便能夠在一個象征西方當代藝術權力場的時空環境中確證自己的主體性在場。換句話說,它們急切地表達了對自己文化身份的焦慮。
三、“再中國化”與“在地化”
這種焦慮是伴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和國內當代藝術在國際上知名度的增長而逐漸沉重起來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關切的問題是突破國內封閉,所以一心一意向西方學習,還談不上什么文化焦慮;如今,它卻充滿了這樣的焦慮,十分在意自己在國際舞臺上是否能以一個平等的主體被對待,所以,它一方面緊跟全球化步伐,一方面又希望與西方當代藝術拉開距離。這樣,一種“全球在地化”的心理氛圍就形成了。
20世紀80年代,日本商界率先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做“土著化”(Dochakuka),用來指代一種新的經濟運行法則和貿易營銷手段,意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或一個地區因應其屬地文化,對國際經濟或商品流動實行本土化改造,并能成功地將本土產品輸出到全球。受此啟發,1992年,英國社會學家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提出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一說,他認為,方此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地文化與全球文化之間,實為一個“相反相成和互動發展的過程”7,一邊是“全球化”(Globalnation),一邊是“在地化”(Localization),兩者同時發生。用美國社會學家瑞澤爾(Ritzer G.)的話來說,即為“全球和地方之間相互滲透,在不同地區產生不同的結果。”8或者,“更為抽象地說就是——普遍性與具體性的同時存在和相互滲透。”9它致力于“全球與本地融合”(Meld global inside local);它向陷身于全球化的人們發出了一個倡議:“全球思考,本地行動!”(Think global, act local)
可是,“全球在地化”之“地”卻有大有小,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文化圈,小到一個村社、一條街道、一棟房屋。故就“在地化”的行動而言,亦必有層次之別,主要看處在何種語境,出于什么考量。對于中國當代藝術來說,人們首先在意的是一個宏大的“中國”概念,并經常是更抽象化的“中國文化”,藝術家們希望在此為其創作找到“在地”的存在感,以告慰自己的身份焦慮。于是,“再中國化”就作為一個選項被提出來了。
“再中國化”事實上并非最近十年才有的概念,此前就已經被提出了。當初,它是一個帶有鮮明政治傾向的概念,當然是針對“去中國化”而言的。2008與2009年間,王岳川等人以學者身份出面,連續發文猛烈抨擊國際國內文化領域里的“去中國化”現象,全力提倡“再中國化”。不過王岳川是以政治表態的面目來發表觀點的。10當時,也有文章立足于這兩個概念,來討論“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身份”,但其論據依然是政治立場。112011年以來,在國內當代藝術界,首先是批評家魯虹重提“再中國化”,并且不斷將其作為一個與中國當代藝術命運攸關的問題加以重申。在他看來,“再中國化”不僅是2010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發展趨勢,而且也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唯一出路。12這就把歷史觀和價值觀合二為一了。不過,如果說文化身份焦慮本來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宿命,我們就無法不承認,“再中國化”注定會成為一個方案,為國內當代藝術的參與者們所重視,而不論它表現為劉驍純的“墨思默想”、高名潞的“意派論”、朱其的“傳統即當代”、呂澎的“溪山清遠”,抑或是王林的“中國經驗”和朱青生的“本土精神”。當然,這些論點也招致了批判,例如程美信就認為,這些理論口號表明,“一向以顛覆傳統和反叛精神為標桿的中國當代藝術(先鋒派前衛藝術)出現了逆轉”13。不過,觀點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外一回事。最近十年來,一股“再中國化”的思潮的確在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界和理論界都表現出強勁的勢頭。也許正因為如此,2014年,湖北“第三屆美術文獻展”才把其學術研討會主題確定為“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14
這股“再中國化”思潮在創作上有兩個朝向:一個是傳統媒介轉化(包括實驗水墨及其他非水墨傳統媒介的當代轉化),一個是中國敘事(包括傳統符號敘事和當下敘事)。由于“地”涉“中國”這個宏大概念,“再中國化”所體現出的“在地性”選擇,主要意味著從中國既有傳統中發掘資源,為我所用,而不論是形式資源還是內容資源。魯虹指出,有一些是在民國以前的老傳統中尋求營養,有一些是面向1949年以來形成的新傳統尋找元素。15但無論利用哪種傳統,過去都早有先例,只不過這十年來有了更多的花樣、更炫奇的形式,以及更多的說法。針對實驗水墨過分在工具性范疇中玩巧的現象,李小山說:“從‘中國畫’變為‘水墨’,表面看不過是概念的轉換,而實質卻是從‘文化’逃避到了‘材料’,大大縮小了它的內涵。”16我們認為,這實可舉一反三,道出形形色色“再中國化”當代藝術創作的表面化與標簽化之弊。
眾所周知,當代藝術不僅指當代藝術創作,而且還包括當代藝術的一整套運作機制,因此,對中國當代藝術來說,文化身份的焦慮就不光是藝術家的焦慮,也是批評家、策展人以及機制運作者們的共同焦慮。這種系統化的焦慮又將注定把我們再次帶回到對展覽的觀照之中。2010年,侯瀚如把自己寫作的一篇英語短文“Towards a New Locality”(走向新的在地性)翻譯成漢語,將其發表在一家國內期刊上。他把“地域性”(Locality)一詞譯為“在地性”。文中寫道:“每個地方的當代藝術雙年展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在文化上和地緣上向外擴展的企圖。在展覽中,他們通過推出特別的,甚至其他地方不可比擬的地域性特征,即我們所說的‘在地性’來爭取其在全國甚至全球的聲望。理想的狀態是,在地性的概念和當地的傳統文化相連接的同時帶有新的創造性,并且對國際文化的發展變化持開放態度。推出國際藝術家的作品是實現這種目標的有效策略,并成為加速這一進程的催化劑。”17該文對全球雙年展的意義前景展開了暢想。回味文中的說法,我們被提醒認為,如果“全球在地化”是一種做法,那么“在地全球化”就是一種意義,正是因為有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在地全球化”,全球化才不顯得是一個殖民化過程。這對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來說,意義特別重大。如果說中國藝術家出征威尼斯平行展是一種“全球化”演練,那么,近一二十年雙年展在全國各地的爭相涌現,便演繹出了一種“在地化”的盛況。
事實上,在國內采用雙年展模式的國際性當代藝術大展中,人們也一直在用各種聲音應答侯瀚如的暢想。始于2002年的廣州三年展,以“重新解讀:中國實驗藝術十年(1990—2000)”為開篇,到2008年的第三屆,便大聲宣布要“與后殖民說再見”了。而同年舉辦的第三屆南京三年展,以“亞洲方位”的主題,發出了一則“再中國化”的宣言:“通過對今天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和注解,由此產生可能對全球文化帶來新的思想和圖解樣式。讓全球分享中國當代文化的同時,理解中國文化淵源和精神。”18隨后,2015年舉辦的第五屆廣州三年展不僅打出了首屆亞洲雙年展旗號,而且將主題設定為“亞洲時間”。回望南京三年展,我們感到,這下“方位”和“時間”都齊了。本次展覽表示,它是以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倡議為策展指導理念的。展覽中涉及到絲綢之路、殖民與后殖民事件、移民和僑民、身份追問、城市化進程、文化相對主義、女性覺醒、信仰危機、媒介化社會、亞洲時間、世界時間等關鍵詞19,連綴起一篇與中國國家敘事聯系緊密的關于“亞洲身份”的命題作文,從而把一種身份焦慮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作為國內雙年展中創辦歷史最為久遠的上海雙年展,其各屆策展主題的變化,也許更能側面地反映出中國當代藝術問題意識的遷移。1996年,首屆上海雙年展以“開放的空間”為主題,表征了中國當代藝術最早的價值關切和行動起點。然后,經過“融合與拓展”(1998),一種回歸本土經驗、重塑主辦者文化身份的愿望開始顯現,并在第三屆展覽的主題——“海上·上海”(2000)——中留下痕跡。從第四屆開始,上海雙年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選題時期,從“都市營造”(2002)到“影像生存”(2004)、“超設計”(2006),再到“快城快客”(2008)、“巡回排演”(2010),每一屆主題都各自聚焦于某個微觀問題,或者屬于當代藝術自身,或者關涉某個全球性的社會熱點,但展覽的具體內容卻表明,它們無不是在中國與世界對話的設定情境中展開的。這就是說,文化身份的關切一直作為潛在背景,影響著這些多元主題的選擇與去處。到2012年,上海雙年展由于主辦單位的變更和場地轉移而宣布“重新發電”(2012)——從上海美術館到新成立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從舊上海跑馬場到上海南市發電廠——場地搬遷之情節,不僅意味著上海雙年展脫離了過去閉合而相對狹小的場館,得以進入一個更開闊更敞亮的空間,而且意味著殖民文化的痕跡消失了,民族工業的記憶將成為這個國際大展未來的伴音。雖然是機緣巧合,但由此卻衍生出一個象征性意義——擺脫殖民文化、重塑民族記憶——其結果是既啟發了本次展覽的主題靈感,也賦予了中國當代藝術關乎其文化身份的方位感。這也在接下來的“社會工廠”(2014)、“何不再問”(2016)、“禹步(Proregress)”(2018)等展覽中或隱或明地呈現出來。
在國內林林總總的當代藝術展事中,2004年開始舉辦的湖北“美術文獻展”,直到其第四屆(“應力場”,2017)展覽以前,都是圍繞中國當代藝術本身進行的。這是主辦方《美術文獻》雜志據有豐厚的學術資源而善加利用的結果,因而富有特征性地顯示出“在地性”的肌理。《美術文獻》雜志盡管創刊于1994年,但其前身卻是“85新潮”時期影響巨大的《美術思潮》,其學術積累薪火相傳。2004年的首屆文獻展以提名展形式,“幾乎概括評介了這十年中國當代藝術各個門類創作的現象和潮流”,呈現了“中國社會本土化生存的綜合場景”20,有著以湖北“重啟”國內當代藝術新篇的意義。就在這個開篇展上,王林提出“本土推進比國家交流更重要”21的論斷,有似于為本項展事鋪設了一個底色,使它與“中國經驗”“中國文化身份”這些問題緊緊相聯。至少迄今為止,接下來的各屆“美術文獻展”都不斷觸動著中國當代藝術本土性建構這一條潛在的問題線索。
在第二屆展覽(“觀念與形態”,2007)上,主策展人皮力談到:“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在中國社會內部而不是在藝術市場、藝術掮客和觀光客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將是藝術家們面臨的首要問題。”面對已經出現的危機,他提出,“真正的解決方案或許只有倡導一種新的認識態度和工作態度,即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文化問題從內部的而不是從外部準繩來評判中國文化現象的意義”22。到2014年的第三屆展覽上,主策展人冀少峰以提出“再現代”的展覽主題而與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形成頗有張力性的互文關系。他指出:“(再現代)這個主題,其實是對中國價值、中國模式、中國崛起、中國主體性的再認識,旨在探討傳統文化如何適應并轉化出現代價值,進而穿越傳統為現代化設置多種屏障逐漸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的過渡,終極目的是構建有中國文化性格的現代文明秩序,即價值系統、制度體系受經濟、社會、政治、國際環境和文明形態轉型。”23這樣,“第三屆美術文獻展”就把現代化焦慮與文化身份焦慮擺到了同一個領域中,并以現代化焦慮來回應文化身份焦慮,啟示了中國當代藝術關聯中國社會所應有的價值方位。當我們從這里意識到現代化仍是中國社會的第一要務時,就會邏輯地聯想到,中國當代藝術在尋求在地化的同時,實在不能忘了全球化的意義。也許正是有了這個思想作鋪墊,2017年的“第四屆美術文獻展”,便以15個國家、57位藝術家、127件作品的跨文化景象,組成了一個“應力場”。如其主策展人馮博一所說:“‘在地’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純粹的概念,它跟全球性是有緊密關系的。”24本次展覽力圖給出一個證明。
余論:從藝術鄉建到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方位
如前文所述,“在地性”之“地”有大有小。本來,這個概念就來源于英語。漢語中目前所使用的“在地性”一詞,至少指涉三個英語詞:第一個詞是Locality,其原始含義為地方性、地域性、本土性,可延伸為地方文化、本土文化;第二個詞是Site-Specify,指的是“在特定地點”,重在某物與特定物理空間的關聯,或可譯為“限地性”;第三個詞是in-site,意指“在當時當地”,可譯為“現場性”。顯然,“再中國化”所連系的“在地性”,指向中國本土文化。可是,在過去十年中,國內當代藝術還有一種現象,便是藝術家走出工作室,去到鄉間地頭,實施與具體村落相聯系的“在地藝術”(Site-Specific Art),其口號是助力鄉村建設,故形成一股“藝術鄉建”熱潮。這樣,我們能見識到中國當代藝術在地性實踐所據有的兩個層面:“再中國化”是其宏觀層面,藝術鄉建是其微觀層面。考察后者的得與失,將對我們辨別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方位,有著重要的鏡鑒作用。
“藝術鄉建”概念,實處于藝術與社會的邊緣地帶,權界甚為模糊。就算是用了博伊斯的“社會雕塑”來作類比,也難以明了其界。因為藝術家和委托人各有打算,前者關心的是藝術,后者關心的是鄉建。這就好比米開朗基羅接手的教皇儒略二世陵墓或圣洛倫佐教堂新圣器室工程那樣,教皇和美第奇家族的主事人希望得到滿意的墓園和家族禮拜堂,而米開朗基羅卻希望它們成為藝術品。因此,當藝術介入鄉建之時,藝術界人士更樂于選擇有助于突出藝術的內容,例如,靳勒的“石節子美術館計劃”就通過雕塑、巖體刻字、攝影、裝置、視頻投影、民藝等,把全村變成了一個公共美術館;歐寧的“碧山計劃”也通過引入書局、舉辦展覽和開展建筑教學與實驗活動,為鄉村涂滿藝術人文色彩。同樣因為想要突出藝術,大型藝術展、藝術節自然更成為藝術界人士樂于選擇的活動方式了。不過,對一個藝術鄉建項目而言,藝術界人士終歸不過是接受委托的一方,而真正的主導力量是委托人。按中國國情,這樣的委托人往往既要牽涉政府又要牽涉企業,政府有政績的考量,企業有盈利的目的。且不說兩者的動機如何復雜糾結,但它們與藝術家的目標之間,肯定不會總是處于和諧狀態。
本來,藝術鄉建的主體當然是在地村民,他們是預期的受益者,應該在這關系到其未來福祉的事業上擁有決定權。可是,在現實中,村民的權利卻早已被假定讓渡給項目的委托方和承接方了。至于項目如何進行,他們扮演什么角色,則須聽憑編導者的組織和安排。所以,盡管十年來藝術鄉建運動如火如荼,但它們在整體上總是躲不過一個詰問:誰的藝術鄉建?雖然此問涉及的關系錯綜負責,但至少包含著一個對象,那便是藝術與鄉建的關系。于是問題就會變成:到底是藝術為鄉建服務,還是鄉建為藝術服務?策展人廖廖總結了目前藝術鄉建的幾大種類:保護傳統特色民居、挽救失傳的手工藝、重現傳統民俗典禮、興建農村美術館(以及藝術家在鄉間建立工作室),然后說:“更多時候,藝術鄉建只是城市人對農村文化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滿足了城市人對鄉村郊野的一種桃花源式的幻想。藝術家對鄉村的贊美和裝飾顯得空洞而蒼白,只是借了鄉村的民居與山水,作為藝術與設計中的一個元素。許多藝術鄉建只能感動中產階級,但是與真實的農村沒有關系。”25如果我們相信他的說法,便會立刻明白,目前,藝術與鄉建到底誰在為誰服務了。
作為內地藝術鄉建先行者之一的渠巖,也概括出十種方式和三種類型,據以描述了目前藝術鄉建的現狀。他感嘆道,在這股熱潮中,鄉村被各種勢力利用,往往本末倒置,失去了鄉村建設的本意。追蹤其原因,他認為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國內當代藝術未能擺脫長期依賴、模仿西方話語邏輯的境況,另一條是藝術家未能突破“精英”“唯美”話語和自我中心主義。26基于這樣的反思,在其第二個重要鄉建項目“青田計劃”中,渠巖提出了“去藝術化”主張。照我們理解,所謂“去藝術化”,應該不是不要藝術,而是要放棄概念先行——預設什么是藝術,什么不是藝術——就像王南溟所說:“并非只有藝術家做的作品才叫藝術,其他用各種方法生成的視覺符號就不是。”27而且,在鄉建實踐中,只有放棄預設藝術,才能放棄預設等級,才有對在地知識和鄉民之主體性的真正尊重。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唯有尊重鄉民的主體性,藝術鄉建才有可能恢復其良善的起點,也才有可能重返“在地藝術”的現象學基礎,發揮出真正的創造性和惠澤生命的意義。道理只有一個,藝術鄉建的目的不是導向象牙塔的作品,而是要生成博伊斯意義上的“社會雕塑”。在此,忘掉藝術,才是最好的藝術。
對待藝術鄉建的前景,目前存在著兩個爭議觀點:一個著意于鄉土生態與傳統的恢復,一個著意于鄉村的現代化改造。前者從“鄉土”“傳統”“生態”這些概念中尋找辯護,后者則從民生出發予以反駁。人類學者方李莉說:“中國未來的道路不是把鄉村莊園化、風情化、現代化,而是要從鄉土中國走向生態中國。”28似可代表前者的觀點。后者卻強調說,藝術鄉建不能為了“極力維護‘古老傳統’而無視農民們走向現代化、改善生活質量的要求”。他們斷言,如果脫離當地現實,無法對接農民的真實需求、無法解決農村的現實問題,藝術鄉建則注定遭遇擱淺的命運。29作家閻海軍舉2016年被廢止的“碧山計劃”為例說:“歐寧反對碧山像宏村一樣過度商業化,但不能給碧山農民帶來實際收益,不能改變農民的現實,藝術鄉建到底建設什么?沒有很好的介入,哪個農民會跟著你玩藝術?”30這就是基于民生的考量。另一個考量則是從農村文化該不該永遠落后的問題出發的。廖廖對挽救失傳手工藝和重現傳統民俗典禮兩個鄉建種類的評價,就說出了這樣一個邏輯:“如果挽回傳統手工藝對農民有用,是否意味著農民只能在保守、封閉、僵化和不方便中生活?被鄉建藝術家重新祭起的傳統民俗典禮如果不是一個空殼,那么,它所代表的宗族文化、封建倫理和等級秩序是否都應該被恢復?”31
作為微觀的在地藝術,藝術鄉建勢必同樣逃不過“在地化”與“全球化”雙向運動的節律。不過,就中國的特殊性而言,它們之間更顯得像是一種張力輪回的關系,一個代表了傳統,一個代表了現代。這樣,藝術鄉建就不得不以其糾結和掙扎而與中國當代藝術共享宿命。在激烈爭論中,兩種藝術鄉建觀都表態說,自己要尊重和“重建”在地知識,但它們對在地知識的理解卻迥然有異:一個僅指過去的知識,一個指不斷積累而變化的新知。王端廷曾經指出,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化之路,究其本質乃是“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如果農村無理由被排除在這種轉化之外,那么我們就只得承認中國農村的在地知識,并不僅僅指那些早已過時不動的知識。認識到這一點,藝術鄉建之“在地”,才開始有了條件。
這個條件不僅是為藝術鄉建準備的,也是為整個中國當代藝術準備的。它啟示我們將“在地性”與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方位緊緊相連;它告訴我們,在地,也是在時間——在歷史,在當下——在這個時空匯聚點上,“再中國化”以及所謂“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身份”也將獲得新的洞察。王端廷說:“就中國而言,傳統與當代、本土與世界的雙重糾纏使得中國藝術的當代性呈現出鮮明的混雜特征,因而評價中國當代藝術便有了國內與國際兩個標準。一些在西方已經完結、屬于現代性范疇的創作主題和藝術樣式,譬如抽象主義,在中國當代藝術中仍有存在的價值;甚至作為西方文化本源亦即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觀念之化身的古典寫實主義在中國當代藝術中仍發揮著‘持續啟蒙’或‘觀念補課’的作用。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主義與勢不可擋的普適主義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全球地方主義’(Globalocalism)的嶄新藝術潮流。簡而言之,全球地方主義就是用地方語言表達普遍人性和普適價值的藝術觀念。”32這也許就是湖北“第三屆文獻展”既重申“再現代”、又要討論“再中國化”的用以所在,因為它也是中國藝術的價值方位所在。
注釋:
1.裴剛:《全球化、市場化、去政治化:中國當代藝術的十年之變》,雅昌藝術專稿,2016-04-19。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The Global Art World:Audiences, Markets,and Museums, Edited by Hans Belting,Andrea Buddensieg, Global Art and Museums(GAM),2006.P.2.
6.彭菲:《雙年展的全球危機和跨學科解決之道?》,雅昌藝術專稿,2016年9月6日。
7.歐陽宏生、梁英:《混合與重構 :媒介文化的 “球土化” 》,《現代傳播 》2005年第2期。
8.Ritzer G.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SAISRe view,2003,23(2):192.
9.[美] 張英進:《影像中國 :當代中國電影的批評重構及跨國想象》,胡靜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91頁。
10.參見:王岳川:《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的文化戰略——大國文化安全與新世紀中國文化的世界化》,《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10期;《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文藝爭鳴》2009年第1期;《文化走向: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花城》2009年第1期。
11.參見:時勝勛:《從“西方化”到“再中國化”——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身份》,《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10期。
12.魯虹:《“再中國化”是中國當代藝術唯一出路》,《中國美術報》2017年4月17日。
13.程美信:《“再中國化”的可能性及其謬誤性》,中國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網,2011年9月22日,https://www.sinoss.net/images/logo.gif。
14.冀少峰等:《“2014·武漢 第三屆美術文獻展”學術研討會紀要》,《美術文獻》2014年第7期。
15.參見:魯虹:《中國當代藝術的“再中國化”問題》,《中國美術》2013年第4期。
16.李小山:《從“中國畫”到“實驗水墨”》,《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 2002年第2期。
17.侯瀚如:《走向新的在地性》(Towards a New Locality),侯瀚如、周雪松譯,《東方藝術》2010年第23期。
18.谷靜:《凸顯藝術家主體——第三屆南京三年展開幕》,《藝術與投資》2008年第10期。
19.趙婉君:《首屆亞雙展聚焦“亞洲時間”》,《美術》2016年第12期。
20.皮力:《第二屆美術文獻展:觀念的形態-1987-2007中國當代藝術的觀念變革》,湖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21.王林:《展覽序三:本土推進比國際交流更重要》,《美術文獻》2014年 第11期。
22.同(20),第9頁。
23.《2014 武漢第三屆美術文獻展:再現代》,湖北美術館官網,2014年9月23日。
24.洪鎂:《當我們談論“第四屆美術文獻三年展”的“國際化”時,我們是在談論什么?》,雅昌藝術網專稿,2017-09-16。
25.廖廖:《藝術鄉建不能跟真實的農村沒有關系》,《中國美術報》2016年10月31日,總第41期。
26.渠巖:《鄉村危機,藝術何為?》,《美術觀察》2019年1期。
27.王南溟:《鄉建、藝術鄉建與城鄉互動中的幾種理論視角》,《美術觀察》2019年第1期。
28.《“藝術鄉建的中國期待”——2017中國藝術鄉建論壇紀實》,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網站,2017-10-12,201https://www.sohu.com/a/197539780_318871
29.《中國美術報》2016年10月31日,總第41期,新聞時評“編者按”。
30.閻海軍:《藝術鄉建開花容易結果難》,《中國美術報》2016年10月31日,總第41期。
31.同25。
32.王端廷:《時代與使命——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研討會綜述》,《美術》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