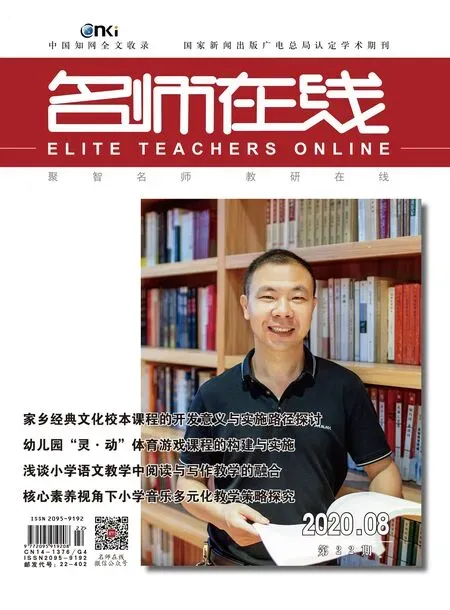想象:察一切所察,覺(jué)不觸之覺(jué)
——以統(tǒng)編三年級(jí)下冊(cè)《古詩(shī)三首》為例談圍繞意象的閱讀
莫祥慧
(江蘇省揚(yáng)州市江都區(qū)仙女鎮(zhèn)中心小學(xué),江蘇揚(yáng)州 225200)
引 言
古詩(shī)教學(xué)的方式方法很重要,如何讓學(xué)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jué),跟著詩(shī)的節(jié)拍深入其中,需要教師充分發(fā)揮想象、利用想象,不斷創(chuàng)新教學(xué)模式。
一、古詩(shī)教學(xué)現(xiàn)狀分析
在實(shí)際教學(xué)中,由于許多教師教學(xué)理念陳舊,教學(xué)內(nèi)容不準(zhǔn)確,教學(xué)方法單一,機(jī)械地組織教學(xué)過(guò)程,課堂常常呈現(xiàn)這樣的狀態(tài)。
(一)讀停留于簡(jiǎn)單重復(fù)
讀,應(yīng)該一遍有一遍的目標(biāo),一遍有一遍的收獲。學(xué)生自己讀,能讀正確,讀出五言七言詩(shī)的節(jié)奏。教師指導(dǎo)讀,應(yīng)該讀出理解,讀出畫(huà)面,讀出語(yǔ)言間的關(guān)聯(lián),讀出自己的想象[1]。然而,在實(shí)際的教學(xué)中,仍然存在讀的層次沒(méi)有梯度,讀的指導(dǎo)沒(méi)有目標(biāo),讀的方法沒(méi)有明確的問(wèn)題。
(二)詩(shī)意領(lǐng)悟停留于單一復(fù)說(shuō)
從小學(xué)古詩(shī)教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學(xué)生正處于最關(guān)鍵的古詩(shī)學(xué)習(xí)期,正在經(jīng)歷從初步感受古詩(shī)語(yǔ)言的優(yōu)美到體味古詩(shī)的內(nèi)容和情感的過(guò)程。依據(jù)課程標(biāo)準(zhǔn),詩(shī)意的領(lǐng)悟在中年級(jí)開(kāi)始應(yīng)該成為古詩(shī)教學(xué)的重點(diǎn)。遺憾的是,很多教師采用的教學(xué)方式過(guò)于粗陋,把教學(xué)重心放在逐字逐句講解上,只訓(xùn)練學(xué)生進(jìn)行大量的字詞句注釋摘抄、機(jī)械默寫(xiě),不顧及語(yǔ)言的美感,不揣摩古詩(shī)的獨(dú)特結(jié)構(gòu),不指導(dǎo)學(xué)生的想象角度,不支撐學(xué)生的情感體驗(yàn)。“領(lǐng)悟大意”變成對(duì)教參的一再重復(fù)、機(jī)械復(fù)說(shuō),這樣的學(xué)習(xí)效果怎么可能優(yōu)化?
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知識(shí)絕不是以“靜態(tài)資料”的方式被接受的。文本資料是支配不了感知的,支配感知效度的是根據(jù)資料所進(jìn)行的種種感知推斷的解答。如果“領(lǐng)悟大意”的教學(xué)內(nèi)容就是教參中呈現(xiàn)的“詩(shī)句翻譯”,而這些“資料”又不經(jīng)過(guò)學(xué)生“感知”“解碼”并有效地“儲(chǔ)存”起來(lái),學(xué)生的古詩(shī)學(xué)習(xí)積極性會(huì)逐漸下降,對(duì)小學(xué)古詩(shī)課文產(chǎn)生抵觸情緒,最終帶來(lái)古詩(shī)教學(xué)的高耗低效。
(三)詩(shī)境領(lǐng)悟方法不明
《義務(wù)教育語(yǔ)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2011年版)》對(duì)第三學(xué)段(5~6年級(jí))的要求為:“閱讀詩(shī)歌,大體把握詩(shī)意,想象詩(shī)歌描述的情境,體會(huì)作品的情感,受到優(yōu)秀作品的感染和激勵(lì),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詩(shī)境領(lǐng)悟已成為高年級(jí)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重點(diǎn)和難點(diǎn),這也是小學(xué)與初中古詩(shī)學(xué)習(xí)的必要銜接。這一難點(diǎn)長(zhǎng)期困擾著小學(xué)甚至中學(xué)古詩(shī)教學(xué)課堂,需要教師不斷地去實(shí)踐、摸索和創(chuàng)新。
二、把“想象”發(fā)揮到恰到好處
很多教師解讀課標(biāo),找到“想象”這一方法,并把“想象”指導(dǎo)實(shí)施為在詩(shī)意基礎(chǔ)上的拓展說(shuō)話(huà)。例如,《所見(jiàn)》的“歌聲振林樾”一句,教師指導(dǎo)“嘹亮的歌聲在樹(shù)林里回蕩,那聲音怎么樣?”學(xué)生只是答復(fù):“聲音非常嘹亮、悅耳。”然而,真正的詩(shī)境“想象”,是有準(zhǔn)確的方法和角度的。《所見(jiàn)》的想象應(yīng)該基于兩個(gè)角色:牧童和蟬,他們無(wú)意間開(kāi)始一場(chǎng)博弈,牧童的高歌與響亮的蟬鳴相互纏繞,嘹亮的二重奏在樹(shù)林回蕩,帶來(lái)牧童的忽然發(fā)覺(jué)、忽然閉口、忽然佇立。只有如此“想象”,童趣才會(huì)躍然于眼前。
《義務(wù)教育語(yǔ)文課程標(biāo)準(zhǔn)(2011年版)》對(duì)第二學(xué)段(3~4年級(jí))的要求為:“誦讀優(yōu)秀詩(shī)文,注意在誦讀過(guò)程中體驗(yàn)情感,展開(kāi)想象,領(lǐng)悟詩(shī)文大意。”第一單元三首詩(shī)的書(shū)后習(xí)題第二題為:“結(jié)合詩(shī)句的意思,想象畫(huà)面,說(shuō)說(shuō)三首詩(shī)分別寫(xiě)了怎樣的景象。”如何想象感受詩(shī)歌的景象呢?北京大學(xué)袁行霈教授說(shuō):“講詩(shī)歌藝術(shù)境界這個(gè)范疇,仍然顯得籠統(tǒng)。再深入一步,用意象來(lái)說(shuō)明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和藝術(shù)規(guī)律,我想是可以的。”因?yàn)楣旁?shī),通常是以無(wú)數(shù)個(gè)意象疊加、組織、生成,最后才形成詩(shī)歌意境的。本單元三首詩(shī),以意象的神奇組合,繪就了三幅經(jīng)千年仍璀璨動(dòng)人的春意圖。教者可以書(shū)后習(xí)題為引,嘗試從古詩(shī)的意象閱讀,展開(kāi)想象之旅。
(一)關(guān)注字詞內(nèi)涵,進(jìn)行意象的整理歸類(lèi)
習(xí)題問(wèn):“三首詩(shī)分別寫(xiě)了怎樣的景象。”要想知道“分別”寫(xiě)了什么,就須緊扣字詞,梳理羅列物象,察一切所察。《絕句》中有江山、花草、燕子、鴛鴦;《惠崇春江晚景》中有桃花、戲鴨、蔞蒿;《三衢道中》中有梅子、山路、黃鸝,都是春景。再深入一點(diǎn),給它們填上形容詞:(壯麗的)江山、(飄香的)花草、(飛忙的)燕子、(臥睡的)鴛鴦、(三兩枝的)桃花、(游水的)戲鴨、(短蘆芽的)蔞蒿、(黃的)梅子、(綠蔭的)山路、(啼叫的)黃鸝。當(dāng)把這些短語(yǔ)帶上色、香、態(tài)、聲等,便帶上詩(shī)人主觀的色彩,代表詩(shī)人的構(gòu)思。此刻,物象成為意象。羅列出來(lái),可以讓我們粗略感受詩(shī)人眼中春的景象。
下一步則須進(jìn)行整合比對(duì)。如果把這些帶上形容詞的短語(yǔ)合并歸類(lèi),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短語(yǔ)與短語(yǔ)之間是有共性的。(壯麗的)江山、(綠蔭的)山路、(飄香的)花草、(三兩枝的)桃花、(短蘆芽的)蔞蒿、(黃的)梅子,都是春的靜物。(飛忙的)燕子、(啼叫的)黃鸝、(臥睡的)鴛鴦、(游水的)戲鴨,都是春的動(dòng)物。
這樣的發(fā)現(xiàn)會(huì)讓學(xué)生了解到三首詩(shī)在內(nèi)容選擇上有相似性,是“從景到物”的觀察。從風(fēng)雨雷電、花草樹(shù)葉到鳥(niǎo)獸蟲(chóng)魚(yú)……當(dāng)然,選擇的具體內(nèi)容有一點(diǎn)差異,如杜甫選燕子、鴛鴦,曾幾選黃鸝,蘇軾則選擇最有農(nóng)家生活氣息的鴨。學(xué)生在這樣的比對(duì)梳理后,整體把握詩(shī)歌素材的異同,把這首詩(shī)和那首詩(shī)勾連起來(lái),體會(huì)到不同詩(shī)人對(duì)春天的不同觀察,在腦中畫(huà)出一幅幅既相似又有差異的圖畫(huà),為將來(lái)描寫(xiě)季節(jié)積淀規(guī)律性的認(rèn)知,積累素材。
(二)關(guān)注全詩(shī)意思,嘗試意象的疏密分析
習(xí)題要求結(jié)合“詩(shī)句的意思”,想象畫(huà)面。理解單個(gè)的詞語(yǔ)或短語(yǔ)意思,形成的是對(duì)單個(gè)意象的聯(lián)想。只有展開(kāi)對(duì)全詩(shī)所有意象的排列、布局,才能在畫(huà)布上繪出一幅畫(huà)。此時(shí)要結(jié)合全詩(shī)的意思,想象眼前這幅畫(huà)什么位置分布著什么,它們有一定的空間、時(shí)間或者邏輯關(guān)系,這樣才能讓學(xué)生更好地理解這幅畫(huà)。
《絕句》講究開(kāi)合。從闊大的壯麗江山開(kāi)始,隨后飄來(lái)無(wú)處不在的花草香氣,春帶著撲面而來(lái)的氣息,拉開(kāi)闊美的畫(huà)卷[2]。一、二句的春是無(wú)邊無(wú)際的;三、四句則收縮視野,看向屋檐下的燕子、河岸邊纏綿的鴛鴦。它們是活的生命體,無(wú)論是筑巢還是臥睡,都分明孕育著春的真正希望。燕子飛忙的身影是為了筑巢,鴛鴦睡臥著,卻仍交頸摩挲。它們?cè)杏碌纳w的誕生!整首詩(shī),由遠(yuǎn)及近,由虛到實(shí),動(dòng)里藏著靜,靜里又蓄著動(dòng)。這樣的意象排布,怎能不叫人拍案叫絕?
《惠崇春江晚景》冷暖有變。從岸邊的桃花寫(xiě)起,只有三兩枝,疏淡至極,此刻早春氣猶寒。但是河里,一群鴨把彌漫寒意的畫(huà)面給攪“活”了,可以想象它們嘎嘎的叫聲喚醒了初春的荷塘。再看,河邊,滿(mǎn)地蔞蒿叫人歡喜,這份喜悅是因?yàn)樘J芽長(zhǎng)得動(dòng)人嗎?不是。冒出的蘆芽吸引人,是因?yàn)樗嘞憧煽冢敲牢都央取.?dāng)蘆芽可吃的時(shí)候,河豚當(dāng)然也快長(zhǎng)成可享用啦!一股溫暖的生活氣居然就從淡淡的、冷冷的畫(huà)面中升騰起來(lái)。這首詩(shī),善于從平淡、簡(jiǎn)約中造出熱鬧的春的歡喜,同樣也暗含生命不息、勃發(fā)生長(zhǎng)的蘊(yùn)意。
《三衢道中》與前兩首一樣也是節(jié)奏有變,明暗有別。從陰涼的山路轉(zhuǎn)到黃鸝雀躍,從寂靜的行走到回程增添出一路活潑,前后色調(diào)、心情均有對(duì)比。
意象的開(kāi)合,冷暖、靜動(dòng)、陰晴形成變化,讀來(lái)一層有一層的新意。學(xué)生在思維的跳動(dòng)、視野的變換中,感受畫(huà)面的生動(dòng)、新鮮。
(三)探索看不見(jiàn)的關(guān)聯(lián),思考意象的疊加再生
詞與詞、句與句之間的關(guān)系,并非只有表面的時(shí)空、對(duì)比等關(guān)系。要讀懂本首詩(shī)中的畫(huà)面,除要“看”到畫(huà)上分布著什么外,更要“想”到物與物、景與物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意象與意象疊加中生成新的圖像[3]。
《絕句》中,杜甫寫(xiě)飛燕、鴛鴦,他不是在單一地寫(xiě),而是在燕子的奔忙中,講到這是燕子感知了泥土的融化,因而銜泥奔忙。這是多么聰慧的燕子。臥睡的鴛鴦因?yàn)楦兄缴匙拥幕嘏抛栽谑孢m地待在岸上,依偎著安睡。泥土與燕子、鴛鴦與沙子是相互感應(yīng)的,物與物、意象與意象為我們營(yíng)造了豐滿(mǎn)的大自然。那里的一切息息相關(guān),彼此照應(yīng)。
此刻,如果追問(wèn),杜甫是先去感受泥土和沙子的溫度再寫(xiě)燕子和鴛鴦的,還是站在春天里,望著飛燕和鴛鴦,甚至連飛燕和鴛鴦都沒(méi)有見(jiàn)到,僅僅根據(jù)經(jīng)驗(yàn)就能敏銳地感受到自然界的變化?顯然,第二種更有可能。杜甫的這份體驗(yàn),珍貴之處就在于他深切地了解自然界的奧秘,并能有機(jī)地把小動(dòng)物與變化復(fù)蘇的大地聯(lián)結(jié)起來(lái),把他贊頌的春的生命力告訴我們。
《惠崇春江晚景》中,蘇軾更勝一籌。他由幾只在江上游著的鴨想到了很多。鴨為何會(huì)下水?是它提前知道了江水的溫暖,知道融化的江水里有蝦有魚(yú)嗎?也許是的。鴨是一個(gè)先知者,先知水暖,急迫地下河覓食。然后,它看到“暖”帶動(dòng)一池春水,帶動(dòng)一江花草,帶動(dòng)鳥(niǎo)獸蟲(chóng)魚(yú)。再接著,蘇軾的眼里,我們的眼里,春的所有意象融合在一起,它們不是割裂的,你完全可以從一只“鴨”的視野,看到充滿(mǎn)煙火氣的春天。這樣的畫(huà)面是蘇軾為我們創(chuàng)造的。蘇軾看到這一切了嗎?沒(méi)有!他的眼前其實(shí)只有一幅不動(dòng)的畫(huà),畫(huà)上只有幾只不動(dòng)的鴨,江水也不會(huì)讓他感受到“暖”!但他就能把鴨寫(xiě)得這么先知先覺(jué),就能不動(dòng)聲色地把春的能量昭告天下,包括蘆芽的萌發(fā)、看不見(jiàn)的水里河豚的發(fā)育。作者只有“感不觸之感,見(jiàn)不視之見(jiàn)”,才能把一切春來(lái)的信息公布于天下;讀者通過(guò)鴨“知”水暖的一個(gè)“知”字展開(kāi)無(wú)限想象,才能獲知蘇軾寫(xiě)的不是景,而是萌動(dòng)的早春、活潑的自然[4]。
結(jié) 語(yǔ)
僅僅了解意象有哪些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通過(guò)“想象”,把意象之間進(jìn)行補(bǔ)充、聯(lián)結(jié)。劉禹錫說(shuō):“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境是綜合的效應(yīng)。詩(shī)人是這樣思考的,學(xué)生更應(yīng)這樣去深讀,這才是想象的最高境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明白詩(shī)人最了不起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