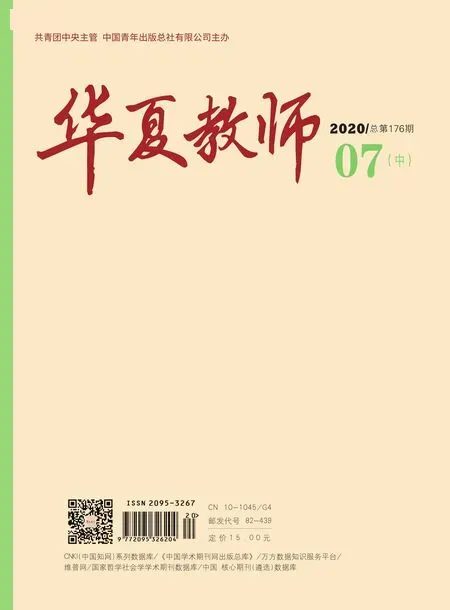因學設導,以導促學
——基于科學核心素養下的導學課堂
福建省福安師范學校附屬小學 鄭吉穎
2017 版小學科學課程標準指出:學生是學習與發展的主體,教師是學習過程的組織者、引導者和促進者。在小學科學教學中,教師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基于學生的認知水平,聯系學生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創設良好的學習環境,引起學生的認知沖突,引導學生主動探究,啟發學生積極思維。在科學課堂采用“疑—導—學—用”的教學模式即以學案為載體,以導學為方法,教師的指導為主導,學生的自主學習為主體,師生共同合作完成教學任務的一種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改變了過去老師單純講、學生被動聽的教學模式,充分體現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使主導作用和主體作用和諧統一,發揮出最大的課堂教學效率,從而實現高效課堂這一終極目標。
一、因學設導,導在學生的認知上
陶行知先生曾說過:“教什么和怎么教,絕不是憑空可以規定的,他們都包含‘人’的問題,人不同,則教的東西、教的方法、教的分量、教的次序都跟著不同了。”現代課堂,學生是科學學習的主體,學生的原有認知基礎就是教師教的起點。每次教學新課前我都設計一些簡單的小問題,通過與學生的交流和討論明確學生原有的認知基礎,根據學生掌握的知識技能,選擇恰當的方式組織教學。從學生原有認知入手,逐步引導學生自主探究,使科學課堂充滿智慧和趣味,也使科學教學蘊含更深層的現實意義。
二年級上冊“神奇的紙”這一課的教材原來是這樣設計的:教師通過視頻或現場演示示范瓦楞狀紙的折疊方法,再引導學生通過實驗探究對比紙折疊前后性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課前,我通過與學生的交流,發現二年級的孩子對于紙已非常熟悉,幼兒園時就有用紙折扇子的經歷,對將紙折成瓦楞狀一點不陌生,他們只是不了解平時他們所折疊的這種形狀是瓦楞狀而已。像這樣的設計在我們的教材中并不鮮見,學生已經掌握了,我們卻非要教,這樣的教學顯然是無效的。因此,我對這一環節進行了重新設計,我先將一張普通A4 紙放在兩端有支撐而中間凹陷的架子上,在紙上放上一塊橡皮,紙馬上就塌了。借由這個情境我請學生完成改造紙的任務:改造一張普通A4 紙使它具有支撐橡皮的能力。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任務一提出就給了學生充分自主探究的權利,有的孩子將紙折厚以承受橡皮的重量,有的孩子將紙折成瓦楞狀,還有的甚至將紙卷成圓柱立起來。這些方法都能讓紙能支撐橡皮,但他們在實驗中也發現瓦楞狀紙所能支撐的橡皮的數量要遠遠多于其他兩種改造,這讓他們對瓦楞狀紙的神奇功能更感興趣了,為下一環節的探究打下基礎。這樣在學生認知基礎上,對教學環節進行適當的刪改,不僅將有限課堂時間留給學生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自主改造紙,也使他們的改造有的放矢,不會因為目標不明確而茫然不知所措。
像這樣導在學生的認知上,導在學生的應學之處,不僅給學生提供了自主改造紙的機會,也使整個環節設計簡潔而有探究性,符合學生的認知需求,真正做到將課堂交還給它的主人——學生。
二、順學而導,導在課堂生成時
科學課堂的開放性使科學課堂常常“意外橫生”,學生在課堂中突然提出教師預設之外問題,發現預設之外的實驗現象或給出意料之外的回答是經常發生的事。該如何應對這些意外狀況,該如何推進此時的課堂教學正是體現教師教學經驗及智慧的關鍵時刻。回避或轉移學生的質疑雖然可以讓課堂順暢地繼續,卻忽視了學生學習需求,學生成了課堂的擺設,長此以往,學生的學習熱情就被慢慢磨滅了。這時候我們應該順勢引導學生對出現的意外生成做出價值判斷,對有價值的發現再進行探究,這樣順勢而生成的課堂導在學生的想學之處,避免了生硬死板,讓科學課堂充滿真實探究的活力。
我有這樣一個經歷,在執教“蝸牛”一課時,學生正在仔細觀察蝸牛的身體結構,突然有個孩子叫道:“我的蝸牛死了!”我走過去一看,他的蝸牛縮在了殼里一動也不動,估計是因為他在觀察時不停用牙簽或樹葉不斷觸碰蝸牛,蝸牛害怕受到傷害所以縮進殼里了。出現了這樣的“意外”,我并沒有急于讓這個學生換一只蝸牛觀察,而是順勢利用了這個美麗的“意外”,引導學生思考:“你有什么辦法確認這只蝸牛到底是活著還是死了呢?”隨之將這個問題拋向了全班,大家議論紛紛。有的學生說要給蝸牛安靜的環境,當它不害怕時就會爬出來;有的學生說用“好吃的”誘惑蝸牛,讓它爬出來;還有學生提出蝸牛很怕水,把蝸牛放入水里就可以了。最后,大家把蝸牛放入水中,果然這只蝸牛被喚醒了,真的就從殼中爬了出來。這節課的這一“意外”不但在學生的討論中得到解決,學生還知道了蝸牛雖然喜歡潮濕的環境卻不能生活在水中,而這只“意外”蝸牛的小主人還真正意識到要使用正確的方法觀察蝸牛,不能傷害或過度刺激蝸牛。
還有一次我執教教科版六年級“抵抗彎曲”這一課,孩子們正用回形針充當重物放在紙橋上探究是增加寬度的紙橋承重能力強還是增加厚度的紙橋承重能力強。許多孩子紛紛說道:“老師,我們的回形針不夠,全部放在紙橋上,紙橋都不會彎曲,怎么辦?”“老師,我們小組的回形針也不夠。”“老師……”怎么辦呢?很明顯因為我的疏忽,實驗材料不夠,課前模擬實驗時使用的一盒回形針的數量比學生實驗時使用的回形針數量多,可我卻沒在意,課該怎么繼續呢?懊惱也來不及了,我急中生智,連忙叫停正在實驗的學生。問道:“同學們,剛才實驗過程中,有些小組的同學用完了所有的回形針也不能使紙橋彎曲,誰能幫忙解決這個難題呢?”學生針對課堂發生的意外狀況紛紛獻計獻策。
三、以導促學,導在學生的疑難處
真實的科學探究活動往往不會一蹴而就,學生常常會遭遇失敗和挫折。這時教師如何引導至關重要,我們雖然了解學生失敗、受挫的原因,卻不宜把實驗的結論直接告訴學生,應該針對學生思維受阻的實際情況進行巧妙地引導,幫助學生突破疑難點,使學生真切地體會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
在教科版小學科學三年級“比較水的多少”一課中,教材呈現出瓶子大小、水位高低不同的三瓶水,讓學生比較哪一瓶水多,哪一瓶水少。當時學生就懵了,到底是比較水位高低還是瓶子粗細呢?顯然都不妥。于是我就通過創設情境,以小豬佩奇一家和佐伊野餐時,通過大家三次分水的情境進行了梯度設疑,逐級降低問題難度。我先呈現一組瓶子相同,水位高低不同的水,問學生哪瓶水多?學生很容易想到瓶子相同,比水位高低。接著,我再出示三瓶水位相同,瓶子粗細不同的水,問學生哪瓶水多?這時,學生想到水位相同,可以比較瓶子粗細。最后我再拋出“水位不同、瓶子粗細不同的三瓶水又如何比較?”此時通過師生的平等對話,我將學生引導到疑難之處,當學生產生認知矛盾,“心求通未解其意,口欲言未達其辭”時,我通過三個有梯度的問題,抓住機會啟發學生質疑思考,幫助學生突破疑難點。很快學生在交流中討論出“分別用三個大小相同的杯子測量”,“用有刻度的容器測量”,“用同一個杯子測量標上記號測量”這三種方法來測量比較水的多少。真正實現了思與行結合、做與思共生的科學課堂。
葉圣陶曾說:“教師之為教,不在于全盤授予,而在相機誘導。”的確,科學課堂是學生的課堂,探究活動是學生的活動,要讓學習真正發生,教師就要把握時機,引導學生的學習,因學設導、順學而導、以導促學,打造以生為本、和諧共振的高效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