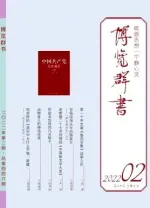馮友蘭的思考與“性善”“性惡”說
孫來燕

“人之初,性本善”出自南宋學者王應麟(1223~1296)《三字經》,意思是每個人生命剛開始的時候,也就是剛出生時,本性都是善良的。由是歷代相傳,很多人將此作為孟子“性善”論的概括,其實這并不是孟子的原意。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在孟子看來,人與禽獸的差別不是很大,只有那么一點點,這一點點就是善端,是仁義。而恰恰這一點點善端、仁義,體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仁也者,人也)。孟子論“性善”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出自《公孫丑(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人,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孟子說人都有同情、憐憫之心,比如一個人看到別家小孩將掉入井中,憑著一種同情憐憫心本能地會去救,他這樣做并非是要和小孩子父母結交情,或者要在鄉里朋友中博取好名聲。孟子由此得出這種要救他人的惻隱之心是與生俱來的,而且像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是與生俱來的,是人就有這四心,沒這四心“非人也”。從孟子這段話中,似乎找到了講“人之初”的依據,但是“性本善”呢 并沒有。孟子雖然說人與生俱來有這四種善心,并不等于說人與生俱來的都是善心,肯定“性有善”,并不等于否定性有惡。同時,孟子將這四心喻之為仁義禮智的“四端”。“四端”的“端”,是“萌芽”之義,孟子講這個萌芽還需后天擴而充之,“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這里講人若要成為“足以保四海”的大善需要助其善“萌芽”長大,用邏輯推理,那么人若成為“不足以事父母”的大惡,自然也是由于“惡萌芽”的長大。如果沒有“惡萌芽”,惡又從何處長起呢 雖然孟子關于“惡萌芽”在這段話中沒有說,但這應是不言自明的。由此看出孟子肯定人之初有“四心”,有“善性”,但并不是講初生時人性皆善。因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所以人對惡需要經常保持一種警覺。
荀子講“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個“偽”字考古發現意指“心為”。亦即人的本性是惡的,但通過后天的學習教育實踐是能夠向善、變善的。如何才能做到呢 就是“化性起偽”(心為),循“禮”而行。由此看出孟子、荀子的“善惡”之爭,一個強調“善性”是先天的,一個強調“善”是后天的。我以為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哲學語言來對孟子、荀子觀點進行比較與統合,這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康德的“道德律”指出,因為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你的行為準則要按照你同時認為也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法則去行動”(鄧曉芒著康德句讀)。這是一個定言命令(無條件的、絕對的、必然的、客觀的)。法則體現著對意志的命令,準則則體現著意志的選擇。定言命令表達的是當自身即為意圖目的而不是作為其他目的的手段時,與這個道德律令(絕對命令)相關聯的意志就只能是我們的善良意志。因為善良意志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如果立足于這點并擴展開,我們是否可以說因為孟子意識到仁、義、禮、智是作為人普遍接受的法則,從而人的“四心”行為準則要向這個法則看齊,而且這是自在的善,“四心”到“四端”是一種自律不是他律。只不過孟子沒用這些話去表達,他從“四心”“四端”是人與生俱來的,因而人應該“遵循”著這個自在的“善性”作為語言表達。我們同樣可以認為荀子的“化性起偽”也是看到人有自由意志(偽——心為),這個自由意志是能夠主導人去求善、向善的,人會在“心為”的實踐過程中,依“禮”而行的實踐過程中去惡從善。是否可以這樣講,因為孟子發現了他的“自在的善”的法則,從而強調自覺“遵循”;荀子則強調善通過依“禮”而行的實踐路徑去追求。我想如果讓康德來評價,他會說你們中國兩位圣人先我2000多年就已經有了這些思想“萌芽”,若要打分的話,孟子先生的“四心”“四端”更接近“道德律”的絕對命令,“吾從孟”。
我以為當下我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國學,并不是要“復古”,而是要用現代人的眼光去批判地揚棄,汲取其精華,樹立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馮友蘭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針對哲學領域的一些“偏向”,提出“抽象繼承法”。馮友蘭先生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命題,說:“過去我們說孔子這樣講有麻痹人民、緩和階級斗爭底意義。從具體意義看,可能有這樣的意義。但從抽象意義方面看,也是一種很好的待人接物底方法,我們現在還是可以用。”
我以為馮友蘭先生的這個觀點對于我們今天學習傳統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方法。不言而喻,古人講的許多話是在當時歷史環境下針對的具體人或事,這同今天已有很大不同。但是抽象地看,具體中蘊含著普遍性,沒有那時的具體就不能承載普遍,而普遍性又是對具體的本質規定。將這些普遍性“抽象”出來正是我們需要繼承的。由此再回到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惡”說。以今天的認知,我們知道“本心”是無善無惡的,我們對孟子、荀子其說既不能因此做簡單的否定,也不能簡單地釋義、重復或認同。要注意古人已意識到行善或作惡是能自主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人有自由意志,這種意志既可依照人的本能又可依據人的理性行事,不論是荀子的“化性起偽”還是孟子的“茍能充之”,都是在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所發揮的作用。再比如孔子講“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講的這個矩是指當時的“禮”,如果我們將孔子的這個“矩”抽象為一種行為約束,能看作是自由意志的絕對命令,是理性的“自律”(鄧曉芒著哲學起步),那么康德先生一定又會比孟子向前追溯200多年說“吾從孔”。
可以看出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對于我們在學習傳統文化、學習國學的過程中,跳出具體事、具體“言”,抽象提煉出普遍意義、普遍價值,具有其重要啟示。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原國有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