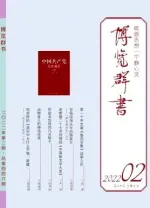我與《親吻世界——曼哈頓手記》
周勵

28年前,我出版了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在這本書的扉頁上我寫著:“此書謹獻給我的祖國,和能夠在困境中發現自身價值的人。”今天,我想把《親吻世界》獻給向往抵達世界各個角落,并探究其歷史真相、呼吁人類與世界和平的人們。
親愛的讀者,如果你愛好文學藝術和歷史,愛好戶外運動和探險,請與我同行——到一個與人類輝煌歷史進行對話的安靜世界去。我相信,你會因為心靈的盛宴而狂喜,因被天堂之光照射而陶醉,因與久違了的偉人相逢而重新喚起巨濤般的激情。
這本書是我在紐約疫情期間書寫和整理的作品,記得早春二月時,白天我與北美文友一起為武漢各醫院張羅募捐運送口罩防護服,晚上萬籟俱寂,我打開電腦開始寫作,時常心潮澎湃地寫到晨曦微露。直到窗外漸現萬道霞光,我依然沉浸在生命片段的回憶里。美國發生疫情紐約封城后,雖然每天憂心忡忡,但有了更充分的寫作時間。回想我在紐約從白天寫到黑夜,直到晨曦微露、霞光萬丈,陽臺下的公園大道空空蕩蕩,有時是救護車鳴笛而過,有時是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暴亂和示威隊伍穿行。門衛擔心示威隊伍會沖入大樓搶劫,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一邊見證動亂的紐約夏天,一邊寫作,有時是含著眼淚寫。
歌德曾懷著敬意把歷史稱為“上帝的神秘作坊”。時光荏苒,從1985年攜帶40美元赴美自費留學,至今我已在紐約生活了35年,親眼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崛起。曼哈頓有我的奮斗青春和燃情歲月。從曼哈頓出發,我追隨自己的夢想游歷了世界130多個國家,探險南極點、北極點,探索珠峰和攀登馬特洪峰。在風雪行旅和日夜兼程的難忘時光,那些歷史上撼人心弦的時刻,譬如斯科特和阿蒙森的南極點競賽,那些從希羅多德開始一代又一代歷史學家與探險家偉大的發現與不懈追求,一直激勵我前行。
《親吻世界——曼哈頓手記》由“被遺忘的煉獄:跳島戰役探險錄”“親吻世界:鐫刻在心靈巖洞上的壁畫”“燃情三極:南極點、北極點、珠峰逐夢”三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二戰歷史散文系列,主要根據近年來我對跳島戰役進行的實地考察而寫。說是探險,因為時而浮潛海底“戰爭墳墓”,時而須雇直升機或單人小飛機飛往小島,濃霧大風與突降暴雨都帶來心理挑戰,是名副其實的歷險記。我先后踏上了貝里琉島、塞班島、天寧島、關島、沖繩島、科雷吉多島、呂宋島等太平洋戰爭遺址,懷著震驚與感傷,我像考古學家一樣仔細發掘歷史上或有或無記載的實物與事件,并去華盛頓海軍陸戰隊硫磺島戰役博物館和美國國家檔案館考證核查,為的是探討戰爭原貌中的人性及狼性,有時甚至是人性至狼性的轉換,解開鏖戰殺戮背后不為人知的隱秘。六篇系列散文在微信公眾號陸續發表后,引起史學界和文學界人士的較大反響,他們驚訝我在貝里琉島戰役遺址發現的尼米茲石碑,同時因這塊石碑所揭示的“在敗者與煉獄面前,王者的謙虛、對失去生命的悲憫與對軍事專業領域勇猛同行的敬佩,都放射著人格與教養的魅力光芒”而深感震撼。
第二部分收錄了我在世界各地游歷的散文。其中《梵高的眼淚》《驚魂“歌詩達協和號”》《冰雪烈焰肯尼亞》《古巴奧德賽》《追逐日光》等各篇均為新冠疫情期間所寫。著名旅美作家盧新華在讀完《梵高的眼淚》后寫道:
這是一個滿懷激情的女作家在寫另一個被激情燃燒著的男畫家的美文——不是用筆,而是用心寫的。她是梵高隔世、隔種族、隔性別的知音……
也有部分文章如《尋找腓特烈大帝》《尋找伏爾泰》《尋找路易十四》《牢獄遺痕》等雖曾在舊作《曼哈頓情商》發表,但這十幾年我重新走了那些“尋找之地”,發掘了新的內容,增添了新的感受。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感言:“我的上帝!多么美好的文章,將歷史帶入生活!”
第三部分主要講述我的極地探險。我先后去過四次南極,三次北極,兩次馬特洪峰(一次攀登、一次飛越),兩次珠峰(一次巔頂航拍、一次攀登珠峰大本營)。我還有幸在南極認識了至今保持15次珠峰登頂世界紀錄的戴夫·哈恩,我們成為好友,在聯合冰川大帳篷的熊熊爐火前促膝傾談。
我喜歡雨果評論莎士比亞的名言:
誰要是提到“詩人”這兩個字,他也就必然是在談論歷史學家與哲學家。荷馬包含了希羅多德和達萊斯。莎士比亞就是三位一體的人。任何詩人身上都有一個反映鏡,這就是觀察,還有一個蓄存器,這便是熱情;由此便從他們的腦海里產生那些巨大的發光身影,這些身影永恒地照徹黑暗的人類長城。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用腳步去丈量、書寫非虛構文學,是時光歲月賜予我的禮物,也是冥冥之中我的文學使命。不久前我在大西洋航行,眺望藍色大海中灰色巖石的幽暗孤島——圣赫勒拿島,那是拿破侖流放和死亡之地,我想起拿破侖臨死前曾這樣寫信給兒子羅馬王:“希望我兒子能學習歷史,因為它是唯一真實的心理學和哲學。”
今天,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災難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也許我們正面臨著“百年之大變”的格局,面臨著更不確定的世界。但可以確定的是,人類面對著共同命運,當下的我們,更需要以史為鏡,以史為鑒,追逐夢想,親吻世界。
疫情期間,我與編者的交流只能通過網絡。在集中創作、修改的幾十天里,我總在大洋彼岸寫到清晨7點,文稿傳來正是上海的晚飯時間,我與編者匡志宏無縫對接,日以繼夜工作。《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是從自己出發,《親吻世界》則是對自我的超越。
35年前,當時35歲的我懷揣40美元,從上海踏上赴紐約州立大學自費留學之路。我根據自己從北大荒到曼哈頓的經歷寫成的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暢銷百萬冊,并獲《十月》文學獎,入選“90年代最具影響力文學作品”。35年后,在紐約疫情日益嚴峻之時,我向國內讀者交出了我近年所行所思所想的成果——新書《親吻世界——曼哈頓手記》。復旦大學教授李天綱說:“如果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是一部成功的自傳體小說的話,《親吻世界》則會是一部紀實性的史詩作品。”希望這部作品能夠給予讀者新的感受和思考。
(作者系美籍華裔作家,紐約美華文學藝術之友聯誼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