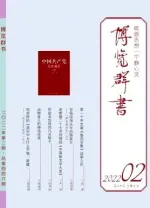為什么信任曹先擢

著名語言學家曹先擢先生1932年出生于浙江長興,于2018年11月7日在北京逝世。曹先擢先生生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歷任北大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國家語委秘書長、副主任,國家語委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辭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等。他胸懷天下,治學深受王力等語言學家的影響,在漢語文字、音韻、訓詁、語法、音義關系、辭書編纂、漢語規范化等方面都有很大貢獻;曾主持修訂《新華字典》、主持編纂《新華詞典》等辭書,擔任《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審定委員會主任,這些需要深湛而寬厚的功力才能做好而又意義重大的語文工作,曹先生都出色完成了,真正為提高全民族、全社會的語文水平作出了貢獻,使全社會受益。去年年底至今,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地,人們在病毒面前不斷反思,更加感到不尚虛談、不慕虛名、默默奉獻、腳踏實地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事業真正做出實績之可貴。曹先擢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身體力行的奮斗者。
—孫玉文(北京大學教授)
2004年,語信司決定成立一個專家工作組,繼續完成新的《規范漢字表》的后期工作,想讓我牽頭。我推諉再三,答應參加但不愿牽頭。我心里明白,規范漢字表的難度不在收字和整理,如果完全按照漢字規律來做這件事,應當不難完成。它的難度是在規范問題上見仁見智,眾口難調,協調才是最大的難度。我1983年正式調進北師大,此前與語言文字規范這個領域人不熟,事不經,說話沒有多少分量,協調工作恰恰是我不可能做好的。有一天下午散會后,曹先擢老師和我一起走出會議室,他把我叫到路邊說:“這件事你最好不要推脫,給國家辦事,自己不能沒有見解,但又不能堅持己見;不能沒人專門做事,又不能不讓大家一起做事。你有隊伍,有見解,有能力,我們也都會幫著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稀里糊涂接了這個差事,事后想來,曹先生的那番話在我心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2004年專家工作組在保定開第一次會議,我提出了繼續完成通用規范漢字表的三個主要原則,這三個原則是此后工作的綱領,我反復考慮,最后還是曹先擢老師幫我定下來的。那些年,許多難以協調的事,大部分是曹老師出主意,有時要靠他在會上最后的幾句話定奪。2006年通用規范漢字表(報批稿)專家委員會成立,我答應在北師大設一個研制組,有一點我是堅決的:“如果曹先擢先生作專家委員會主任,我可以跟著他來做具體工作。”《通用規范漢字表》研制前前后后12年,在教育部、語信語用司的直接領導下,多少人為之出力,我們做的那一部分都是學術技術工作,不過是協調一點就走一步,在這些問題上,曹先擢老師在很多問題的決定上,都是我們的主心骨。直到他生病在家休息,我還是習慣了遇到大難小坎兒,會去聽聽他的意見。這些年關于漢字規范,左的左,右的右,任何討論永遠無法說到一塊兒,曹先生卻一直在講規律,講字理,也講國家需要、社會實情。他做過語言文字工作,但不左;他信服《說文》,懂得字里乾坤,但不右;他編過不少字典,但不鉆在材料堆兒里;他熟悉文字改革,但沒有教條主義。和他一起工作,我有的是一種由信任產生的安全感。
我常常想,從青海回京之前,我并不認識先擢老師,對他的信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林林總總的大小事,一件件想起,在這里只說兩件事吧。
我認識曹先擢先生是一個意外的機會。1979年,我從青海文學藝術創作研究室借調到文化部,到北京第一件事是去前青廠看望陸宗達先生。非常巧的是,第一次去穎民師家里就遇到曹先擢先生,當時他還在組織編輯《新華詞典》,到穎民師那里是去商量詞典出版前的一些詞語解釋問題。讀研究生的時候沒有見過曹先生,穎民師忙著給我介紹,之后把曹先生提出的16個問題交給我去查驗,并讓我弄完后直接寄給曹先生。過了不久,我再次去前青廠,也把上次遵師囑寄給曹先生的問題抄給穎民師匯報。不料想穎民師拿出一套王力先生主編的《現代漢語》來對我說:“這是曹先擢老師寄來讓我轉給你的。”書里附了一封信,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古代漢語》四冊,請轉王寧同志,她是跟您專攻文字訓詁的研究生,學得這樣好,實在難得,千萬不可放棄專業轉行。”我才想起上次遇到曹先生時,曾說起我轉到文藝界7年的無奈和苦楚,曹先生一直惋惜,勸我盡快“歸隊”。那天還說起我們當研究生時,王力先生正在主編《古代漢語》,畢業時書還沒有出版。我和曹先生是第一次見面,對他來說,我還是陌生人,沒有想到曹先生卻聽進去了,他給我寄書的意思我都明白。穎民師讓我回歸的建議和這四本《古代漢語》,就是我一生抉擇的號令。
1985年,穎民師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先擢老師介紹一位他的學生過來,是一位人品、學識都很優秀的學生,穎民師欣然接受。過了一年,因為一件工作安排的事,產生了一點誤解,穎民師很不高興,我深知其中誤會,但無法說明原委。這時候,我第一個想起曹先生。那時曹先生已經調到國家語委和語用所,于是我匆匆忙忙去找他。去的時候,我心存卑微,十分忐忑。從第一次認識先擢老師后,我們只在會上見過面,他在主席臺上的時候多,幾乎沒有說過話。我想請他幫助這件事,其實與他關系不大。已經快到他的辦公室,我猶豫著沒有馬上進去。不料想曹先生聽到動靜卻迎出來,看見我也很意外。但他聽我說完這件事,卻很快地說:“我也好久沒見陸先生了,這件事我問問情況,我來辦。”過了幾天先擢老師果然到北師大來了。他說了一番話,問題也就解決了。我知道,穎民師通過編《新華詞典》的相處,對曹先生非常信任,不止一次談到他通情達理,待人誠懇,善于學習。但這屆研究生沒有畢業,潁民師就過世了。我又親自看到曹先生為這位學生安排工作。于是論文答辯的事,也就由我和曹先生一起安排了。那場博士論文答辯在語用所進行,但要由北師大組織,定下的評委名單里沒有我的名字,曹先生看到名單,一定要把我加進去。我一再請他不必麻煩,我說這是陸先生未盡的事,我來完成理所當然,到時候會來料理一切并辦手續,不必進評委會。他一定不肯,并且說:“這是原則問題,一定要辦到。”后來他是怎么辦到的我沒有問,但我內心卻是震動的。
時隔30年,曹先生已經故去,我的處境也已經有了些變化,然而人生百難,冷暖自知,人們往往不會記住應酬場合里的幾聲夸贊,卻會永生感念困境中的關照和微弱時的幫扶。也許正是許多類似的事情鏈接起來,讓我從內心感到了先擢老師的善良、公允、仁厚。
這些別人看起來不經意的小事,不但別人會認為微不足道,恐怕連曹先生自己也未必記得。我常常想:惡念總是刻意的酷想,而善意卻只是仁人的習慣,他們自己是不覺得也不會記得的。但這些事發生在我人生抉擇的路口,在我舉步維艱自信不足的情景下,卻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如今人雖遠去,德馨猶存,希望曹先擢老師一路走好。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語言文學藝術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