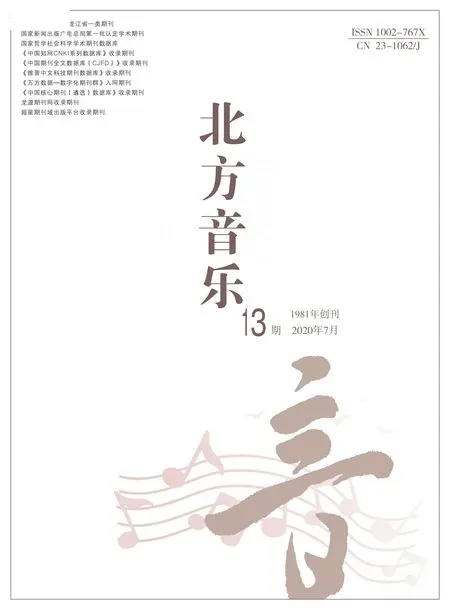“中為度,和為聲”
——試談中國傳統器樂演奏之“中和”美學思想
劉亞慧
(陜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中和”之美,不僅向來是中國傳統音樂創作的追求目標和審美需求,同時還是一種充滿哲學智慧的價值觀念。當今“中和”思想也隨處可以感知,人們經常把“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等俗語掛在嘴邊。2017年12月1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京召開,主旨為“美美與共,和而不同”,新聞報告指出,這是“蘊含中國智慧,彰顯中國理念的中國方案”,由此可以看出,“中和”觀念已經成為一種“中國標識”深入到絕大多數人心中。如果溯源它的思想基礎,其實是來源于儒家的“中庸”之道,孔子在講述中庸之道時就非常注重“和”,他主張人們應該擁有一種不偏不倚、有節有度、平和適中的處世態度,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人體和心理上的雙重平衡。下文筆者即以傳統器樂演奏中的普遍現象為中心,借以闡述中國人特有的“中和”之美學思想。
一、“中”:器樂演奏中的板式變化與變奏原則
古人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表現的是音樂內部一種和諧與適中并存的狀態。在中國人審美觀念范疇中,“中”代表“合度”“適可而止”,它的另一面“淫”則代表了“過度”、沒有節制,因此,“淫”所代表的音樂一定是無節無度,沒有規矩可言的“不入流”音樂;而在“中”思想指導下出現的音樂才是人們所崇尚的高雅正統之音,這種審美取向影響了數千年來中國一代代人的創作思想,它體現在方方面面。現以傳統器樂演奏中的板式變化和變奏原則為例進行說明:
(一)器樂演奏中的板式變化
板式,是一種在器樂和戲曲中專指節奏節拍的板眼形式,板式變化是以改變節奏、節拍、速度為核心而發展音樂的一種創作手法,例如陜北鼓樂的幾種典型結構:
1.引子(散板)-慢板-流水板-垛板-甲板-煞尾
2.引子(散板)-慢板-流水板-二流水-垛板-三流水-煞尾
3.引子(散板)-慢板-搶板-流水板-垛板-煞尾
4.引子(散板)-慢板-流水板-垛板-煞尾
其中散板沒有固定拍數,速度較為自由緩慢;慢板有固定拍數,速度一般為1分鐘36-56拍;流水板屬于快板,分鐘120-156拍;二流水比正常流水板再快一些,用在流水板之后;垛板比慢板速度稍微快一些,1分鐘80拍左右;搶板速度比慢板快一倍;甲板類似于我們熟知的“急板”,是一種特快的板式,速度在每分鐘180拍以上。將各個板式速度與上述陜北鼓樂板式套曲結構相結合,可以明顯看出它們之間速度調適的嚴謹性:慢板之后一般配以不同速度的快板銜接,緊接著用慢板形式或用更快板式來發展升華音樂,之后再出現與該板式速度相反的階段。
從陜北鼓樂套曲中各個板式銜接的嚴謹性可以看出,中國人音樂創作中有一種合“情”適“中”的思維,演奏速度要有節有度、合乎情理,如果板式進行一直都是快板且越來越快,這就會給人情緒或心理上造成不適反應,超過了人們承受和欣賞快板音樂的“度量范圍”,反之亦然,此乃“淫聲”。但凡事具有兩級性,“度”的嚴格遵守并不是要制約人們音樂創作的發展,使其固守某種觀念而不敢在有節制的范圍里去嘗試創造,人們感官的適應能力與審美能力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對音樂的審美感知能力可以隨著時間的發展而逐步提高,中國固定音階由五聲調式發展為七聲調式,就足以證明人不斷發展的審美感知能力和創造性。由此可以看出,“中”要求適中,反對過度也反對不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傳統音樂審美觀念——“中”的兩面性和完整性。
(二)器樂演奏中的變奏原則
“變奏”即為“變化演奏”,是我國民間發展音樂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變奏手法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一首曲調為母體的曲牌變奏手法;另一種是以某種板式為母體的板式變奏手法。
變奏中最根本的變化依據是“母體”形態,它可能是一個完整的曲牌、一個片段性的旋律甚至只是一種由幾個旋律骨干音構成的“曲調框架”;同樣在板式變奏手法中,“母體”所指就是變奏之前最初的音樂結構。筆者認為,母體形態是判定諸多變體音樂是否存在共性的基本標準,在中國人審美觀念維度里,母體形態為“中”和“度”,在“度”的范圍里,離母體形態越近的變體音樂其辨識度就會越高;反之,離母體形態較遠的變體音樂其辨識度相對較低,但仍能分辨出淵源關系,但如果超出了識別母體的衡量范圍,沒有了章法與規約任意變化器樂中母體曲牌和板式,失了“度”,也就失去了變化演奏的適“中”觀念。若后者音樂形態與前者音樂形態毫無關聯,那么“母體”就失去意義,“變奏”也相應失去了意義。因此,從器樂變奏手法中也可看出中國人對“度”的把握與衡量,與上文所述一樣,中國人進行多樣性變化的前提是保證音樂內部具有整體性和統一性。
二、“和”:器樂合奏中的組織形式和配器思維
“和”與“同”是中國音樂審美中又一對思想范疇。史伯著名的“和同”論認為君子應該“和而不同”“和實生物”且“異類相雜”,才能不斷衍生出新事物,若“以同裨同”,只有同類量的增多,則不會產生新事物。
晏嬰的“和同”論將音樂與烹調對應起來,揭示“和”的重要性。他認為“和如羹焉”,在烹調羹的過程中要注意將各種味道互相聯結起來,使之能夠相互吸收,最終“齊之以味”,也就是說烹調出的味道要有統一標準;同樣,“‘聲亦如味’則表明了音樂的和諧也是經由音樂內部諸要素之間圍繞某個正確的標準(具有‘中’的特征)而進行的同樣的交流轉化融合過程來達到的。”基于這種認識,我國傳統音樂的發展也主張“和六律以聰耳”“求和不求同”,它充分體現在器樂合奏中的組織形式和配器方面,如下:
(一)器樂合奏的組織形式
我國傳統器樂合奏的組織形式,按照其聲音大小和地域風格可細分為五種類型,分別是音響較大風格較為粗獷的“粗打”“粗吹”型樂隊,以及音響較小風格較為溫婉的“細打”“細吹”型樂隊,再有就是將擦奏樂器和彈奏樂器歸為一類的“弦索”類樂隊。
藝人們會根據樂隊的不同風格類型來對內部組織結構進行合理分配,比如鼓吹樂隊講究吹奏大于擊奏,所以在進行布局時要考慮到各種樂器音響效果,吹奏樂器可以多加幾件進行強調,而打擊樂器則可以適當減少以突出配合吹奏樂器為主;再比如絲竹樂隊強調“絲”與“竹”類樂器并重,但“絲”的音響效果在同等數量下弱于“竹”,于是,藝人們會增加“絲”類樂器并減少“竹”類樂器的使用,以平衡音響效果。因此,合理分配樂器在樂隊中的比重是樂隊音響效果和諧統一的重要手段。
(二)器樂合奏的配器思維
配器是從音色角度出發用以豐富音樂表現力的一種思維,樂器的音色最能夠體現出獨特性,但樂隊所追求的音響效果卻不是個性而是和諧,它要求在統一和諧的音樂風格下展開各個樂器間的對比交流,因此,要辯證統一的看待樂隊中不同樂器音色之間的協調和對比兩種關系:
面對同類或相似音色樂隊時,要注意本身自帶的協調性,著重加入對比性因素,例如鑼鼓樂隊擊奏部分,一般采用金屬樂器與非金屬樂器同時使用的方法,這樣豐富音色的同時還可以帶來聽覺上的變化;面對不同音色樂隊時,要著重在其中加入協調性音色調和極為突出的個性元素,例如“粗吹”與“粗打”兩類樂器音色對比較為強烈的樂隊,藝人們會分別在兩類中加入可以弱化二者之間沖突性的樂器,一般會在“粗吹”樂隊中用笙來削弱嗩吶、竹笛等一些明亮突出的音色個性,在“粗打”樂隊中加入一些材質為非金屬的樂器來淡化金屬樂器尖銳粗厲的聲音,這種做法既可以使音色對比強烈的雙方分別做出“讓步”,又可以豐富整個樂隊的組織結構,保證和諧統一下還具有多樣性表現,綜上可以看出,我國器樂合奏中無論是樂器數量的合理布局還是組織結構中的配器思維都具有強烈的“和”觀念。
三、“中和”:戲曲伴奏音樂
筆者認為在我國傳統器樂演奏形式中,最能代表“中和”之美的是戲曲伴奏樂隊,它在劇中氣氛、情感、人物唱腔等方面具有塑造功能,這種獨立性使唱腔一定程度依靠著伴奏音樂,要求樂隊演奏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同時還要高度配合唱腔音樂,協調好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系。例如京劇唱腔的發展與京胡之間的聯系,京胡本身結構導致里弦音色較難發出平穩聲音,因而里外弦的五度定音也不完全準確,但這正好成全了京劇唱腔風格獨特的“韻味兒”,以至于當今京胡在具備把音定準的情況下,考慮到對特定風格的追求,絕大多數琴師也仍然會將里弦空弦音調低,這種做法正是藝人思想觀念里對“中”的理解,也是對“度”的把握,即在不破壞音樂統一性的前提下,選擇一種符合聽眾和演員們審美觀念的做法。
另外,還有戲曲伴奏樂隊“引”“托”“送”“補”四種伴奏手法體現出的“中和”思想。例如“托”,專指“托腔保調”,有輔助演唱幫助演員固定音調之作用;“補”是“補”唱腔中間隙、停頓、換氣口等不足之處,借此來和諧音響效果、豐富音樂表現力。
四、結語
綜合我國傳統器樂演奏種種情況來看,“中和”審美觀念已深入人心。“中”是“和”的理性基礎,是體現音樂多樣性的前提方式;而“和”則是“中”的最高追求,是體現聲音效果統一性的重要考量,“中和”之美,就是將“中”所強調的“度”與“和”所講究音聲的“協調統一”辯證地、立體地結合起來,使之真正達到“美美與共,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