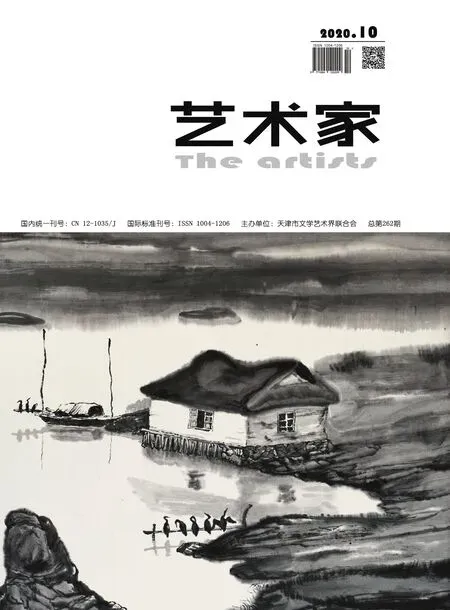淺評中譯本《論巴赫》—巴赫音樂語言中的圖畫性特點
□朱南亭 四川音樂學院音樂學系
巴赫的音樂到底應如何詮釋和理解?在巴赫音樂領域的著名研究學者阿爾伯特·施韋澤的《論巴赫》中,作者用自己獨特的觀點去詮釋和理解巴赫的音樂,并努力糾正大部分美學研究者固執的思維路徑[1]。此書雖出版于20 世紀,卻依然占據巴赫研究中重要的地位,值得我們細致評讀。
在探尋篇首問題的答案前,了解巴赫與美學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在第十九章中,施韋澤提到了“tonepainting”(聲音繪畫)、“ProgrammeMusic”(情節音樂)和“AbsoluteMusic”(純粹音樂)這三類音樂理論中本質性的概念。這三者之間存在相互聯系的邏輯性。“TonePainting”(聲音繪畫)強調的是用音樂來描繪事物,模仿繪畫這一概念。“ProgrammeMusic”(情節音樂)是音樂學界熟知的概念,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將此理解為“標題音樂”。但在本書中,“標題音樂”這一釋譯則顯得較為表面了。實際上,這類音樂強調的是敘述事件,隨著時間推移有序展開故事的情節,因此在這里譯為“情節音樂”最佳。“AbsoluteMusic”(純粹音樂)則處于“ProgrammeMusic”的對立面,這類音樂立足音樂本身,別無其他,因此是最純粹的音樂。而巴赫的音樂作品總是被片面地認為是“純粹音樂”的絕對代表。
而在《論巴赫》的第十九章與第二十章中,施韋澤將這三個美學概念放在一起,并反復提到“圖畫性音樂”這一術語,他強調巴赫音樂語言中圖畫性的特征。他在書中提到,圖畫性音樂本身就是一種古老的藝術。但以施韋澤的話來說“卻不完全是原始的”。這是因為,在巴赫之前的部分作曲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作品是在使用音樂表現一些不同的事物,如場景、行為和動作。他們也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創作行為跨越了純粹音樂的嚴格邊界。但除了這些無意識跨越邊界的作曲家們外,一些劇院中的作曲家則是刻意越過這樣一條邊界來進行創作,如漢堡劇院的作曲家們。他們為了增強戲劇化的表現力,有意識地用音樂來表現戲劇中需要體現的事件和人物。可以說,在他們的創作意識中,音樂可以再現戲劇中的重要關節,如人物的行為動作、每一幕的場景,甚至是人物的思想感情。
而巴赫與以上兩類作曲家截然不同。他明確了自己的創作目標——圖畫性的描繪及寫實主義,并在這個時代中目睹了這類音樂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最終成為集大成者。但這一現象在當時并沒有得到重視。如同看待上述兩類作曲家一般,人們只將其看作一種在純粹音樂邊界外稚嫩的玩鬧和暫時性的反常。筆者認為,美學家們對巴赫這些充滿“表現性”的音樂態度也是有據可循的。巴赫的前奏曲與賦格在他的創作生涯中可以作為一大典范且頻繁出現。因而,美學家們將巴赫的這類“純粹音樂”視為他音樂作品的“標準”,自然也就輕而易舉地撇開了巴赫這一反常的創作思維。
直到19 世紀后半葉,對此進行爭論的聲音才越發響亮,人們開始不情愿地承認巴赫的音樂的確存在圖畫性的特點。但人們對這一現象依舊保持熟視無睹的態度,并極力擁護巴赫作品中純粹音樂的特點,從而避免給巴赫扣上一頂“令純粹音樂淪為表現音樂”的帽子。施皮塔便是這一擁護者中的典范。而施韋澤在文中對施皮塔認為的觀念打上了引號。施皮塔的“巴赫藝術的正確理念”真的是正確的嗎?在施韋澤看來,施皮塔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對音樂唯物主義的畏懼。隨著時代的變遷,標題音樂給人們的聽覺帶來了強大的沖擊,無論是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還是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都讓人們眼前一亮。但依舊沒有太多音樂學家關注到巴赫康塔塔作品中那些“蘊含著戲劇性與圖畫性音樂”的蹤跡。美學家們亦是如此。對巴赫康塔塔的關注,實際上也是對音樂本質問題的專注。因此,施韋澤嚴肅地提出:美學最迫切的任務便是旋律創作的本質。他批評道:“我們的美學家們,并不從藝術作品本身出發。”在美學理論方面,繪畫藝術中的討論比音樂藝術中的討論更加激烈、全面和徹底。這也體現出,面對巴赫的作品時,或許我們的研究思路值得改變和完善。切忌在為了獲得“純粹音樂”的滿足后,刻意避免音樂中那些具有明顯表現性的音樂主題及描繪性和表現性的詞句。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巴赫是繪畫性音樂的代表,巴赫在創作時首先關注的是哪些場景可以用來作為他聲音繪畫的材料。
在第十九章的論述中,施韋澤試圖極力扭轉美學家們的研究思路,肯定巴赫音樂作品所蘊含的圖畫性,并對美學家們提出了嚴苛的要求。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后,施韋澤便大膽提出,巴赫的音樂除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征以外,還具有新潮的“現代性”。因此,他的音樂作品顯現出來圖畫性和表現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于巴赫圖畫性和表現性的雙重特征,施韋澤從藝術這個整體板塊入手進行論述。藝術家們的產物都是在選擇適合自己的“語言”后才創作出來的。其“語言”便是藝術表達的媒介。從繪畫、音樂,再到詩人,他們都在不同的領域對這一媒介做出抉擇,以達到更好的藝術效果。然而正是音樂藝術的綜合性導致“畫中本有詩,詩中本有畫”的現象出現。但這兩種不同性質藝術類別的融合,在不同比例的限制下會出現從“畫”過渡到“詩”的感受。這一看似復雜的過程就是巴赫作品雙重性的重要源頭。而人們對表現性音樂和圖畫性音樂有類似不可磨滅的質疑,實際上就是來源于對藝術的本質,即綜合性意識的缺失。他們在面對巴赫的作品時,從一而終地采用了“純粹音樂”的概念。因此,這樣的盲目使人們的視角變得更加狹窄。
但當人們認識到藝術的綜合性之后,便可將人們在面對音樂作品時所采用的接受方式引導得更為綜合。綜合的感知過程能夠更好地理解音樂作品的“弦外之音”。當人們有了完善的感知過程,音樂中象征的一系列含義也就油然而生。人們在欣賞音樂時,人類所具有的音樂感受力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我們對音樂進行想象的能力。而我們在音樂中感受到的方方面面就是作曲家們使用媒介符號表現出來的。施韋澤明確提出:“音樂的表達完全是象征的。”他認為情緒和思想與音樂中的某一特定的聲音是相對應的。
結語
施韋澤極力肯定了巴赫是圖畫性音樂的人物代表,他勇敢直面人們對圖畫性音樂的抵抗和質疑,力圖改變人們的美學觀念,將藝術的綜合本質展現給所有的音樂學家。實際上,在對這本書進行細讀時筆者發現,人們對巴赫的認知很容易產生施韋澤所提到的各種誤解,而這種種誤解或許源于我們沒有站在正確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如同施韋澤一再強調的,無論分析還是演奏巴赫的作品,都應認識巴赫獨特的音樂語言,并且要清晰地認識到,巴赫不僅在作品中顯露出圖像主義的傾向,而且追求一種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