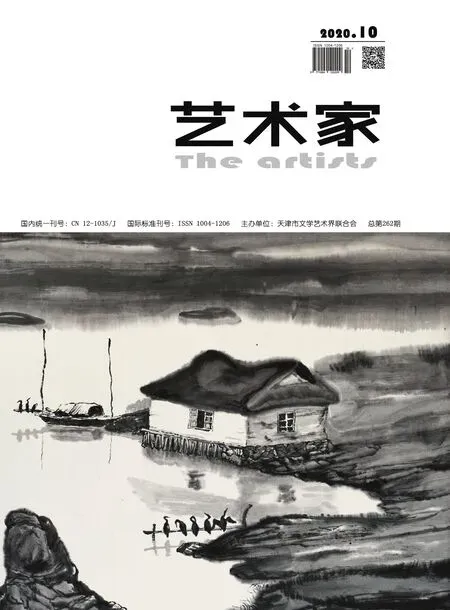《遺產風波》與西方視角下的印度
□鄭舒文 上海戲劇學院
從某種意義上說,《遺產風波》這部由加拿大印度裔導演于2007 年嘔心數載拍成的影片,并不是一部典型意義上的印度電影,那些歌舞歡言的場面,那些美好的巧笑娉婷,那些神話式歷史的自戀書寫,以及流動著寶萊塢風格的敘述模式,在這部電影中全部成為缺席的狀態。
如果將《遺產風波》與2008 年在美國上映的英國導演丹尼博伊爾執導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進行比較,或許我們可以更準確地感受和領悟里奇梅塔渴望異端化書寫印度現實社會和現狀的現實主義企圖。但在他努力將自己置身于印度社會底層中去體悟小人物生活的悲喜,并野心勃勃地采用記錄式的鏡頭語言再現真實場景的同時,是否真的有別于《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明顯的東方主義癥候呢?
在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中,東方永遠都是沉默、女性化、暴虐和貧困的形象,東方主義的東方是低于西方的“他者”,在《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象征著東方的“貧民窟”充滿原始的氣息,它貧窮落后,只有在西方“救世主”的形象出現后,利用科技和文明拯救東方,東方才會重現光明。與此相比,《遺產風波》與此意義并不相近。
主人公阿莫庫馬無疑是一個站在神壇上,擁有最質樸靈魂和處世真理的人(這一性格的產生,有一部分或絕大部分可以說是來自其父親的遺傳),女主角雖然有著一點小市民的計較,但也在更高層面上彰顯了人性的愛與無私。小女乞丐東方形象的塑造無疑是純真善良和光明的,與此同時,對于GK 的兒子尤里克,乞丐頭目乃至蘇雷叔的塑造則趨向貪婪、黑暗、爾虞我詐的一面。
在鏡頭語言方面,影片著力以嘟嘟車司機的視角來客觀真實地將現實的印度再現于銀幕之上。嘟嘟車黃綠相間的“前文明”身影出現于道路之間,破敗的低矮危樓與林立高聳的現代化建筑同時出現在觀眾的視野中。在這里導演毫無區別的眼光注視,異常冷靜與宏大。他沒有刻意避免刻畫印度臟亂的一面,而是在徹骨清醒的塵世鏡像下為我們建構起一座繁花似錦的圣城。導演力圖把印度的傳統與現代勾勒在同一張畫布上,不僅表現了這兩種文明之間的沖突,也表現了文明的和解與交融。
就像前文所說的,主人公性格是對其父的繼承,他身上體現著從父輩一代傳承的質樸的處世哲學,而那輛嘟嘟車則演變成這一權利的物質象征,也就是東方文化的象征。對于主人公性格的刻畫和描寫,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從一而終地對嘟嘟車事業的虔誠,在深層次則表現為導演的隱含意圖,即他對東方文化的不離不棄;其次,主人公對于小女孩的無私幫助,體現印度傳統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力量;最后,表現為主人公對金錢的不刻意和從容坦然。
而以尤里克為代表的西方則是失去基根的一代,父親遺產的拒絕繼承,正是這種無根性最直接的表現。在影片的最后,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成在經過東方與西方的交流活動或碰撞后,東方依舊東方,西方依舊西方。這似乎構成了對霍米巴巴的“模擬”的實踐,只是最后,東方和西方盡管涇渭分明,但都不再是最初的自己。基于前文對于人物形象、鏡頭語言及文本細讀后,我們可以認為該片開始在反東方主義和敘事話語中表現出難得的先鋒性,成為第三世界電影里強有力的聲音。
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衡量,里奇梅塔的《遺產風波》是否突破了長久以來東方主義的窠臼,這的確是一個亟待思考的問題。首先從影片的另一個譯名《窮得只剩下錢》來看,省略的主語是西方,所以我們可以將其看成一部資本主義殖民者進行自我反思的影片,而導演里奇梅塔便是被第一世界意識形態所詢喚成功了的“前印度人”,他憑借這樣一種含混與曖昧的身份,企圖表達殖民地人們的生活現實。在影片中,他對印度人進行非真實的想象、主人公的神化,這種無根性即意味著在人物塑造上的現實割裂;而他對改良主義的殖民者則持一種明朗的贊揚或至少是同情的態度,這種中產階級立場的同質性,使得諸如對蘇雷叔、GK 等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物塑造入木三分。這無疑構成了一個頗有意味的悖論。
如果我們從電影開放性的結尾來看,那些開始力圖學習和平等對待“東方”的“西方人”無一不是以死亡終結,而毫無此意識的尤里克則成為財富的繼承者。這里的財富代表一種權利的象征,而“東方”只能因其無知(不識字)、科學性的匱乏而喪失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權利。由此可見,西方殖民者的存在是毫無協商姿態的,就像阿莫對普嘉說的:“這個星期,我搭了捷運,一切都在改變,當這輛車開不動了,我可能要去買部計程車。”在這種殖民化的進程中,“東方”只能作為被動接受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