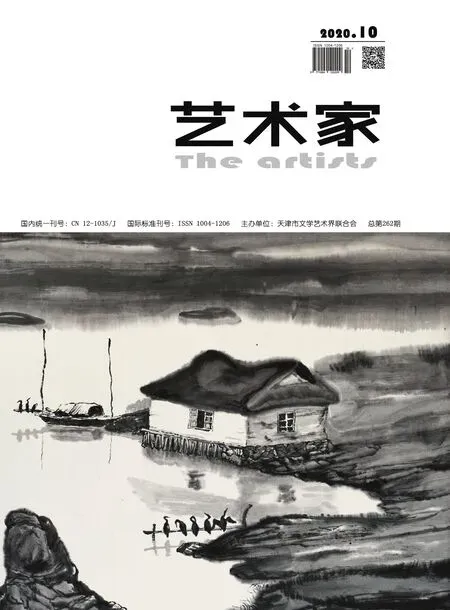從項陽《山西樂戶研究》看民族音樂學(xué)對中國音樂史研究的意義
□烏肖靈 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
一、山西樂戶概述
《山西樂戶研究》是項陽老師的研究成果,他到民間實地考察,發(fā)現(xiàn)一位民間藝人自稱張居正的后人,還有族譜記錄,自此發(fā)現(xiàn)樂戶這一特殊群體的存在。他先后查閱200多種書籍、近百余種相關(guān)文獻(xiàn)資料并做10 萬余字的讀書筆記,走訪山西數(shù)個村落,以夯實的案頭工作與扎實的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資料完成了這本體現(xiàn)多學(xué)科、多視角、全方位、具有時代意義的著作,彌補了歷代文獻(xiàn)中沒有記載的樂籍制度的存在。
山西是樂戶的主要發(fā)源地,歷代分封的藩王與軍旅樂籍中在籍的樂人,在客觀上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雖制度本身存在很殘酷的問題,但將各地的人與其地的音樂文化帶到山西,間接地保護了音樂文化流傳發(fā)展的完整性。
二、民族音樂學(xué)的發(fā)展
“民族音樂學(xué)”一詞最早見于20 世紀(jì)70 年代音樂學(xué)中文資料翻譯中,20 世紀(jì)80 年代以后,民族音樂學(xué)進(jìn)入我國。首次“全國民族音樂學(xué)學(xué)術(shù)研討會”于1980年6月在南京召開,標(biāo)志著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在中國興起,逐漸確立在音樂學(xué)領(lǐng)域的分支學(xué)科地位。《山西樂戶研究》注重對主體觀的把握與多學(xué)科交叉滲透研究方法的運用,并對其進(jìn)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在調(diào)整知識結(jié)構(gòu)、梳理文獻(xiàn)、建立“歷時觀念”的基礎(chǔ)上,與音樂史學(xué)相結(jié)合的學(xué)術(shù)理念,以縱向歷時性與橫向共時性相結(jié)合的角度對多種音聲之活態(tài)存在進(jìn)行實地考察與辨析。以現(xiàn)存音樂文化進(jìn)行逆向考察,符合民族音樂學(xué)中縱向“歷時”觀的思維,能引導(dǎo)研究者注重其縱向的歷時發(fā)展過程,認(rèn)識到它是持續(xù)存在的音樂形式,追溯歷史的發(fā)展蹤跡來解釋說明它的現(xiàn)實存在與變遷。任何一種音樂事象的顯現(xiàn),都包含著歷時構(gòu)成和共時構(gòu)成兩個方面,橫向“共時”觀是對其“現(xiàn)時構(gòu)成”的考察與研究,了解其與外部環(huán)境之間的聯(lián)系,與其他同時代音樂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與影響,都能幫助研究者全方位地深入研究樂戶和樂籍制度的存在、變遷與發(fā)展。
三、民族音樂學(xué)對中國音樂史研究的意義
(一)可以從理論上豐富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
民族音樂學(xué)不是一種純技術(shù)性的音樂理論學(xué)科,其在對象范圍和目的上偏重于音樂人為內(nèi)容的研究,對技術(shù)性音樂理論起到補充、擴展的作用,可進(jìn)一步幫助研究者從更為廣闊的人文背景中,加深對所研究的音樂事象的理解和認(rèn)識,可更全面、準(zhǔn)確地把握音樂本體及現(xiàn)象的歷史性、現(xiàn)實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全方位完整的學(xué)科性質(zhì)是其不同于其他學(xué)科的獨有的特色。
民族音樂學(xué)在發(fā)展過程中同許多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其他分支學(xué)科都發(fā)生著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其中與之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是民族學(xué)、民俗學(xué)、地理學(xué)和語言學(xué)等學(xué)科,不僅要結(jié)合音樂學(xué)中其他分支學(xué)科的方法論觀念,還著重借鑒民族音樂學(xué)與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非音樂理論學(xué)科之間的關(guān)系,來作為實際田野調(diào)查中的理論基礎(chǔ)。多學(xué)科之間的交流借鑒及影響是雙向的,注重主體觀及多學(xué)科交叉滲透的研究方式,可以從理論上促進(jìn)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展。
(二)可以彌補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空白
《山西樂戶研究》以現(xiàn)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通過對其現(xiàn)存音樂文化的逆向考察,梳理出承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樂籍制度;運用多學(xué)科交叉視角、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的指導(dǎo),厘清中國封建社會在一個相當(dāng)漫長的歷史時期的現(xiàn)實存在的音樂文化群體,彌補了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空白。輪值輪訓(xùn)制是樂戶對音樂文化的重要貢獻(xiàn)之一,它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主脈傳承之所在,我國音樂文化從賈湖骨笛的出土可證至八千年前,發(fā)展至今從未缺失或斷層,正是得益于這一制度既封閉又開放的特點,其結(jié)構(gòu)與組織既嚴(yán)密又相對松散,使宮廷、民間上下一致、上行下效,無論雅樂、禮儀鼓吹,還是筵席俗樂,均是一脈相承,同時,它也決定了我國音樂文化發(fā)展的歷史走向。
(三)有益于研究傳承保護非遺文化
人們對樂籍制度的研究,對整個中國音樂史會有更加清晰深刻的把握,從宮廷、王府到地方官府,乃至軍旅和寺廟音樂文化的一致性,都使我們對音樂形態(tài)脈絡(luò)的認(rèn)識漸漸清晰起來。許多我們以為已經(jīng)失傳的宮廷音樂,其實都可以從現(xiàn)存民間的音樂中找到;許多我們向來以為是俗樂的東西,其實很可能是當(dāng)年宮廷中的雅樂。樂戶雖然從人格上忍受著社會的不公,但正是他們以其獨特的方式、精湛的技藝?yán)^承保護了中國傳統(tǒng)的音樂與戲曲文化,較完整地保留了我國傳統(tǒng)的音樂文化,并決定著整個中國音樂發(fā)展的歷史趨向。我們應(yīng)將其落實到當(dāng)下存在的音樂現(xiàn)象中加以研究,如非遺傳承等,將更多特有的、活態(tài)的音樂文化以更好的形式保護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