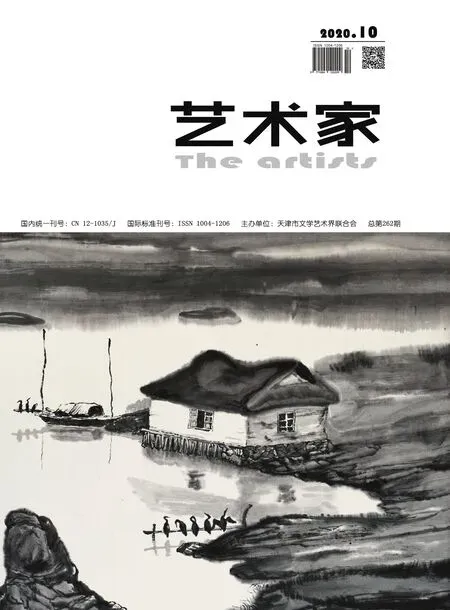從“白日夢”到創(chuàng)作—以青年藝術(shù)家胡佳藝為例的創(chuàng)作心理分析
□葉 舟 四川美術(shù)學(xué)院
潛意識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一直以來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弗洛伊德的論文《創(chuàng)造性作家與白日夢》中提出,人的一切動機都來源于無意識的本能欲望。人從小就會產(chǎn)生無意識幻想,弗洛伊德認為,無意識幻想是為了滿足未實現(xiàn)的愿望而產(chǎn)生的。成年人往往羞于提起關(guān)于自身的白日夢幻想,但是創(chuàng)作家、藝術(shù)家可以通過藝術(shù)的形式將這些幻想表達出來,并且不會讓觀看者感到不適。這一條路徑究竟是如何發(fā)生的呢?筆者通過對青年藝術(shù)家的采訪,得出了一些答案。
一、從童年經(jīng)歷中尋找創(chuàng)作動機
在開始探討這個問題時要大膽假設(shè),早在弗洛伊德1908年發(fā)表的論文《創(chuàng)造性作家與白日夢》中,就提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靈感應(yīng)在童年中尋找。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有很多相同之處,在論文《一篇啟發(fā)世人的杰作》中,作者馬科斯提出,可以沿著弗洛伊德的方向做更進一步的探索:首先,將精神分析應(yīng)用到藝術(shù)家與藝術(shù)家領(lǐng)域的方法學(xué)問題上。其次,難以言喻的心靈產(chǎn)物具有錯綜復(fù)雜的身份,如波濤洶涌一般從心靈內(nèi)部涌出。創(chuàng)造性作家與藝術(shù)家有一定的相同之處,二者都是文藝工作者,要靠創(chuàng)作產(chǎn)出作品。
青年藝術(shù)家胡佳藝的作品《除夕守夜》的創(chuàng)作背景是2015 年新疆持續(xù)發(fā)生暴力恐怖事件。胡佳藝以往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圍繞著家鄉(xiāng)與自己家人的故事進行創(chuàng)作的。在《除夕守夜》中,胡佳藝拿著槍站在家鄉(xiāng)的湖邊,一個看起來并不是那么強大的女孩子以一種堅毅的姿態(tài)拿著槍守護著家鄉(xiāng),這本身就是充滿了矛盾感的畫面。筆者問她怎么會想到呈現(xiàn)一個這樣的作品,她說:“我的出生地是新疆吐魯番葡萄溝,2015 年新疆發(fā)生暴力恐怖事件,其實在除夕的晚上出去是非常危險的。當時姥爺病危,家里沒有聚在一起過年,所以也得以在團聚日溜出家。”從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不僅是她,她的家人自我保護的意識也非常強,當然這也受到了當?shù)靥厥猸h(huán)境的影響。胡佳藝從小在這種氛圍中長大,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也就是說,藝術(shù)家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搜集、處理、刪節(jié)、修飾并節(jié)錄了自己的記憶,從而能夠創(chuàng)作出作品。筆者問了藝術(shù)家本人對這種創(chuàng)作動機的分析的看法,她說:“我在不了解這些原理之前,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現(xiàn)在回想起來,其實肯定是受到了童年經(jīng)歷的影響,并且恰好遇上類似的事件,所有的情感都一下子在作品中表現(xiàn)了出來。”
二、強迫性暗喻的覺察闡明作者的無意識層面
弗洛伊德認為,在心理小說中,作者并沒有從一個主人公沖動的滿足感中得到他本質(zhì)的滿足感,而是形成了一個身份認同。現(xiàn)代作者可能會將他的自我分裂成幾個部分。這幾個部分被賦予了其作品中的多個角色,并且將他自己生活中沖突的議題“擬人化”了。這個機制近似做夢者使用的方式,他們以替換和濃縮來表達自己潛在的想法,借此有條理的方法滿足愿望的沖動。我們從胡佳藝的作品《達利的胡子》能夠發(fā)現(xiàn)她的一些暗喻。
《達利的胡子》確實是和達利的胡子有關(guān)的一個作品,胡佳藝將陰毛經(jīng)過處理后制作成了達利的胡子。在以往的報道中,有人問過:“使用這種材料是否為了產(chǎn)生極度私密的相遇?”她否認了這種說法。筆者也問過有關(guān)這個材料的問題,她告訴筆者:“最早并沒有用這個材料的想法。甚至以前也沒有觀察過陰毛,只是一次偶然的機會,觀察到這其實是挺可愛的存在,就產(chǎn)生了做這個作品的想法。”一開始,她還嘗試過用胡子膠和蠟打理成達利的胡子的原始形狀,但沒有做成;又用燙頭發(fā)的夾板和熨斗企圖把陰毛拉直后再固定,也沒有做成。陰毛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倔強,所以就讓它毫無保留地呈現(xiàn)原始狀態(tài):偏硬的,卷曲的。筆者也問過,她為什么會選擇以達利為原型來做這個作品。她說,她認為達利在她心中是一個很酷的藝術(shù)家,并且達利的胡子是他的一個標志。她喜歡達利對自己的作品要求苛刻,喜歡他的偏執(zhí),甚至狂傲。他的這些特質(zhì),讓胡佳藝覺得達利是最適合呈現(xiàn)這個作品的藝術(shù)家。弗洛伊德認為,小說中英雄式的主角其實反映了“唯我獨尊的自我”,也可以說是移情的外射。那么,可以大膽假設(shè),胡佳藝之所以會選擇以達利為原型做這個作品,是因為她將自己對達利的欣賞投射到了作品上,希望通過作品讓“觀念性的自我”流連和沉沒在對對象的關(guān)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