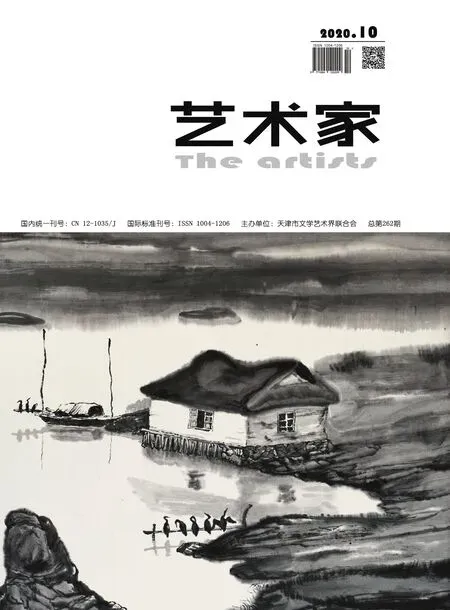縱橫交匯 通達文藝—當代文藝理論研究漫談
□張旭耀 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談及文藝理論,人們腦海中立刻就會閃現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等一大批經典的傳統文學思想和文學大師的形象,就近百年來看,都可謂思潮迭起、精彩紛呈。從文藝思想來看,先后興起過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兩大巨浪思潮,這兩座豐碑至今仍然讓人高山仰止;從文藝研究的重心來看,也是風起云涌、起伏不斷,出現過從創作者到作品文本的轉移、從作品文本到讀者和接受程度的轉移。與此同時,對于文藝作品的研究,也曾經出現過對語言論的轉向和非理性的轉向兩大陣營,其中涌現出如象征主義、表現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數十種文藝批評的流派。因此,當我們在回看文藝理論的演進變遷歷程時,不禁感到風云激蕩、高潮迭起,同時也難免有一種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之惑。
南帆先生在其大作《文學理論》中說道:“文學是什么?一旦受到文學的吸引,對諸多問題的探究就會接踵而至:作家、文本、文類、敘事與抒情、修辭以及文學與歷史、宗教、民族、地域、道德、性別之間的種種聯系。這一切如何組織起來,從而產生非凡的魔力,以至于令人如癡如醉?這是文學理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這些問題得到了初步的答案后,人們就有條件‘登堂入室’,進行更為專業化的考察。這時,文學史、文學理論史上的一批重要概念及各種文學批評流派的特征將會逐漸進入視野。顯然,對每一個概念的考證或者對一個批評流派的描述,背后都隱藏著寬闊的研究領域。”[1]南帆先生研究文學理論的格局開闊、視角獨特,總能化繁為簡、切中筋脈,猶如庖丁解牛一樣精深解析、干凈利落。《文學理論》從“文學是什么”“如何研究文學”兩個基本問題出發來探討文藝研究,闡釋了文學創作者、作品文本、敘事風格與抒情手法、語言修辭等內容,同時對文學作品與社會文化(如歷史、宗教、民族、地域等)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還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新時代下文學中經典作品與讀者接受欣賞的問題。掩卷沉思、反觀當下,恢宏耀眼的工業文明漸行漸遠,信息技術革命營造出來的絢麗景觀不覺間已經將我們吞噬,那么,我們該如何從容應付當下及未來的文藝研究?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橫向分析
研究者必須打通文藝理論要點與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銜接,緊密關注其間的互動變化。
回看20世紀的西方文藝理論不難發現,大多文藝思潮或直接基于某些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理論產生,或與其他理論背景相衍相生、交織依存。存在主義哲學的一代大師海德格爾,為后人描繪了“詩意地棲居”的唯美境界,并一直極力倡導并推崇“藝術讓真理敞開”。而波蘭哲學家英伽登的現象學文論,可以說是建立在以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和“懸置”的方法上,以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期待視野”等理論為營養,是第一個系統深入地建立現象學、美學的文藝理論家,他也極大地推動并催生了伊瑟爾等人的接受美學理論。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獨樹一幟,其理論體系中所闡述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組成的人格整體,纏綿交錯、共存互生、相互使用,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人類行為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與此同時,該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又與人類行為中所遵循的快樂原則、現實原則和理想原則相對應。而要想真正體會榮格“原型”理論中的“分析心理學”的“原始意象”“自主情結”等內容,或許可以考慮從弗洛伊德個人“潛意識”理論出發,引進“集體無意識”的概念,那么一切就會更通透。羅蘭·巴特說:“從每個故事里抽取出它的模型,以這些模型再建立一個巨大的敘述結構,然后(為了驗證)又回到任何一部作品上去:這件任務使人筋疲力盡,而且索然寡味,因為文本因此而失去了差異。”風格鮮明地表達了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反思。而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則明確反對語言中心主義,其解構主義的文學新論極大地動搖了傳統人文科學的基礎,是構成整個后現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論源泉之一。德里達認為,“所指”的世界構成一個流動的意義指涉過程,是不確定的,存在任意性、差別性。“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延異”(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蹤跡”(trace)等新詞都極具德里達特色。
由此可以看出,文藝研究早已不能只囿于自身理論及作品本身,其與社會文化的生態樣貌、周邊學科的思想流轉及相互關聯都應該密切關注,尤其是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對文藝研究的進化發展意義重大。
二、縱向分析
研究者必須厘清文藝理論各流派的生演脈絡、起承轉合,明晰文藝嬗變的聯通點。
首先,20 世紀初的傳統文論認為,作品內容和形式是可以分別討論的,然而此二分法受到了形式主義文論的顛覆。什克羅夫斯基在《詞的復活》中對“陌生化”的考察研究,雅各布森等對隱喻和換喻的深入探索,掀起了形式主義文論的浪潮。他們認為,文學形式是作品中各部分之間關系形成的系統,形式與形式之間相互依存、不可分離,而傳統意義上的作品內容如情節走向、人物脈絡等,都是形式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歐美相繼出現的文論新批評及結構主義文論傾向,則是形式主義文論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入。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陌生化”理論又充分吸收了形式主義文論的精華,同時也深受黑格爾的異化理論及辯證法的影響,融合了馬克思文藝理論的審美反應論。他極力倡導在戲劇創作中融入文學敘事的手法,讓觀眾看戲但并不融入劇情,達到以“第三者”的身份來進行理性體察的間離效果(defamiliarizationeffect)。雅各布森的隱喻和換喻,則跟漢語中的比喻和借代有異曲同工之處,但仔細體味又并非完全一致。
再次,馬克思主義文論基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這兩個全新維度,從二者關系出發來思考文學的意識形態性,突出放大了文學的能動功能,其理論觀點大多是夾揉著馬列經典學說、心理分析學說、存在主義等流派,再結合當下社會現狀進行探索。在深入了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過程中,隱隱能夠體察到“人的異化勞動”“國家機器”“藝術生產”以及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的味道。馬克思認為,文藝創作起初應該是源于人類勞動,而另一位學者盧卡奇卻說:“原始社會里,人的勞動和巫術一起,推動了藝術的出現。”[2]仔細分析就會明白,盧卡奇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基礎上融入了賴納等人關于藝術的巫術起源的觀點,是對馬克思的文藝勞動起源說的豐富和完善。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之一的馬爾庫塞,極力批判資本主義“消費控制”把人變成“單向度的人”,也是受到馬列學說中“人的異化”理論的極大影響。但是,馬爾庫塞過度夸大了藝術的功能,聲稱藝術的本質是“革命”,認為文藝作品能夠創造“新感性”,顯得有些過激。
最后,到了瓦爾特·本雅明那里,古典藝術的“獨特性”被放大,甚至被賦予某種“膜拜價值”,而當代文藝作品的“展示價值”更為凸顯,更具親民普世性。工業文明下機器復制時代的呼嘯而至,極大地推動了古典藝術的大行其道。本雅明的觀點是結合社會發展現狀對藝術形態的客觀判斷,但也能夠發現其中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的“二重性”理論對他的啟發和影響。現象學文論家伽達默爾,則主張無論當代藝術還是古典藝術,其根基都源自人類交往共在的原始本能,他試圖鑿通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壁壘。當代藝術極力拉近甚至湮滅存在于觀眾、讀者與藝術作品之間的隔閡或對立,試圖讓觀看者和創作者直接對話,為當代藝術尋找合法性,其中不免有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在現實條件下激起的深度反思[3]。
近年來,在經歷了文本轉向、讀者轉向后,文論界又出現了傳播學轉向,同時文藝理論中出現的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等傾向無不呈現反中心化、反確定性的特質。由此可見,對先賢高論的起承轉合的清晰了解,將更有助于精準把握文藝研究的生相脈動,以強勁的生命力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結語
而今,面對紛亂復雜的社會環境,我們更需要對各類思潮流派、先鋒觀念的演變脈絡有所了解,明晰各階段文藝嬗變的拐點,以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關聯互動,這樣才能在未來的文藝研究中做到游刃有余、有的放矢,透過迷霧看清本質并把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