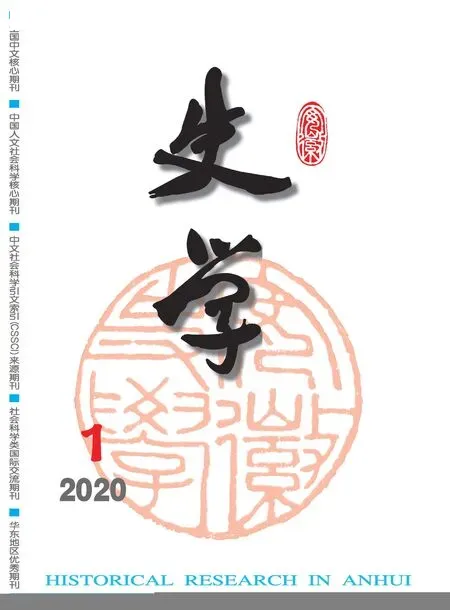從家訓文獻看晚明士大夫的治家認識
——以方弘靜《家訓》為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傳統中國家訓主要用于訓示、教誡子孫,以治理家政,進而服務于平天下的最終目標。故而,家訓文獻必須具備足夠的權威、具體的目標和相應的手段。這些內容直接反映出家訓作者對于家庭治理的認識,它們不僅會受到之前經典家訓文本的影響,還有著家訓產生時代的烙印。盡管家訓作者身份具有足夠的權威,或者使用家譜、鄉約等特殊文本闡述家訓時,個人或文本會直接提供家訓所需要的治家權威,家訓作者會側重于闡述后兩部分,而弱化前者,但削弱并不意味著消失,三者共存仍是現存家訓文獻當中的普遍現象。
就傳統中國家訓發展史而言,明清時期產出了大量的相關文獻,細觀其中脈絡,可發現明清家訓的盛況肇始于明嘉靖朝。以數量論,依照相關學者的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共有相關家訓文獻238種,而在37種明代家訓中,僅有6種成書于嘉靖之前。(1)陸睿:《明清家訓文獻考論》,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就作者身份而言,大部分均出自于士大夫之手。家訓文獻的龐大規模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產生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2)陳延斌:《試論明清家訓的發展及其教化實踐》,《齊魯學刊》2003年第1期;王雪萍:《明清家訓中馭婢言論的歷史解讀》,《史學月刊》2007年第3期;陳時龍:《論六諭和明清族規家訓》,《安徽史學》2017年第6期。但學者大多關注家訓文獻的內容、特征及體現出的價值觀,對于文本所反映的作者意圖及其與當時社會的關聯則討論較少。在31種晚明家訓當中,方弘靜所撰的《家訓》體量較大,涉及范圍較寬,在具有時代共性的同時,也有著自身的特殊之處,成為討論上述問題的一個范本。正緣于此,本文以晚明士大夫方弘靜所撰《家訓》為中心,討論其中的治家觀念,進而從另一個側面探討時代變遷與家訓撰述間的關系。
一、方弘靜生平及其《家訓》
方弘靜(1517—1611年),字定之,號采山,南直隸徽州府歙縣巖鎮人。關于其人之生平,已有數
位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3)韓開元:《詩人方弘靜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邱仲麟:《金錢、欲望與世道——方弘靜論嘉萬之間的社會風氣變遷》,《東吳歷史學報》第28期,2013年。,在此不一一贅述,僅舉其生平部分特點予以論說。首先論及出身與生活時代。方弘靜從屬于歙縣方氏環巖派中川門,此族在明清時期商賈迭出,乃是歙縣大族之一。(4)唐力行:《徽州方氏與社會變遷——兼論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韓]樸元鎬:《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時代徽州的市鎮與宗族——歙縣巖鎮和柳山方氏環巖派》,《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至于其家庭,同樣是數輩經商,曾祖方茂富,長期在外經商,至中年時,方才多有積蓄,并回鄉定居,留次子京生“屏侍于內”,長子泰孫與三子齊孫繼續“殖生于外”。(5)方弘靜:《素園存稿》卷20《譜略·譜傳述論·德潤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1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63頁。泰孫便是方弘靜的祖父,其長期在山東經商,“累金至巨萬”,并在當地結交士人,之后“挾重資”回鄉,屢行善事,時人尊之為“英達長者”。(6)方弘靜:《素園存稿》卷20《譜略·譜傳述論·通議公》,第366頁。至弘靜父親方虎,同樣早年在外經商,中年后又轉而學醫、習儒,“出入醫賈,卒歸于儒”。(7)吳子玉:《大鄣山人集》卷53《祭方小春先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1冊,第851—852頁。弘靜生于明正德十二年,卒于萬歷三十九年,享年九十五歲,實屬長壽。正德至萬歷年間,正是明代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的時刻,社風、世情均有著急劇的變化。(8)陳寶良:《明代社會與文化的演變》,《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3期。而方弘靜逝世前后,又是明代國家轉至衰亡之時,三十余年后,明亡清興,政權更迭,社會又再次出現較大的轉變。
再次論述個人生涯。方弘靜的人生可以中式與致仕兩個時間節點分為三個階段。登科之前,方弘靜長期鄉居,為縣學生員,并逐漸在當地文壇展現聲名,二十六歲時,與程誥、王寅、陳有守等人創立徽州著名詩社天都社。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方弘靜考中舉人,四年后,參加會試,名列二甲第八名,時年三十四歲。(9)韓開元:《方弘靜年譜》,《徽學》第3卷,2004年。此后,方弘靜開始了長期的官宦生涯,先后歷任多地不同官階文武職位十數種,只是未曾任職于中央,其間亦有部分年歲去職在鄉。在七十三歲時,即萬歷十七年(1589年),以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南京糧儲職位致仕。(10)顧起元:《懶真草堂集》卷28下《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采山方公行狀》,《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68冊,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頁;葉向高:《蒼霞續草》卷11《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方公墓志銘》,《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2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3頁。離任五年之后,方弘靜回到家鄉歙縣,除偶有外出,直至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卒,在鄉時間竟達二十二年之久,并于四年后,詔贈南京工部尚書。(11)《明神宗實錄》卷530,萬歷四十三年三月丙辰,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實錄》校印本1962年版,第9973頁。
最后闡述其人身份。從方弘靜的人生經歷來看,其屬于典型的傳統官僚。而在官宦生涯之外,弘靜同樣有著相當長的鄉居生活,這使得他又具有了鄉紳之身份。(12)關于鄉紳的定義,參見徐茂明:《明清以來鄉紳、紳士與士紳諸概念辨析》,《蘇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在兩種身份之外,方弘靜還是當時有名的詩人,他年少時便偏愛詩文,“余總角則從先元兄習舉子業。舉子所業在章句、訓詁,不得泛及藝苑,乃元兄所誦習者,皆周漢以前古文詞也,余時竊窺而喜之”(13)方弘靜:《素園存稿·素園存稿自序》,第13頁。,以至于在李維禎筆下,他乃是“少即以詩文著聲”。(14)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卷17《〈方少司徒年譜〉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冊,第675頁。方弘靜所撰之詩,在當時與后世皆有較佳的評價,時人袁宏道稱之為,“有長慶之實,無其俗;有濂洛之理,無其腐,質在是矣。”(15)袁宏道:《行〈素園存稿〉引》,方弘靜:《素園存稿》,第8頁。錢謙益《列朝詩集》摘其詩三首,并援引王寅所言:“定之抱性幽閑溫秀,故其修詞吐氣有似于人……宛然王孟遺響也”。(16)錢謙益:《列朝詩》丁集卷3《方侍郎弘靜》,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171頁。總而言之,方弘靜的身份多樣,但可被歸入士大夫群體當中。(17)陳寶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頁。
方弘靜一生留有著作多種,以《素園存稿》與《千一錄》兩種最為重要,前者是詩文集,后者則屬于雜俎,而《家訓》便是錄于此書當中。《千一錄》始撰于鄖陽巡撫任上,最終在方弘靜致仕鄉居后成書,歷時長達十四年之久。(18)方弘靜:《千一錄·千一錄自序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1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頁。全書分為五個部分,卷一至四為《經解》,卷五到八為《子評》,卷九至十二是《詩釋》,卷十三至二十二為《客談》,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即是《家訓》。其后不久,此四卷《家訓》被何偉然刪減后以《燕貽法錄》為名,納入《快廣書》當中。(19)方弘靜:《燕貽法錄》,《叢書集成續編》,上海書店1995年版,第473—486頁。就收錄于《千一錄》中的《家訓》而言,內容較多,規模較大,但未有明確清晰的排列條理,當為弘靜隨想隨錄的緣故。(20)這種家訓的創制過程還可見于弘治年間劉良臣所撰的家訓,“省侍歸來,課農頗暇,年日就衰,舊習猶在,恐懈意一生,終于自棄,乃以所嘗經歷體驗之真切,或偶有一得者,筆之于書,題曰‘克己示兒編’,不拘體裁,不限條目。”劉良臣:《鳳川子克己示兒編》,《續修四庫全書》第938冊,第62頁。這種特殊的產出過程,也決定了文本不會是簡單的按需而生之物,作者對于文本的影響亦相應較大。這四卷《家訓》,全面展現出家訓文獻的三方面內容,可被視為分析方弘靜治家觀念的范本。同時,《家訓》不僅包含方弘靜本人對儒家治家傳統的理解,還囊括了他當時能夠獲得的多樣治家經驗,故而可被視為研究這一時段士大夫治家觀念的一個樣本。需要注意的是,《家訓》的篇幅與體系安排,自然會對文本的實際訓誡功能產生影響,何偉然的刪減編輯之舉便是明證。反面觀之,何偉然的所為,亦證明了弘靜《家訓》仍有一定的實踐價值。
二、治家權威的來源
由于家訓將會運用于實際的家庭治理當中,故而作者需要于文本中論述治家權威之由來。就這種權威的論據來源而言,方弘靜在使用前賢言行之外,還大量使用具體人物與事件以為論證之資。在此情形下,家訓的權威便不僅是圣賢所構筑的理想,更多是個人或家庭經驗的總結,進而具備豐富的生活和時代色彩。同時,方弘靜還傾向于利用事件正反兩方面佐證自身的言論,使得論證有著一定的“畫面感”,也更能在實用層面上增加其訓誡言論的權威。這種構成,實際上與當時其他家訓文獻并無根本區別,只是方弘靜著重利用歷史與時代經驗的比重較多,使得《家訓》的權威來源較為特殊,具體而言,其治家權威來源是由以下四個方面構成的。
(一)諸子與名儒的言行
盡管方弘靜所處的時代心學大盛,但他顯然更傾向于程朱理學,明代著名政治家葉向高有言,“其論學則服膺紫陽,以《太極圖》《西銘》《通書》《定性書》為六經羽翼,深惡世之好為異說以掊擊儒先者,謂其罪浮于揚雄之僭經”。(21)葉向高:《蒼霞續草》卷11《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方公墓志銘》,第123頁。這種學術旨趣也影響到《家訓》的制作,文中開宗明義,“圣賢之訓,盡在經書。濂、洛、關、閩之學,圣學也。后此者,信而述之,可也。何必別開戶牖,凌駕前薪,立異為哉,小子戒之。”(22)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29頁。從《家訓》內容來看,這些儒家先賢的言行確實構成了家訓權威的重要證據。關于孔子言行,文本中共出現了近40次,涉及多個方面,如方弘靜援引孔子言論,以勸誡子弟應恭而守禮(23)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46、461頁。,又以孔子遷父墓行為為例證,批駁當時因風水而遷葬的行為。(24)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46、461頁。孟子的言行同樣被方弘靜屢次引用,檢索《家訓》內容,以孟子為證者亦有20余條。例如,以孟子為例勸誡子弟應當浩然有正氣(25)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2頁。,又以孟子的人生經歷論證自己的家教觀念。(26)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82頁。宋明理學家們的言論同樣成為了《家訓》的論據來源,只是數量明顯較少,例如提到程頤論及《論語》一書的名言,提醒子弟應多讀《論語》。(27)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77、462、466頁。至于朱熹,方弘靜則主要是以其《家禮》作為立論來源,說明家庭與宗族的祭祀規則。(28)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頁。雖然方弘靜在思想上服膺程朱理學,但在家訓當中,并不排斥其他學派的觀點,以道家言論為例,弘靜從老子言語出發,闡釋他所認同的生死觀念(29)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2、447、454、455、456頁。,又通過引用莊子所言,分析家庭關系(30)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頁。與貧富態度。(31)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2、447、454、455、456頁。此外,方弘靜還在家訓中使用了管仲、韓非子、晏嬰、淮南子等多位不同派別名家的言論。
(二)歷史人物與事件
在歷史知識方面,方弘靜具有一定的功底,《千一錄》謝陛序中有言,“在昔藏書自六家七略之后,則有崇文四庫定為經、子、史、集也,迄今中秘因之。余閱方定之先生《千一錄》深有所當于衷,初惜無史,閱至‘客談’,則強半史也。”(32)方弘靜:《千一錄·千一錄序》,第100頁。在此歷史知識積累的基礎上,方弘靜于家訓中大量使用歷史人物,并兼采歷史事件來具體訓導、教諭子弟,使得歷史經驗成為家訓權威的重要源泉。就歷史人物而言,方弘靜使用了三種方式進行闡述,一是凝聚某些歷史人物的形象,弘靜直言此是為了見賢思齊,“讀史睹古哲人之跡,思企而及之,曰彼何人也,吾惡可不如彼也,斯可與讀史矣……見賢而不思齊,見不善而不自省,即淹貫百氏,何以異于庸眾人哉?”(33)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2、447、454、455、456頁。進而以張良、諸葛亮與范仲淹為例進行分析。二是以人物的具體行為作為闡釋對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弘靜往往綜合多位人物的行為來佐證自身的論點,如“齊王好射,引虧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顧愷之好自矜伐,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弄。夫人好人譽己,而為所戲弄者多矣。茍知譽我者為戲我,庶幾佞人,可遠耳。袁嘏詩平平爾,多自謂能,乃遺誚于后世也。小子戒之。”(34)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80、491頁。三是談論士大夫與風俗間的關聯,并以為言論的落腳點,如“殷仲堪性真,素食常五盌,外無余肴。夫五盌,視季文子之無兼味為侈矣,乃猶以儉素率物,江左靡汰之風可睹哉。蓋自何王輩來矣,其曰,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此士人所當服膺也。”(35)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2、447、454、455、456頁。又如“謝安石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夫賢者,眾之表也,忍以其身為厲階而敗,先王之訓乎。”(36)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77、462、466頁。在大量使用歷史人物進行論證之外,弘靜還少量引用了某些特殊的歷史事件以為證據,例如“子產為政,大人之侈者,取其衣冠而赭之,今詔書屢禁異服,而鬻于市、行于道者,輦轂之下若罔聞知,其何以令四國。”(37)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頁。“東漢建武、永明之世,禁上事言圣,浮辭虛譽,抑而不省,示不為謟子蚩,其規度遠矣,此可為萬世鑒。誠知謟子面謾而中蚩,必惡而遠之,佞人遠,則直諒之士進矣。萬乘之主猶懼為謟子蚩也,況士庶乎?匹夫無能遠謟子,況百乘以上者乎?”(38)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2、447、454、455、456頁。
(三)時人言行與故事
豐富的人生經歷與多重的社會身份,使得方弘靜具備了較為復雜的社會關系,通過這些社會關系,他積累了大量來自不同人物的社會知識,“蓋嘗從大夫之后,故及政從事四方,東西南北之人,談非無稽也,識之”(39)方弘靜:《千一錄·自序二》,第100頁。,它們同樣服務于《家訓》對于權威的論證。這些知識主要來源于三種人物群體,并以方弘靜為中心構成了明確的差序格局。其中與方弘靜關系最為親密者,當屬他的家庭與宗族成員,尤其是弘靜的父母,其言行在家訓中多可見到,例如弘靜之父的土地買賣之事(40)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頁。與晚年以樹木之喻訓子的言論。(41)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頁。又如在方弘靜幼時,其母的身教(42)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77、462、466頁。,以及祖母的治家觀念。(43)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7—438、430、430、433、435、436頁。在血緣群體外,家訓中還出現了依業緣而與弘靜有關的同僚、同年,以及以地緣而與方弘靜形成聯系的徽州人物,但這兩個部分并非涇渭分明,其中亦有重疊之處。就同僚而言,家訓中出場了夏元吉、李默、霍與瑕等人,同年則數量較少,僅有姚邦材與陳道基。而徽州人物較多,具有官身者如潘潢、鄭佐等人,同樣與方弘靜在官場上有所往來,另一些如江珍、王寅等人,則是方弘靜的朋友,還有一些則是方弘靜在居鄉中所接觸到的人物,如里中某甲者、里中汪某者與里中吳生珍等。此外,在徽州人物方面,家訓中還提及了以往的徽人事例,如程信、程敏政父子。最外層則是方弘靜風聞的一些人物,例如金陵記江南一計吏、杭州府推官、山西石州男子等,他們與弘靜并無直接關聯,但他從不同處得知這些人與事,認為有用于勸誡子弟,便將之記入家訓當中。但這些事件并非全然真實,部分可被視為故事,真實性大多難以證明,有些連作者本人都有所懷疑,“汪司馬傳鄭緝之事,甚異而不近情”。(44)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80、491頁。
(四)個人經驗與理解
方弘靜身經三朝,歷官數十載,且轉任多職,復雜的生命歷程便意味著豐富的人生經驗,他對此多有總結。同時,身為士大夫階層中的一員,方弘靜對于時代之變遷又有著與時人的共識,它們與弘靜的個人經驗一起,構成了《家訓》中治家權威的證據來源。在個人經歷方面,方弘靜總結他的官場經歷與讀書體會,以為身教之資源。以官場經歷論,方弘靜持身較正(45)就持身而言,方弘靜并不攀附,他的多篇壽序中均有提及,參見鮑應鰲:《瑞芝山房集》卷7《壽方少司徒采山先生九十序》,《四庫禁毀書叢刊》第141冊,第142頁;董其昌:《容臺集》卷2《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1冊,第297—298頁;湯賓尹:《睡庵稿》卷9《方采山先生九十壽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3冊,第147頁。同時弘靜也十分清廉,于時人筆記中可得以一窺,參見潘游龍輯:《康濟譜》卷4《清操》,《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冊,第285頁。,故而對其道德操守較為自得,于家訓中多有記錄,如官員壽禮,“余五十為按察使,僚友未知吾生辰也。六十園居謝客,而五、六君子枉駕焉,優人在門,未進也,小坐清談而已。七十填鄖陽,所屬未有言稱賀者,里闬中寄文數篇,覽之徒用愧汗耳。德之不修是懼,亦奚以為?”(46)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4、455頁。又如官方財物,“凡官物,不能視如己物,尚何云奉公體國哉?至于官舍,尤當嚴諭仆輩,臨去如始至乃可也。”(47)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5、469頁。再如官場立身,“吾初登第,肯一至分宜之門,即得翰林,然未必不終得罪。南都卿貳,若遵屢旨,供職三品十七年,可旦夕轉,然未必康健至今。造物者之予奪,宜順受,毋幸求,小子書諸紳可以坦蕩蕩矣。”(48)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92頁。
方弘靜在家訓中同樣書寫了他的讀書體會,例如“士之讀書開卷有益,其猶雨之潤物,灌園丈人之桔槔乎。故曰:學,猶殖也,不殖,則落。”(49)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8、439頁。“讀書能口誦心,惟身體力行,則一部《小學》可以為士矣。如其不爾,即博覽多聞,適以滋穢,不若椎魯田父,為近道也。”(50)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5、469頁。于讀書之外,弘靜還在家訓中以較大篇幅記載了他對于作文的理解。(51)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0、459頁;卷25《家訓三》,第472頁。
嘉萬時期,社會有著較大的變化,方弘靜于此也有著自身的看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士大夫的共識,并將之寫入家訓當中。對此,方弘靜有著明確的傾向,即通過對前朝社會的懷念,以反襯當時,其中多以具體問題為對象進行展開,如論及當時全國士人風氣,“嘉靖初,士風猶厚,于時談者,猶以成、弘時為不可復見也。”(52)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8、439頁。又如論述近來徽州奢靡世風,“今侈靡之風日益甚,雖吾郡亦漸汗習,非復舊時矣。有識者每思力挽之,無論成弘以前,即如嘉靖初年,何可得也。”(53)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4、455頁。
三、治家目標與手段
盡管方弘靜在撰述《家訓》時未曾列有明確而又細致的條款,但文本卻并非全無條理,其內容仍然是按照具體治家目標與手段展開的。與前述權威論證所不同的是,目標與手段主要是由方弘靜自身所創制、總結或改造而成的。在目標上,方弘靜描繪了理想化家庭的樣態,而治家手段便是如此家庭的構建過程。前者包含子弟人格、家庭關系與宗族秩序三個層次,其中子弟人格與家庭關系自家訓出現起便是文本闡述的重心,而宗族秩序則是在宋明以來徽州地域宗族發展影響下的產物。這種樣態描述盡管在形式上大多數屬于照本宣科,但方弘靜本人是仍將之放置于具體環境下進行闡述的。而在構建過程方面,《家訓》文本除了討論了一些基本的構建方式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針對當時出現的問題做針對性的闡釋。這種撰述狀態體現出《家訓》與當時社會的密切聯系,使得文本具有一定的獨到之處。
(一)治家目標:理想化家庭的樣態
1.理想化的子弟樣態
在家訓中,方弘靜用大量篇幅闡述他認定的理想化子弟。由于其人在學問上認可理學,故而主要以理學思想來塑造理想化的個人。(54)關于理學范疇內理想化個人,可參見楊國榮:《宋明理學:內在論題及其哲學意蘊》,《學海》2012年第1期;張學智:《宋明理學中的“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劉培:《理學對人生的塑造與規范——以朱熹辭賦為中心》,《南京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在家訓中,弘靜多以儒學正統道德概念來設定理學化的個體樣貌,并以此作為相應的合理和合法來源。以儒家所論的“仁”為例,數十次出現于《家訓》當中,且方弘靜會將之放置于特定環境之下,“凡有忽人之心,傲人之色,凌人之辭,皆自損其德,無與于人。在上而臨下者,猶不可,況同輩乎?況長者乎?如其為人所慢則宜自反,吾可慢耶?則恥不若人,莫如為仁,孟子之言至明切矣。”(55)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1、461、458頁。再如“君子”概念出現的更為廣泛,在單獨闡述的同時,方弘靜還會將其與“仁”“義”等詞綜合起來進行討論,如“趙文子為室而礱其椽,張老之懼也,宣子之服義也,志于仁矣,君子哉。今也士庶之室鮮不礱也,吾見加密石焉者矣,不仁者之為也,戒之哉。”(56)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2、474、470頁。又如“是故君子戒慎不違,窮不失義,奚有于敗,達不離道,寧幸其成,是以坦蕩蕩而長囂囂也,若此者可謂成人矣,成人則何敗之有。”(57)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41、437頁。
在直接利用儒家概念訴說理想化個人的同時,方弘靜又借用另一些概念以展現其理解的理想個人,較為典型者便是理學中的“天”。在家訓中,方弘靜認為,“先儒言天者理而已,至哉言也,理具于心,心違理,斯逆天矣。逆天者,天寧祐之。每見兇人立心傾險者,其后必不昌。吉人存心端厚者,其后必不替,閭里中可悉數也。”(58)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2、474、470頁。而在如此概念體系之下,方弘靜吸收了當時的社會經驗,在前述后三種論據知識的支撐下,進一步具體地闡述了不同情境中的理想化個體應具備的因素,例如善,“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悅諸心而已矣,心不欺天所監,故曰:知我者天,豈欺我哉。”(59)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1、461、458頁。又如富,“天不能貧人也,乃若終歲營,營未必如愿。仕有不遇,耕有不獲,賈有不利,皆有主之者,此天之所命也……故曰:人不能自富也,天人之交相勝也,于是乎征之。”(60)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41、437頁。
此外,方弘靜還從實用角度利用某些儒家概念,闡發了他對于某些方面理想化個體樣貌的認識。以“慎”的概念為例,方弘靜展現了三個方面的理解,一是“敬慎”,二是“慎謙”,三是“慎言”。(61)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29頁;卷24《家訓二》,第460頁;卷26《家訓四》,第487頁。實際上,《家訓》展現出的理想化個體并非全然是一種儒家話語中的完美人格,還包括儒家以外的思想內容,最為典型的例證,便是方弘靜在宿命觀念下對于理想化個體的表述。通過對個人宦途的總結,方弘靜于家訓中得出了宿命支配人格的核心結論,即個體理應順應命運,“吾初登第,肯一至分宜之門,即得翰林,然未必不終得罪。南都卿貳,若遵屢旨,供職三品十七年,可旦夕轉,然未必康健至今。造物者之予奪,宜順受,毋幸求。”(62)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92、478頁。
2.理想化的家庭關系
對于理想化家庭,方弘靜同樣是從理學思想出發進行描述,且未有多少偏離。在具體內容上,則是以父子、兄弟與夫妻三種關系為核心點。
就父子關系而言,方弘靜主要是強調父子身份的責任,特別是子弟對于父親的服從,“伊川云,古也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伊川之生宋之盛也,而俗之下乃爾,然此系于世之升降,而家之盛衰亦可占矣。從父兄者家必昌,從子弟者家必替。”(63)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1、461、458頁。“吾見東西家其卑少從長者教令,未有不昌者也。其子弟恣意自擅,不率父兄之訓,未有不傾者也。”(64)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92、478頁。至于父親之職責,則是在于教,“子所以為斯人,慨也,孟子則又望之于賢父兄也。曰:養之無棄之,益懇至矣。夫以善養人者,天下未有不服者也,況于家乎?”(65)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2、474、470頁。
對于兄弟關系而言,其中亦有責任部分,即弟弟需要服從兄長,“明道伊川同游,從游者皆隨明
道,伊川曰此頤不及家兄處,蓋伯子溫而叔子嚴也。余意非惟諸人宜隨明道,弟固從兄者耳。”(66)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0、450、453頁。在此之外,于家訓中,方弘靜還論述了兄弟友愛乃是兄弟關系理想狀態的另一組成部分,“世人之貽厥孫謀也,必曰:和以致祥,莫不諄諄然矣!于兄弟則鮮能白首一心者,何以啟后人耶?夫婦時有反目者矣,事過則相愛如初,兄弟之相猶則藏而不忘,何不一推之也。”(67)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頁。對于夫妻關系,方弘靜堅持認為“夫為妻綱”當是此種關系的理想狀態,且強調丈夫必須堅持此種認識,“夫為妻綱,責在已爾,已不能以禮儀刑,而區區求備于婦人,豈有遠志者與?”(68)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頁。
3.理想化的宗族秩序
縱觀《家訓》全文,弘靜并未在宗族秩序上著墨太多,但對于宗族秩序的存在基礎和具體形式多有強調。在他看來,子弟知曉“一本”之意后,便可使得宗族秩序長久存在,“吾家自西漢末渡江至今,子孫猶守先墓,雖散處閩、浙者,源流甚明,茍知一本之義,則百世萬里宜在念矣。”(69)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5頁。至于理想化的宗族秩序形態當是以“禮義敦睦”為核心的,“宗族以禮義敦睦相尚,此可稱故家如以富挾,以貴挾,以眾挾,皆薄夫也。”(70)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0、450、453頁。而禮則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基礎,其中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宗族主體所帶來的宗法秩序,其范本來源主要是朱熹所做的《家禮》(71)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頁。;另一層面則是族人個體所確立的孝悌秩序,“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士之次也志乎。上者見其進而不惰矣。其為人也,不親于族,不信于鄉,而長傲自滿,豈惟不可謂士人,道惡盈孽且作矣,小子戒之。”(72)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頁。
(二)治家手段:理想化家庭的構建
1.子弟層面的構建
方弘靜在《家訓》中設定的理想化子弟乃是以理學道德為核心的個人,而如此子弟構建的一般方式便是個人的修德。從家訓內容來看,修德的具體方式有多種,大部分都是以往儒家學者所闡述的。(73)參見金桓宇、陳延斌:《方弘靜家訓之修德思想研究》,《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在此之外,方弘靜還針對當時社會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構建方式,主要通過前述論據知識中的后三類,標示出應參照或規避的行為模式,并且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屢有重復和強調。
這些問題涉及較廣,主要集中于日常行為,如時人生活日趨奢侈且竭力追逐財富,方弘靜便于家訓中多有立論,不僅列舉了歷史人物與當時人士以為正反之例,還直接列出了一些錯誤行為,愿子弟予以變更,“婦女競華飾至擬王家,飲酒無筭爵,客多飲則主人以為樂,或有以勸酬不行而成忿恚者……婚論財,厚聘厚嫁,又有不納聘財,而反遺之以銀幣者……每為家計累故多溺女,然亦有得壻家利益者……示兒輩有識者宜思有以挽之。”(74)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頁。又如針對當時社會士人風氣變化,尤其是士人的驕橫,方弘靜于家訓中多次強調當以謙卑為上,特別列舉了多個歷史與當時的事件,以為告誡,“開元中有常敬忠者,能一遍誦千言,勅中書試之,賜賚驟貴,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余里中吳生珍,一遍誦數百言,亦能之,而所著無奇,不為時所取。有汪生旻者,游興化李公之門,李賞愛之,遂自矜也,而驕其同輩,一夕流血而死,莫知其由。夫小有才而不能處于不兢,鮮能免者,其可以鑒也夫。”(75)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0、450、453頁。再如當時社會,特別是在徽州區域內,風水兇吉之說盛行,有著相當不良的影響,方弘靜在家訓中多有反對,以柳渾為例,勸導子弟,“柳渾年十余歲,有神巫言其相夭且賤,幸而為釋乃可緩死耳。渾不從,為學逾篤,其后大有勛名于唐,年七十四。余未冠時,術者言年止四十,余以為造物者茍靳余,余惡能為躍治之金乎,安之爾。余位與德不能逮柳也,年幸過之。術士多言時或億中,而舉世惑之,何哉?由妄冀之念,勝而徼幸于可必也。”(76)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5、430、437—439、460、434、442頁。
2.家庭層面的構建
對于理想化家庭關系的建構,方弘靜所提出的和、忍等基本方式并未超越前人,但為了解決當時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總結的相應方式有著某些新意。就這些問題的核心內涵而言,不過是財富與情感而已,但外在表現則有所不同,方弘靜則進而提出了相異的解決方式。
在財富方面,當時社會,特別是徽州地區,出現了三種威脅家庭關系的情景,一是家庭財富的由來,由于晚明時代金錢的社會影響力日趨強大,某些家庭不顧儒家倫理關系去追求財富。在《家訓》中,方弘靜標示出一些例證,以為警戒,尤以借婚嫁之事斂財的情況較為典型,“嫁女必勝吾家,娶婦必不若吾家,此有激之言亦不盡爾,惟是崇禮敦義,不兢侈靡者,乃不失其親也。茍徒慕一時之榮盛,鮮不悔矣!”(77)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0、437、436、438、432頁。二是家庭財富的分配,方弘靜對于當時徽人分家簡單按利而行的舉動較為不滿,認為應以“義”為標準進行分家,“人顧義何如,何可違義從利,利不必得,而不義可為耶?若是父是子者,可以為訓矣。”(78)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0、437、436、438、432頁。并在家訓中列舉了多個不同例證以為證明。三是家庭財富的延續,晚明時期社會流動頻繁,造成家庭地位下行的可能性較大,方弘靜認為在家庭生活中當對子弟進行治生教育,并將之寫入《家訓》當中,且以他的朋友作為例證,“吾郡士大夫素重名節,仕宦無厚積。余耳目所接,在邑里中如程方伯旦、鄭大參佐、吳太守遠、余族兄圉卿遠宜、鮑司徒道明、余宗人太守瑜,此其子皆馴謹,而歿后貧乏,或至易產不能為活者……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予俱善殖生,二公家頗厚,非以官起也,前輩楷范,后生無忘哉……不則勤殖,亷入而儉出,恒足之道也。”(79)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9、475、476頁。
而在情感方面,晚明時期的徽州婦女社會關系日漸復雜,進而影響到了家庭內部成員間的情感。盡管對于婦女社會關系的管制乃是傳統家訓長期關注的重心,但方弘靜針對這種情境,仍然提出了一些更為強力的理解,例如“三姑六婆比之三刑六害,昔之閑家者詳言之矣。今所謂齋婆者,名為事佛,其實奸盜之徒也。福善禍淫,圣有明訓,何用別希功果。佛亦言,即心是佛,不欺心,不必佞佛耳!宜時提省,嚴拒此輩,勿使入門也。”(80)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0、437、436、438、432頁。
3.宗族層面的構建
盡管方弘靜在《家訓》中對于理想化的宗族秩序并未有太多的描述,但卻以較大篇幅批判了當時一些影響宗族秩序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祭祀、墓葬、財產與繼承四個方面。就祭祀而言,方弘靜在家訓中明確反對于祭祀之外舉行其他信仰活動,并以其父親的行為以為佐證,“先通議府君治家時,祭之外別無祈禳,一切巫覡僧道輩無許及門,吾謹遵焉,此家人所共見也。異日有聽婦言惑邪說玷素風者,非克肖子哉。”(81)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78、492頁。而在祭祀過程中,則明確限定女性參與祭祀,“婦人不宜畫像,像非禮也……宗祠或稍遠,婦人不必與,亞獻以主婦,恐未能如禮。”(82)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0、437、436、438、432頁。在墓葬方面,方弘靜通過多重例證反對墓地兇吉之說,其中既有歷史事件,也有當時故事,特別是后者,有著明確的針對性,例如“風水禍福逹者必不泥之,近如邑中汪氏先墓為仇家所掘棄,而富盛如故,里中潘氏墓,他姓建社屋以塞之,而其孫發科。吳氏、程氏之墓有挾仇而害之者,亦不為害,皆昭然耳!目者可以辨惑矣。”(83)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0、437、436、438、432頁。又如“邑中發塚之變,凌氏被害為甚,其年入學二人,二舉人固無恙。風水之不足信,亦一征也。何世人易惑而難悟。”(84)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9、475、476頁。
對于財產,方弘靜在《家訓》中闡述了兩種情況,其一是正確使用宗族資產,“祠茍完有余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獲焉,可也。若游閒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為也,惟煢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85)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9、475、476頁。其二則是預防宗族資產的流失,“萬歷己亥有利色映之樹,而擅伐之者,山下居民于里中五之一耳,而少亡者三十余人,安可不戒也。此山吾家數百年之業,他姓不得與,何為自孽而殃人后之。有識者,時警省之,毋忽也。”(86)方弘靜:《千一錄》卷26《家訓四》,第478、492頁。最后是繼承,方弘靜針對當時社會因繼承而影響家庭與宗族的情況,認為應當直接參照當時法律規定,于法律允許范圍內進行繼承便可,“薄俗爭繼而破家者,知利而不知害,良可鄙也。余嘗因事而諭之,兄弟之子多可并繼,茍不肖可擇繼二者,律之所許也。無子而有猶子者,定之于豫可也。異姓則所必禁,是不孝之大者,不孝者,惡可以不刑乎。”(87)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7頁。
四、社會風俗與治家認識
縱觀整個明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風俗也呈現出明顯的變化。晚明士大夫對此多有總結,其中存在著這樣一個聲音,即正德之后風俗逐漸變壞,至萬歷時,已是風俗澆漓。(88)參見陳寶良:《明代的時代轉移與風俗變遷》,《中州學刊》2015年第10期。這些士人大都還有著對于晚明社會風俗變化的憂心,以及對之前歲月社會風氣的懷念。事實上,從一些萬歷年間形成的中國南北多地方志文獻當中,可以看出社會風氣變化的普遍狀態,例如萬歷《洪洞縣志·風俗志》(89)常建華:《從“日常生活”看晚明風俗變遷——以山西洪洞縣為例》,《安徽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和萬歷《歙志·風土論》。正是在如此情感驅動下,一些士大夫認為應當有所作為,且進行了一定的嘗試,方弘靜便是其中的一員。
就方弘靜的生活哲學而言,李維楨有所概括,“先生九十有五,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俛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默為檢式儀表,如丘山塊然不動。”(90)李維禎:《大泌山房集》卷17《〈方少司徒年譜〉序》,第675頁。《明神宗實錄》中也有著較為類似的表述,“(方弘靜)寧定恬素,不與時移,歷試諸藩,多所建樹,至海上之防,奇謀制勝,弗自居功。既歸而型家范俗,終始不渝,享衛武之年,時謂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云。”(91)《明神宗實錄》卷507,萬歷四十一年四月己亥,第9619頁。由此可以看出,方弘靜崇尚儉樸且意志堅定,于個人行為上有著自我的堅持,這一點也可從他取字“定之”當中窺得一二。而對于當時的社會風俗,方弘靜的看法也與前述士大夫群體類似,“我朝自圣祖開基,力鎮之以樸。洪武至于弘治,士重節義,閭閻有恥,庶幾近古矣。嘉靖初年,淳風未盡泯也。隆、萬以來,日趨于薄,無論視成、弘時若太古,即求如嘉靖初年不可得已。”(92)方弘靜:《千一錄》卷21《客談九》,第411頁。同時,方弘靜對于改變世風也有著一定的信念,并在家訓中有所體現:
成、弘之際,幾于比屋可封。正德時,雖宦豎為孽,而士習猶端。嘉靖稍漓矣,以視今則邃古也。習而不察,非智也。知而不變,非勇也。在位者泄泄沓沓,若非所急,非忠也。居鄉不能表率,而隨其波,非仁也。肉食者不慮,藿食者相忘,一室不能治,如遠何?古之人恥之,吾亦恥之。(93)方弘靜:《千一錄》卷24《家訓二》,第458頁。
實際上,在方弘靜最后的鄉居歲月里,在此方面已然有所作為。方弘靜在致仕歸鄉之后,訂立《屏帖》,上書不應酬、不飲酒等數條戒律,并在最后寫上訂立之目的,“君子居鄉,使不善者化,上也。有過相規,雖未及化,冀其改焉,次也。若德不能化,規不如約,面諛而背非,君子恥之。”(94)方弘靜:《素園存稿》卷19《屏帖》,第346頁。
而在鄉里與宗族間,弘靜也同樣有所舉動,如訂立鄉約以圖制止迎神賽會或導正主仆倒懸(95)方弘靜:《素園存稿》卷19《諭里文》《諭里》,第349、354頁。,以族內宗老身份勸導族人等。(96)方弘靜:《素園存稿》卷19《諭里文》,第350—351頁。同時,他還期待著有“同好者”,并曾寫信給大學士許國(97)方弘靜:《素園存稿》卷15《又奉內閣許公》,第277頁。,望其能力行儉樸,成為當時之表率。
在如此背景之下,方弘靜撰述《家訓》便不足為奇了。同時,從前述《家訓》的內容來看,弘靜顯然是認為家庭治理可作為改變世風,使之回歸之前簡樸狀態的一種途徑。《家訓》文本中的治家認識,則可被視為方弘靜對于當時社會風俗,特別是徽州社會風俗的一種反應,其直接證據就是文本當中大量源自或針對“里中”的訓誡。如此一來,《家訓》文本并非是以往家訓文獻的翻本,或是道德榜樣的綜錄與轉述,更多地是基于經驗治理家庭,進而勸導當時社會風俗的指南。相較于子弟是否能夠成為圣人,方弘靜更為擔心子弟于日用之中延續當時的壞行惡習,以至于不能挽回風氣,而此事正是他治
家認識的核心。(98)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5、466頁。
在這種關注的驅動之下,《家訓》文本展現出方弘靜對于當時徽州社會的諸多憂慮,使之具備明顯的時空特點,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首要的是本家家庭地位的下行,其中包含有家庭財產、子弟品行、成員關系等多個方面。方弘靜甚至會論述一些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以為其論之佐證,可見其惦念之深。(99)方弘靜:《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5、466頁。而家庭社會地位的忽變在此時徽州較為多見,弘靜之顧慮正源于此。(100)徽州方氏的情況可為參考,唐力行:《徽州方氏與社會變遷——兼論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其次是徽州地區內社會關系的翻轉,《家訓》中多處可見弘靜加強僮仆管理的思路,有些觀念甚至較為極端。(101)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6頁。此論同樣來源于明嘉靖之后徽州佃仆家族的興起,與大族間矛盾日漸突出。(102)[日]中島樂章著,郭萬平、高飛譯:《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為中心》,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最后則是徽州社會分化及道德淪喪,弘靜在《家訓》中明確指出當時徽人之間的財富不均以及里中個人之狡黠,并給出了明確的管理方式。(103)方弘靜:《千一錄》卷23《家訓一》,第433頁;《千一錄》卷25《家訓三》,第463頁。這種擔心亦本于晚明徽州的社會狀態,當時徽州官府檔案便是其明證。(104)參見王燦:《社會轉型與明代后期徽州社會風氣——以〈新安蠹狀〉為主要材料的考察》,《合肥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觀察同時期的其他家訓,以如此細碎狀態針砭鄉里時弊的文本,僅有《家訓》一件,但方弘靜期待通過撰述《家訓》以正世風的治家認識,在當時徽州卻非個案,隆慶年間金瑤便在其修的《家譜》當中以《陳俗》為名撰寫了類似的家訓文本。(105)金瑤纂:《珰溪金氏家譜》卷18《陳俗》,明隆慶二年刻本。全文參見常建華:《16世紀初的徽州宗族與習俗——以〈新安畢氏族譜〉為例》,《東吳歷史學報》第19期,2008年;《16世紀初徽州的宗族與習俗補正——以〈珰溪金氏族譜〉為例》,《徽學》第9卷,2015年。對于其實際上是家訓的判斷,來源于金瑤的《引·陳俗》,“為父兄者知以是誨其子弟,為子弟者知以是自誨。”金瑤:《金栗齋先生文集》卷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8冊,第206頁。
在徽州之外,產于同時及之后的數部家訓也有此旨趣,例如王祖嫡的《家庭庸言》、徐三重的《鴻洲家則》、陳繼儒的《安得長者言》、莊元臣的《治家條約》、秦坊的《范家集略》、李淦的《燕翼篇》等。(106)陸睿:《明清家訓文獻考論》,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只是這種有著明確針對世風目的《家訓》文本,實際效力可能并非如方弘靜等人所愿,主要原因便是他們并未能夠準確把握晚明時代的發展脈絡,進而在家訓中采取正面疏導的方式以推動社會發展,而僅是試圖通過治家而實現世風“復古”。之后徽州區域的風俗變遷恰好能夠印證這一點,明末時期的徽人愈加焦灼浮躁,社會亦是震蕩不安。(107)卞利:《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徽州社會變遷中大眾心態研究》,《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