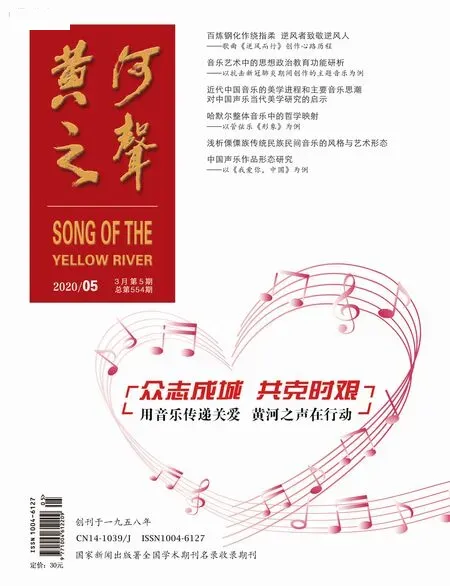高中音樂教學對學生音樂鑒賞能力的全面培養
◎ 史麗華 (甘肅省涇川縣第一中學)
音樂是人類一種藝術化了的情感產物,因而其具有審美潛力,又具有精神情感陶冶的功能。因此,區別于音樂創造而指向優秀音樂作品聽覺欣賞的音樂鑒賞便在素質教育體系下成為高中教育及音樂學科課程的重要內容。其通過聆聽者對自身主觀經驗的結合,調動內心聽覺,從而引起回憶、想象及聯想等,豐富自己從音樂欣賞中獲得的情感體驗。但在此內心聽覺能力之前,主體必得具有對作為基礎的音樂音響感知能力。
一、對音樂音響的辨別、感受能力及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培養
音樂作品的音響通過節奏、旋律、和聲等音樂諸要素的合作參與、加之人為對其進行的藝術化加工形成,而以某種“聲音工藝品”的面貌最終呈現。依靠人天生皆有的外在聽力,而皆可對此進行接收,但是單純的對聲音的接收并不等于對其藝術性的認識和解讀,也即我們的聽覺需要按照音樂音響建構形式的專門訓練,以達到分辨、解析音樂作品的目的,繼而過渡至內心聽覺,獲得情感體驗。而針對音樂音響、按照其建構形式的聽覺感知訓練,可以分為對音樂音響的辨別、感受、注意力和記憶力此三大層級維度,對應的訓練方式則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加強對音樂基本要素的辨別訓練
對音樂音響的辨別也即對音樂的音高、節奏、力度、音色等基本要素的辨別。《淮南子》中亦有“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的記載,也即如若欣賞者具備對此類基本要素的辨別能力,則有了音樂感知的基礎。
例如:對于音高辨別,我會借助鋼琴,以讓同學們的音高達到與鋼琴某個鍵發出的音高相契合的方式,加強其對不同音高的感知與發音。除卻此,在此方式的練習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又會穿插進行聽音辨音的訓練,即我隨意按下鋼琴中的任一鍵,讓同學們轉過身去,依靠聽覺感知辨別說出音高符號。如此,同學們的音高聽辨與把控能力皆能夠得到有效的提高,對于音樂作品中的音域、音高變化及其難易性和變化性等便皆能夠具有清晰的判別和理解。
(二)外化表現形式幫扶音樂音響的感受
繼對音樂音響基本要素的辨別能力之后,則應是在此基礎上對更上一層級的音樂音響的旋律感、節奏感、多聲部的音樂感以及對樂曲結構的整體感知過程。對此的感知接收是欣賞主體在進一步認知音樂藝術性、獲得音樂美感的目的下所需必備的能力。而教師對學生此能力的具體幫扶則可依據上述所需感知的要素特點,采用如舞蹈、演唱、指揮等的外化表現形式。
例如:“旋律”即是由一系列的樂音按照一定的音高與一定時值組合在一起構成的起伏性音線,即其自身具有內在的走向和傾向,而聽者內心是否能夠捕捉、感受到此走向與傾向便決定著其內心“旋律感”的是否生成。據此旋律屬性即“旋律感”的生成原理,我們發現,不論在樂曲創作過程中,創作者對于旋律的創造必以其出自人之本能的呼吸、起伏規律為基礎,以達到使人聽覺“舒適”的目的。而此呼吸與起伏規律是人所共具的,因此,對同學們旋律感的鍛煉則可通過讓其進行自主演唱,以自然而然體驗到旋律中的分句、呼吸、起伏、氣息、表情、語氣等種種要素,從而生成“旋律感”。如在《長江之歌》的欣賞中,我則讓同學們唱出來,在歌唱如“你從雪山走來,春潮是你的風采”等句時,其則可感知到為什么“走”字是高音“do”與“so”組合且占兩拍,為什么“來”字是“la”音且占三拍,因為這樣的音高變化與樂音時值設置方式符合人的呼吸、氣息規律,且生成深沉、宏偉、莊嚴的語氣,不僅使聽覺與歌唱舒適,又使聽者與歌者能夠生成契合此作品基調的內心情感。
(三)結合音樂認知的重復傾聽以促進自主化音樂延伸
除卻上述對學生音樂基本要素的辨別、感受力的培養之外,我們還應意識到:音樂是時間的藝術,音樂的音響材料在時間中展現并伴隨時間的運動而消逝,因此,傾聽欣賞者必得在音樂欣賞過程中具備高度的注意力與記憶力。對此注意力與記憶力的培養則可依據學生的記憶規律,以結合音樂認知的重復傾聽促進其自主化的音樂走向感覺延伸。
例如:對于沒有歌詞的樂曲的整體記憶是學生難以逾越的一大關卡,如對于《第六(悲愴)交響曲(第四樂章)》一曲的欣賞中,我則先讓其反復聽一小節音樂的彈奏,直到能準確地哼唱出來為止;而后則再加上一小節音樂,并將此節音樂與前面的音節關聯在一起,使音樂不中斷,然后再進行反復傾聽與哼唱。之后再加一小節……如此循序漸進的方式契合學生的記憶規律,且在達到一定程度時,同學們則能夠具有一定“樂感”,即對音樂組織規律的感知,而能夠自覺地生成快速的音樂記憶能力。
二、對內心聽覺能力的培養
情感是音樂的靈魂。在上述欣賞音樂的過程中,在對學生音樂基本要素的辨別力、對音樂音響的感受力、注意力和記憶力進行培育訓練時,其同時也在借助于內心聽覺發生情感體驗。而針對音樂的情感內涵進行體驗的過程,亦是傾聽者自身的感情與音樂表現的感情發生交融與共鳴的過程。因此,對學生內心聽覺能力的培養,亦應分為兩大陣地和階段:前述的音樂音響感知與對學生生活體驗及情感訴求的調動。
(一)音響音樂感知奠定內心聽覺力基礎:準確、深刻、細致
音樂是聽覺的藝術,因為其由節奏、旋律、和聲、速度、力度、音色、曲式、體裁等音樂要素、并經過人為藝術化設計處理而最終以“聲音工藝品”的面貌示人,而欣賞主體唯有具備發現完整音樂作品中的各要素形態及各要素組合形式、并能夠將其進行整合看待,才能夠真正準確、深刻、細致地認識音樂作品,進而在此認識過程中產生音樂情感。
例如:在《草原放牧》一曲的欣賞中,同學們如若具備分辨各音樂要素的能力、旋律感、節奏感等音樂音響感知力、對音樂音響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其則可知道本曲將民族傳統曲式中的多段體和交響樂中常見的奏鳴曲式進行了結合,并共分為五部分:草原放牧、與暴風雪搏斗、在寒夜中前進、黨的關懷記心間、千萬朵紅花遍地開。且每部分由于所表現的情景與主題不同,所采用的節奏、主要樂器等亦有不同,如第一部分節奏活潑輕快,以刻畫姐妹倆歡快的放牧場景,旋律則包含舞蹈性因素及內蒙民歌中的“短調”特點;而第四部分的節奏則自然舒緩,旋律如歌而深情,以揭示姐妹倆對黨的感情以及黨對倆姐妹的親切關懷。同學們能夠認識到此,便首先會回歸音樂創作者的立場而體驗到音樂原本的情感內蘊(歡樂、黨與小主人公之間的情感等),而為之后融合自身生活體驗與情感訴求的深切共鳴情感的產生奠定鑒賞的基礎。
(二)融合學生的生活體驗與情感訴求
白居易具有良好的音樂音響感知能力,“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等可映證,所以其能夠聽懂琵琶女所彈奏的曲子,體會其所想要傳達的情感,但由于其自身有“謫居臥病潯陽城”的經歷,才會與其情感發生共鳴,而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慨嘆。對學生在音樂欣賞中,融合自身生活與情感的指導亦便為教師所應進行的工作。
例如:在《長江之歌》一曲的欣賞教學中,同學們基于自身生活的局限可能在音樂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基調之外,并無法有更深層次的共鳴,此時,我則讓其回顧自所見過的祖國宏偉自然景觀,如泰山、黃河等,或者回顧自己所看過的愛國類影片,如《戰狼》、《我和我的祖國》等,以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某種大情懷、團結感與凝聚力,進而運用到對《長江之歌》的欣賞與歌唱中去。如此,則亦具有了學生主體與音樂作品之間情感共鳴發生的空間,其音樂內心感受力,則亦會由此自身生活與情感的參與而更上一個臺階。
結 語
總之,對學生音樂欣賞能力的全面培養,是一個需要進行詳細規劃與穩步落實的系統教學工程,這絕不是一朝一夕中可以一蹴而就。但鑒于高中教育中,學生音樂學習的非專業性及學科課時的有限性,教師則可在此系統中摘取具有節點、基礎作用的要素與范例展開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