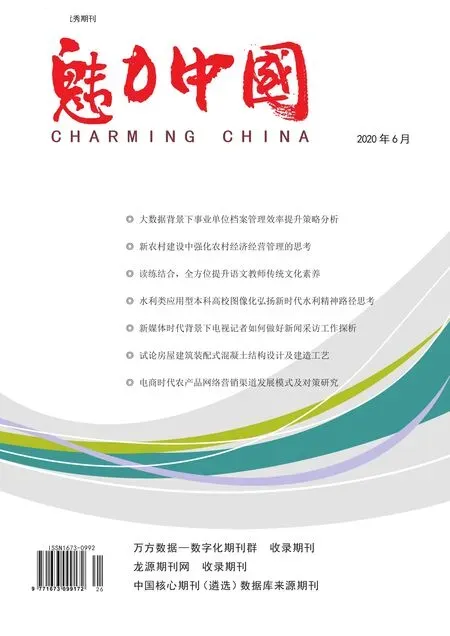河北棗強(qiáng)移民探源
(江蘇省邳州市戴莊鎮(zhèn)人民政府,江蘇 邳州 221300)
一、河北棗強(qiáng)移民傳說(shuō)流傳范圍
在山東省濟(jì)南、淄博、濰坊等地,有很多人自稱其祖先是河北省棗強(qiáng)縣移民,且遷徙時(shí)間集中于明初洪武至永樂(lè)年間。在今天的章丘、壽光、博興、惠民等縣市該傳說(shuō)尤為突出。據(jù)說(shuō)當(dāng)時(shí)有多達(dá)三十五萬(wàn)人從河北棗強(qiáng)移民到山東中、北部。據(jù)有關(guān)資料顯示,章丘市的棗強(qiáng)移民村落占村落總數(shù)的36.5%,壽光市的棗強(qiáng)移民村落占村落總數(shù)的16%,博興縣棗強(qiáng)移民村落占61.5%,惠民縣占到了84%,其他地區(qū)也有大量分布。在清末民初編篡的大量鄉(xiāng)土志中也有一些來(lái)自河北棗強(qiáng)的移民記載。如《長(zhǎng)山縣鄉(xiāng)土志·氏族》收錄的九個(gè)大姓中,有王氏、李氏等七個(gè)姓來(lái)自棗強(qiáng),其中五個(gè)姓氏遷于洪武二年,一個(gè)姓氏遷于洪武四年,一姓遷于永樂(lè)四年。另一個(gè)大戶劉姓,于洪武二年遷于棗強(qiáng)附近的寧津。只有徐氏來(lái)自江蘇昆山,但時(shí)間也是洪武二年。《章丘縣鄉(xiāng)土志》記載在清末該縣的七個(gè)大姓中,有五個(gè)宣稱來(lái)自棗強(qiáng)。五個(gè)大姓中,焦氏、胡氏、高氏稱遷徙于“明初”,謝姓聲稱遷于洪武二年,只有張氏稱遷徙于金章宗承安四年。我們對(duì)《廣饒姓氏考》一書(shū)的移民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廣饒縣553 個(gè)村莊社區(qū),203個(gè)姓氏,其中從棗強(qiáng)縣移民的涉及271 個(gè)村,90 個(gè)姓氏。又其中有17 個(gè)村莊的某姓氏由山西或河南經(jīng)棗強(qiáng)縣中轉(zhuǎn)后分發(fā)到廣饒縣;其余的254 個(gè)村則記載從棗強(qiáng)遷出。那么,如此眾多的棗強(qiáng)移民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是否真的遷于明朝初年和河北省棗強(qiáng)縣呢?
二、河北省棗強(qiáng)縣是移民發(fā)源地可能性排除
(一)據(jù)《明史》和《明實(shí)錄》等記載,明初移民始于洪武三年,止于永樂(lè)十五年,歷時(shí)四十七年共十八次,前三次移民是為了建設(shè)中都鳳陽(yáng),所有移民全部安置到鳳陽(yáng)。而真正意義的移民開(kāi)始于洪武二十一年。洪武年間徙民九次,建文年間徙民一次,永樂(lè)年間徙民八次。永樂(lè)年間移民全部到北平及附近地區(qū),不多贅述。洪武年間移民到河北及山東的有關(guān)信息摘錄如下。
1.公元1388 年。《明太祖實(shí)錄》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wú)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等閑曠之地。”
《明史》卷三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徙澤、潞民無(wú)業(yè)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nóng)具,復(fù)三年。”
2.公元1389 年。《明太祖實(shí)錄》卷一九三載:“(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后軍都督朱榮奏,山西貧民徙居大名、廣平、東昌三府者,凡給田二萬(wàn)六千七十二頃。”
3.公元1392 年。《明太祖實(shí)錄》卷二二三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軍都督府僉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恪等往諭山西民愿遷居彰德者聽(tīng)。至是還報(bào),彰德、衛(wèi)輝、大名、東昌、開(kāi)封、懷慶等七府徙者凡五百九十八戶。”
《明史》卷七十七載:“其移徙者,明初,當(dāng)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wú)田者四千余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dá)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萬(wàn)五千八百余戶,散處諸府衛(wèi),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wàn)兩千八百余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kāi)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fù)徙江南民十四萬(wàn)于鳳陽(yáng)。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狹鄉(xiāng)之民,聽(tīng)遷之寬鄉(xiāng),欲地?zé)o遺利,人無(wú)失業(yè)也。太祖采其議,遷山西澤、潞民于河北。眾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于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wàn)戶于京師,充倉(cāng)腳夫。太祖時(shí)徙民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成祖核太原、平陽(yáng)、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wú)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shí)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鮮矣。”
從以上移民記錄可見(jiàn):明朝初年,所有移民信息幾乎都有詳細(xì)記載。冀州一帶是移民遷入地區(qū)之一,而不是移民遷出地區(qū)。最早的移民記錄是洪武三年遷徙蘇、松、嘉、湖、杭民之無(wú)田者四千余戶,這是在朱元璋統(tǒng)治的大后方進(jìn)行的。而許多認(rèn)同棗強(qiáng)移民的記載年代是洪武二年和洪武四年,是不符合歷史的。洪武二年到洪武四年正是徐達(dá)掛帥北伐期間,明朝廷統(tǒng)治尚未穩(wěn)定,無(wú)法實(shí)施大規(guī)模移民。而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移民598戶尚有記載,卻沒(méi)有棗強(qiáng)移民35 萬(wàn)相關(guān)記載,可見(jiàn)洪武年間棗強(qiáng)縣對(duì)外移民是不存在的。
與大槐樹(shù)移民、小云南移民到十九世紀(jì)才引起人們普遍關(guān)注不同,棗強(qiáng)移民在明代已經(jīng)被人提及。如明嘉靖年間的戶部員外郎李開(kāi)先曾經(jīng)指出:“章人由棗強(qiáng)徙居者,十常八九”。但是,我們查閱《明太宗實(shí)錄》發(fā)現(xiàn),在官方記載中,移民的流向恰恰與之相反。永樂(lè)元年十二月,刑部尚書(shū)郭資等奏報(bào):“真定棗強(qiáng)縣民初復(fù)業(yè),加以蝗災(zāi),流殍者眾。今天寒,祈遣人核實(shí),以施賑濟(jì)。”朱棣認(rèn)為當(dāng)?shù)亍懊窭绱耍瑵?jì)之如當(dāng)救焚拯溺,少緩即無(wú)及。”于是下令馬上遣官賑濟(jì)。朱棣的迅速反應(yīng)間接證明當(dāng)?shù)卮_實(shí)破損嚴(yán)重,亟需休養(yǎng)生息。《明太宗實(shí)錄》記載:“(永樂(lè)七年)六月庚午,山東安丘縣民邢義等言:本邑人稠地隘,無(wú)以自給,愿于冀州棗強(qiáng)占藉為民。從之。曾命戶部徙青州諸郡民之無(wú)業(yè)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戶。”這些記載證明明初的移民是從山東青州等郡遷徙百姓到冀州棗強(qiáng)縣。可見(jiàn),李開(kāi)先所指的“棗強(qiáng)”移民,要么是錯(cuò)誤的,要么是另一個(gè)“棗強(qiáng)”,而不是河北省棗強(qiáng)縣。
明嘉靖版《棗強(qiáng)縣志》和康熙版《棗強(qiáng)縣志》均沒(méi)有棗強(qiáng)縣對(duì)外移民的記載。
(二)從戶籍資料分析。據(jù)《元史·地理志》記載:棗強(qiáng)在元代屬于中等縣。至元三年元朝朝廷規(guī)定:“六千戶者為上縣,二千戶以上者為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結(jié)合真定路其他各縣人口規(guī)模多為“下”縣判斷,元代棗強(qiáng)的戶數(shù)應(yīng)該僅僅超過(guò)二千戶。《真定府志》載:棗強(qiáng)縣人口資料如下:洪武二十四年在冊(cè)1352 戶,7731 口;永樂(lè)十年,在冊(cè)1953 戶,9847 人。可見(jiàn),無(wú)論是在元代還是明初,棗強(qiáng)縣人口皆不及萬(wàn)人,其對(duì)外移民沒(méi)有人口來(lái)源支撐。
(三)再?gòu)拿鞒膽艏芾碇贫确治觥C鞒跄隇榱思訌?qiáng)戶籍管理和恢復(fù)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同時(shí)方便賦稅征收,朝廷禁止民戶遷徙。《明史》載:“太祖藉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shū)名、歲、居地。藉上戶部,貼給之民。有司歲計(jì)其登耗以聞……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藉復(fù)業(yè),賜復(fù)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愿歸者,令在所著藉,授田輸賦。正統(tǒng)時(shí),造逃戶周知冊(cè),核其丁糧。凡流民,英宗令勘藉,編甲互保,屬在所里長(zhǎng)管轄之。設(shè)扶民佐貳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又從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言,免流民復(fù)業(yè)者稅。”又載:“凡附藉者,正統(tǒng)時(shí),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本藉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fā)還。景泰中,令民藉者收附,軍、匠、灶役冒民藉者發(fā)還。”可以看出,明朝景泰年間之前戶籍管理相當(dāng)嚴(yán)格,所有逃難戶和流民即使在居住地有了戶籍,原籍在千里之內(nèi)的除限制條件以外的全部發(fā)還原籍。傳說(shuō)的棗強(qiáng)移民地區(qū)距離棗強(qiáng)縣不過(guò)幾百里,若有流民或難民必被遣返。因此棗強(qiáng)縣不存在難民遷徙到山東省北部。
(四)移民經(jīng)棗強(qiáng)縣中轉(zhuǎn)可能性排除。明朝初年山西移民經(jīng)由河北棗強(qiáng)中轉(zhuǎn)山東北部,也是不可能發(fā)生的。棗強(qiáng)縣位于山西洪洞縣的東北方向,同時(shí)位于山東省的西北方向,三地形如三角,棗強(qiáng)縣位于三角形之頂,假使真有山西洪洞縣移民遷徙,移民只會(huì)直接前往目的地,不會(huì)繞道西北數(shù)百里,再折往山東。況且洪洞縣大槐樹(shù)移民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大槐樹(shù)移民發(fā)生在金國(guó)統(tǒng)治時(shí)期的江蘇省邳州市,而河南省移民到山東北部更是無(wú)稽之談。
從以上史料記載分析,河北省棗強(qiáng)縣移民到山東省中北部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河北棗強(qiáng)”移民發(fā)生地必定另有源頭。
三、論證河北棗強(qiáng)移民發(fā)源地,必須明確兩個(gè)概念:“河北”和“棗強(qiáng)”
首先,我們必須分清“河北”和河北省。行省制度開(kāi)始于元朝,發(fā)展于明清。元朝時(shí)期朝廷設(shè)置中書(shū)省總領(lǐng)全國(guó)政務(wù),時(shí)稱“都省”。元朝在全國(guó)共設(shè)十個(gè)行省,即嶺北、遼陽(yáng)、河南江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而河北、山西、山東和內(nèi)蒙古等地則稱為“腹里”,由中書(shū)省直接管理。明朝開(kāi)國(guó)以后沿用的是元朝的行省制度。直到明太祖洪武九年改元朝之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又設(shè)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獄;都指揮使司掌軍政,合稱都、布、按三司。除京師、南京為明朝都城外,計(jì)有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十三個(gè)布政使司。京師(永樂(lè)十九年遷都順天府改為京師)又稱北直隸,南京在遷都北平后稱南直隸。此即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稱為十五省,為明直轄地區(qū)的行政區(qū)劃。元明兩朝不存在河北省,明朝洪武九年以前也沒(méi)有山西省。之前所謂的河南、河北指的是黃河以南和黃河以北,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河南省和河北省。同理,山東、山西指的是太行山脈以東和太行山脈以西廣大地區(qū),有別于現(xiàn)代的山東省和山西省。因此,河北棗強(qiáng)移民的“河北”,指的是“黃河以北”而不是河北省;其次,要明確“棗強(qiáng)”的概念。“棗強(qiáng)”可能是鄉(xiāng)、村、渡口名稱,可能是特定地名,也可能是“棗墻”,不能特指“棗強(qiáng)縣”。
四、邳州市岔河鎮(zhèn)良璧村是河北棗強(qiáng)移民發(fā)源地論證
邳州市位于江蘇省北部,屬于徐州市轄縣級(jí)市,邳州北部有三處國(guó)家級(jí)古人類文化遺址,分別是“大墩子文化遺址”、“劉林文化遺址”和“梁王城文化遺址”。邳州有六千余年的文明史,自古以來(lái)就是人類聚居區(qū),是江蘇文明發(fā)祥地之一。“其地北控齊魯,南蔽江淮,西走梁宋,東俯朐海。魏晉以來(lái)為重鎮(zhèn),蓋水陸之要沖,南北之襟喉。”北宋末年靖康之難后,金太宗天會(huì)七年邳州屬山東西路,1221-1223 年為山東行省所在地。元朝初年屬汴梁路,1271 年屬歸德府,隸河南江北中書(shū)省。明太祖洪武元年為南京中書(shū)省邳州直隸州,洪武四年改中都邳州直隸州。洪武十五年改南京淮安府邳州。邳州境內(nèi)北部有東西走向山地丘陵,其他大部分為平原,海拔多在21-25 米,地勢(shì)低洼平坦。邳州境內(nèi)河網(wǎng)密布,沂水、泇水、汶水、武水、大運(yùn)河、故黃河、古黃河穿境而過(guò),河湖縱橫交錯(cuò),古稱“洪水走廊”。
良璧,古稱羊陂,又稱良陂,位于蘇北魯南兩省交界處,現(xiàn)屬江蘇省邳州市岔河鎮(zhèn),民國(guó)前屬邳州偃武鄉(xiāng)。《唐書(shū)·地理志》記載的“十三陂遺址”指的就是良璧。村內(nèi)有大量歷代遺址、遺物,如古唐槐、唐貞觀五年興建的興化寺遺址和漢代石羊等,有6000 年以上文明史。《邳州志》記載:“梁王城北數(shù)十里為良璧,元時(shí)興化院在焉。碑所稱棟宇膠葛,樓觀櫛比。殆明以前一巨鎮(zhèn)。舊有僧坊、牙埠、牲畜四至,歲人常巨萬(wàn)。比年以來(lái),戶口彫攰,為狐兔所窟宅……。”可見(jiàn),明代以前良璧是個(gè)大鎮(zhèn),人口萬(wàn)人計(jì)。良璧是邳州市平原地帶海拔最高村之一,平均海拔在29-31 米。
論證邳州是河北棗強(qiáng)移民發(fā)源地,不得不提黃河“奪淮入海”。黃河在1194 年至1855 年以淮河的河道作為出海口。黃河曾有數(shù)次侵奪淮河流域,但為時(shí)較短,對(duì)淮河流域改變不大。唯1194 年第四次大改道后,淮河流域的豫東、皖北、蘇北和魯西南地區(qū)成了黃河洪水泛濫地區(qū)。《書(shū)經(jīng)·禹貢》載:“九河既道。”說(shuō)的是遠(yuǎn)古時(shí)候古黃河下游分九支入海,到齊桓公元年,“九河”已“塞其八流”。而曾經(jīng)的黃河九河形成的水系依然遍布下游地區(qū),邳州就是典型的黃泛區(qū)。古邳州城南是泗水,1194 年黃河改道之后,泗水稱為黃河。良璧村北黃河也是古代黃河分支之一。黃河雖然“九河塞其八流”,但黃河不時(shí)的改道造成的災(zāi)害屢見(jiàn)于史籍中。
正因?yàn)辄S河改道造成的災(zāi)難,才導(dǎo)致深受洪水之害的邳州百姓大量逃離家園。通過(guò)史籍分析,“河北棗強(qiáng)”移民時(shí)間段是公元1194 年至1213 年,人員來(lái)自于金國(guó)統(tǒng)治時(shí)期的邳州,具體分析如下。
1.黃河決口史料記載。《宋史·高宗紀(jì)》載:“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軍。”《五行志》載:“金明昌五年河決陽(yáng)武,注梁山泊,復(fù)分為二。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自建炎二年以后終金之世,率皆分支,南下徐、邳。迄元至元二十五年,始改趨陳穎,經(jīng)徐、邳凡百六十一年。”結(jié)合黃河“奪淮入海”的歷史可以看出,1128 年北宋名將杜沖決黃河水阻止金國(guó)軍隊(duì)造成的災(zāi)害只是暫時(shí)的,對(duì)下游造成的影響不是很大。而造成災(zāi)難性后果的黃河水患始于金明昌五年。這是河北棗強(qiáng)移民逃離邳州的起始時(shí)間點(diǎn)。
2.相關(guān)年代人口史料分析。《寰宇記》載:北宋崇寧年間邳州(北宋時(shí)期稱淮陽(yáng)軍,含下邳、宿遷二縣)有民76887 戶,154130 口。戶均2 人,通過(guò)查閱資料我們得到這樣一句話:“太祖乾德元年……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女口不須通勘”,以此來(lái)看,可知從宋太祖以來(lái),女性都沒(méi)有計(jì)入戶口。按照中國(guó)古代家庭構(gòu)成分析,一般是祖孫三代一起生活,以戶均5 口計(jì)算,推測(cè)出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 年)邳州人口超過(guò)38萬(wàn)。《金史》卷八十一載:“皇統(tǒng)二年,時(shí)邳州土賊嘯聚,幾二十萬(wàn),蒲里特軍三千,分為數(shù)隊(duì)急功之,賊潰去。”從本次農(nóng)民起義軍規(guī)模和被鎮(zhèn)壓分析,當(dāng)年的起義軍沒(méi)有組織性,也缺乏戰(zhàn)斗力,必然是邳州當(dāng)?shù)刎毧噢r(nóng)民。邳州在1142 年人口超過(guò)100 萬(wàn)人,20 萬(wàn)戶。推測(cè)理由:一是金國(guó)統(tǒng)治時(shí)期邳州管轄范圍增加了蘭陵縣。蘭陵縣在北宋崇寧年間是望縣,戶2 萬(wàn)余,約10 萬(wàn)人。因此北宋崇寧年間邳州(含下邳、宿遷、蘭陵)人口基數(shù)應(yīng)該約10 萬(wàn)戶、50 萬(wàn)人。二是四十年的人口自然增長(zhǎng),邳州人口超過(guò)100 萬(wàn)。到金明昌五年邳州原住民約30 萬(wàn)戶,150 萬(wàn)人。《金史》卷二十五載:“邳州,……戶二萬(wàn)七千二百三十二。”貞祐初年(1213 年)邳州戶籍統(tǒng)計(jì)資料顯示只有27232 戶,戶數(shù)比金明昌五年減少約27 萬(wàn)戶、135 萬(wàn)人。據(jù)邳州志記載:紹興十年宋金決戰(zhàn)于泇口鎮(zhèn)之后,到貞祐初年七十余年,邳州沒(méi)有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也沒(méi)有其他自然災(zāi)害記載,可見(jiàn)邳州人口減少的原因只能是黃河水患。因此,黃河改道邳州造成的難民逃離時(shí)間段為1194 年到1213 年之間。考慮朝廷統(tǒng)計(jì)戶口的滯后性,邳州難民逃離最確切年代應(yīng)該是公元1194 年至1200 年。
3.邳州是河北棗強(qiáng)移民來(lái)源地分析。《邳州志》記載,黃河決口之后,邳州是“洪水走廊”,邳州大部積水丈余,即平地積水三米多深。黃河之水從山東微山湖方向而來(lái),在邳州北部古黃河、中部運(yùn)河、南部黃河自西向東穿境而過(guò),匯入駱馬湖,之后向南流往淮河入海。每當(dāng)水災(zāi)來(lái)臨,西、南、東三個(gè)方向皆是洪水,人們只能選擇向北逃難,然后渡過(guò)北清河,逃往地勢(shì)高亢的山東省中北部。難民選擇逃往山東另一原因是山東是當(dāng)時(shí)最富裕的地方,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的長(zhǎng)三角地區(qū)。《金史》卷一百十七載:“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quán)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可見(jiàn),水災(zāi)期間,山東南部深受其害,只有逃往山東中北部才是最佳選擇。除了黃河水患,邳州水患還來(lái)自沂蒙山區(qū)。每當(dāng)汛期,沂蒙山區(qū)南部的雨水通過(guò)沂河、西泇河、東泇河等河流泄入邳州境內(nèi)。歷史上來(lái)自泇河的水災(zāi)最近的一次是1957 年7 月,邳州大部被山東客水淹沒(méi),幾十萬(wàn)人被轉(zhuǎn)移到附近的山上。
良璧村北有古黃河分支,一直被當(dāng)?shù)卮迕穹Q為“黃河”。河上有橋名“登龍橋”,又稱“石橋”。1855 年黃河改道之后,古黃河慢慢消失,該河道被改造成良田,現(xiàn)在只有遺跡“石橋窩”。邳州地方志記載可以佐證該河道的存在。《邳州志》載:“貞祐三年紅襖賊數(shù)萬(wàn)破邳州崗子崮,得船數(shù)百艘,將夸河為亂”。地方志記載:1215 年紅襖軍六萬(wàn)余人在良璧、崗子崮和楚墩一線與金軍交戰(zhàn),大敗金軍,繳獲戰(zhàn)船七百余艘,操練水兵,準(zhǔn)備攻打邳州城區(qū)的金軍。可見(jiàn)良璧古黃河戰(zhàn)略地位很重要。古黃河南岸有建于唐貞觀五年的興化院,當(dāng)?shù)卮迕穹Q“興化寺”或“大寺”,有庫(kù)房36 間,奉銅像26 尊。元至元十五年重修興化院碑記現(xiàn)存邳州博物館。北岸有建于北宋早期的天齊廟,天齊廟東有子孫堂、領(lǐng)官?gòu)R和貞姑奶奶廟,構(gòu)成“天齊廟群”。當(dāng)?shù)卮迕袢吮M皆知:“先有河南興化寺,后有河北大天齊。”說(shuō)的是興化院和天齊廟建造時(shí)間順序。良璧古黃河北岸千百年來(lái)有一道野生酸棗樹(shù)形成的天然屏障,被稱為“棗墻”。上世紀(jì)六十年代被砍伐時(shí)其長(zhǎng)度千余米,棗樹(shù)直徑約十厘米。《邳志補(bǔ)·物產(chǎn)》載:“酸棗,樹(shù)小實(shí)酸……一名橪,《說(shuō)文》:橪,酸小棗,叢生。邳多生于斷岸荒蕪,其仁入藥。”酸棗樹(shù)是叢生植物,其樹(shù)干和枝條長(zhǎng)滿一寸多長(zhǎng)的硬刺,只要長(zhǎng)成很難逾越,形成天然屏障,正如一堵墻壁。而其生命力特別頑強(qiáng),無(wú)論是刀砍和火燒,來(lái)年依然會(huì)茁壯成長(zhǎng),所以良璧人把這段“棗墻”稱之為“棗強(qiáng)”。邳州及其附近很多地名里有“棗”字。比如:山東省棗莊市,距離良璧不過(guò)五十公里;岔河鎮(zhèn)明清時(shí)期有古村落“棗林莊”,是良璧出村渡口,距離良璧僅二公里;村西有古地名“洪棗林”,現(xiàn)稱“洪林”;邳州有古地名“棗墩”;戴莊鎮(zhèn)有“棗莊營(yíng)”,距離良璧不過(guò)二十公里。
古代良璧是重要交通要道。《邳州志》記載:“(偃武鄉(xiāng))石埠社在城西北,疃上社在其西,有礓石、濤溝二河;石蘭社在城北少西。”石埠在良璧北偏東方向,距離約十五公里,其西北方向三公里處西泇河上有老鴣巷橋。通過(guò)調(diào)查走訪當(dāng)?shù)乩夏耆耍摱魏拥拦糯Q為老鴣巷河。老鴣巷橋又稱老鸛巷橋,原名中濟(jì)橋,是邳州跨越西泇河的唯一橋梁。始建于唐代,再建于明代天啟七年,明代大橋毀于上世紀(jì)四十年代,現(xiàn)老鴣巷橋位于原橋址北約500 米,為郯夏公路的重要橋梁之一。古代出邳州進(jìn)入蘭陵的西北通道就是從良璧去往老鴣巷橋,然后北上山東各地。黃河“奪淮入海”期間,每當(dāng)洪水來(lái)臨,沂河與西泇河之間的廣大地區(qū)大部被水淹沒(méi),難民北上必然途經(jīng)地勢(shì)高亢的良璧。良璧有兩處善堂安頓難民:北門(mén)善堂建于北宋初年;西門(mén)善堂建于北宋中期。邳州僅有十五處善堂,良璧占其二,充分證明良璧交通重要性。可見(jiàn),黃河在1194 年改道邳州,邳州的先民們家園被洪水摧毀,莊稼失收,人們不得不北上逃離故土。而逃離的路徑就是從邳州各地沿官道北上,途經(jīng)良璧村的登龍橋跨過(guò)古黃河。而黃河水面寬闊,只有北岸的“棗樹(shù)墻”為難民指明了道路,防止人們跌落河中,這段棗樹(shù)墻成了渡河難民的“救命墻”,因此“河北棗強(qiáng)”深留在難民及其后裔記憶中。越過(guò)良璧古黃河之后再沿村西老鴣巷河?xùn)|岸北上。章丘縣的張氏族譜記載其始祖遷徙于金章宗承安四年才是真實(shí)可信的,與黃河改道難民北上年代相吻合。
良璧附近金、元時(shí)期消失的古村落可以佐證黃河改道造成邳州先民的遷出。臺(tái)前莊,位于良璧興化院東北二公里,始建于西漢,面積40 畝;小臺(tái)子,位于良璧興化院東一公里,始建于西漢,面積25 畝;譚王莊,位于天齊廟西,始建年代不詳,面積30 畝;無(wú)難莊,位于良璧東三公里,始建于隋初期,面積50 畝;皇甫村,位于興化院西,始建于唐初期,面積70 畝。這些古村落位于良璧古黃河兩岸,海拔高度相對(duì)較低,消失于金元時(shí)期,邳州其他地區(qū)受到的水害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公元1194-1213 年之間,邳州先民因黃河水災(zāi)逃難山東中部和北部,逃離時(shí)經(jīng)過(guò)良璧村古黃河北岸的“棗強(qiáng)”,逃難人口約135 萬(wàn)。
幾乎所有棗強(qiáng)移民后裔都說(shuō)自己的祖先來(lái)自明洪武二年和四年的直隸州。邳州在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期間是直隸州,而冀州是在朱棣遷都北平之后才升為直隸州,兩地時(shí)間差五十余年。因而移民后裔所謂的始祖來(lái)自“直隸州”只可能是邳州,而不會(huì)是冀州。黃河改道年代正是金國(guó)統(tǒng)治末期,政局動(dòng)蕩,宋、金、元戰(zhàn)爭(zhēng)不斷、“紅襖軍”農(nóng)民起義等戰(zhàn)爭(zhēng)此起彼伏;加之終元之世,元朝廷征討四方、政局不穩(wěn),加之黃河水患、“紅巾軍”起義、元明戰(zhàn)爭(zhēng)等等,曾經(jīng)的難民一直沒(méi)有得到戶籍。直至明朝建立,百?gòu)U待興,朝廷實(shí)行戶籍登記制度,之前的難民才會(huì)取得合法戶籍,有關(guān)地區(qū)才會(huì)有始祖于洪武初年從直隸州遷入的傳說(shuō)。結(jié)合部分移民是大槐樹(shù)移民經(jīng)過(guò)棗強(qiáng)中轉(zhuǎn)之說(shuō),而邳州良璧是“大槐樹(shù)移民”發(fā)源地,恰恰印證了棗強(qiáng)移民來(lái)自邳州。
“大槐樹(shù)”是良璧村內(nèi)數(shù)棵唐代槐樹(shù);“棗林莊”是良璧東南出村渡口;“老鴣巷”是良璧村西泇河舊稱。正如“偃武鄉(xiāng)大槐樹(shù)移民”、“山東棗林莊移民”、“老鴣巷移民”一樣,“河北棗強(qiáng)”不過(guò)是良璧古黃河北岸的棗樹(shù)林,這些特定名稱不過(guò)是移民遷徙路途上的關(guān)鍵記憶節(jié)點(diǎn)。之后的數(shù)百年來(lái),不同地區(qū)的移民后裔關(guān)于移民遷徙路線記憶的側(cè)重點(diǎn)不同造成了不同的遷徙名稱。這些移民來(lái)源地都在江蘇省邳州市及其附近地區(qū)。前者是1214 年后紅襖軍農(nóng)民戰(zhàn)爭(zhēng)造成山東和蘇北難民南下,是難民后裔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表述;而“河北棗強(qiáng)”移民實(shí)質(zhì)是黃河水患造成的邳州災(zāi)民北遷。“河北棗強(qiáng)”移民早于前者約十五年,不排除同一時(shí)期逃難到北方各地難民自稱是“大槐樹(shù)移民”。歷史上途經(jīng)良璧村的大型移民有兩次:第一次是公元1200 年前后的黃河改道造成的難民北上,難民遷徙方向是由南向北,包括“河北棗強(qiáng)移民”和“大槐樹(shù)移民”,移民主要來(lái)源于金國(guó)統(tǒng)治時(shí)期的邳州,人數(shù)約135 萬(wàn);第二次是1214 年到1219 年的紅襖軍與金國(guó)戰(zhàn)爭(zhēng)造成難民南遷,包括“偃武大槐樹(shù)移民”、“老鴣巷移民”和“山東棗林莊移民”,難民來(lái)源于山東大部,遷徙方向是由北向南,人數(shù)達(dá)數(shù)百萬(wàn)。各類自然災(zāi)害和戰(zhàn)爭(zhēng)摧殘著飽經(jīng)磨難的先民們,曾經(jīng)見(jiàn)證難民艱辛的“大槐樹(shù)”、“棗林莊”、“老鴣巷”和“棗強(qiáng)”依然存在于邳州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