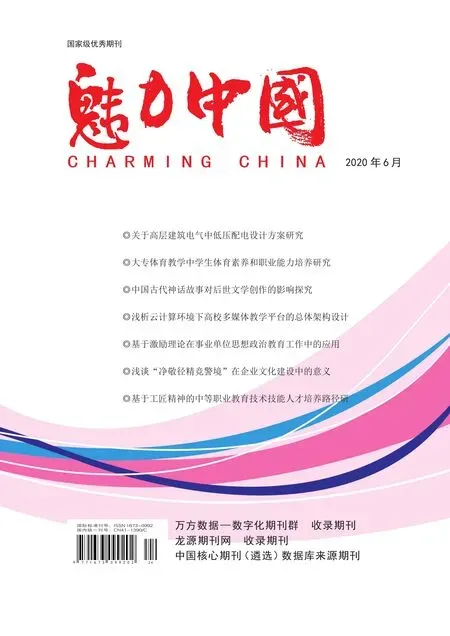《失明癥漫記》的主題淺析
宋超
(山西大學(xué)商務(wù)學(xué)院,山西 太原 030031)
在一個(gè)與往昔如常的日子,在一個(gè)與昨日相較沒有任何改變的十字路口。一位駕著私家車的男子,在紅綠燈的注視下。他大聲呼喊著,咆哮著:我瞎了,我瞎了。此刻這位男子仿佛處在了秋日濃厚的大霧之中,仿佛處在了被牛奶占據(jù)的大海之中,眼前白茫茫一片,除卻可以感受到一絲光線外,他對這個(gè)世界已經(jīng)全然無知了。
在一位本意為幫助他,開他的車送他回家的男人,由于看他處于失明狀態(tài)下賊心大起后成為偷車賊。妻子回家后帶他去一位眼科醫(yī)生的診所看病。在這之后的短短幾日里,第一位失明的人的妻子和偷車賊,以及眼科醫(yī)生包括同去找眼科診所的一位年輕女子、戴眼鏡的老人,斜眼男孩都失明了。但神奇的是唯獨(dú)醫(yī)生的妻子沒有失明。
失明竟然可以歸為傳染疾病,只不過與普通傳染疾病不同的是,失明是通過目光的接觸傳染的。薩拉馬戈構(gòu)建了一個(gè)盲人的世界,通過陌生化的表達(dá)方式賦予了一種強(qiáng)烈的真實(shí)感。就如薩拉馬戈本人所說:“歸根結(jié)底,這部小說所要講的恰恰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理智上成了盲人”。盲人們面對困境,是像動(dòng)物一樣活著還是選擇勇敢的做人?盲人們怎么才能走出困境呢?怎么才能走出黑暗迎來光明呢?
一、困境——文明消失、獸性回歸
薩拉馬戈大量描寫了失明后人們的困境和人性的崩塌,以及文明墮落和自尊的消失。《失明癥漫記》超越了時(shí)代、國界和人種,把人類在災(zāi)難下的百態(tài)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也讓我們在黑暗之中看見了光明。
伊始,該國為了扼制失明癥的擴(kuò)散。將所有失明的人和同失明者有過接觸的人,全部遷入一座破舊的精神病院。醫(yī)生的妻子,由于舍不下醫(yī)生。就謊稱自己也失明,陪同醫(yī)生一同關(guān)入了精神病院。神奇的是,醫(yī)生與其妻子、戴墨鏡的女孩、戴眼鏡的老人、偷車賊、第一位失明的人與他的妻子,分入了同一間宿舍。
起初,人還不是很多,食物也可以得到充足的供應(yīng),政府每天都會(huì)通過廣播鼓舞這些盲人犧牲自己去愛護(hù)這個(gè)國家。后來人越來越多了但是食物得不到補(bǔ)充,宿舍也越來越擁擠。人們?yōu)榱藫寠Z食物采用了武力,而政府的士兵為了防止被傳染,也對盲人們規(guī)定了活動(dòng)范圍。
失明使得盲人們的生活產(chǎn)生了諸多困難,由于看不見行動(dòng)不便,并且也沒有好脾氣好耐心去找?guī)と藗冮_始隨地大小便。因?yàn)樗械娜硕际髁耍簿蜎]有必要去也顧忌羞恥。慢慢地整個(gè)精神病院遍地都是排泄物,臭氣熏天,大家像動(dòng)物一樣活著。
在獸性回歸之后,叢林法則也到來了。這時(shí),人類歷經(jīng)艱辛,用勞動(dòng)和拼搏建立起來的文明和道德,遇到了重大危機(jī)。
二、走出困境——愛、自尊
薩拉馬戈為這群失明的人們留下了唯一的光明。醫(yī)生的妻子,作為這部小說中唯一沒有失明的人。她的存在給這個(gè)悲痛的故事帶來了一絲溫暖。她給予者同屋的盲人們母親般的愛,她給予盲人們堅(jiān)強(qiáng)下去的力量。她對這群盲人說:“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人那樣生活,那么我們應(yīng)當(dāng)盡量不完全像動(dòng)物一樣生活”。盲人們也以此為原則,他們沒有迷失自己沒有失去自尊,這為他們回歸人性奠定了基礎(chǔ)。
醫(yī)生的妻子引領(lǐng)盲人們?nèi)ド蠋鶐椭麄兦逑瓷眢w,帶領(lǐng)他們閱讀來保持理智。在精神病院的女人們被由一個(gè)持槍盲人領(lǐng)導(dǎo)下的盲人團(tuán)體壓榨。正所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們團(tuán)結(jié)起來,除去了該團(tuán)體首領(lǐng)后,點(diǎn)燃了精神病院并且逃離了。逃離出去后,在這個(gè)地獄一樣的世界里,醫(yī)生的妻子為他們找來了食物和換洗的衣服,用她的堅(jiān)忍和博愛之心勇敢地引導(dǎo)著盲人們一步一步重建著做人的尊嚴(yán)。在大雨之下,他們回歸了文明的人類世界。
最后,人們突然間恢復(fù)了視力。可是復(fù)明后的城市卻不是失明前的樣子了。隨著恢復(fù)的視力讓我們懷疑:曾經(jīng)失明過,現(xiàn)在能夠“看”的人們會(huì)不會(huì)去“看見”?
三、結(jié)語
失明之后的人不僅失去了光明,他們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理智、倫理、道德。留下的只有求生欲望和依舊強(qiáng)烈的本性。文明和人性在大災(zāi)難下的極其脆弱。但是災(zāi)難一旦過去文明就會(huì)重生,人性就會(huì)回歸。但文明的重生和人性的回歸是需要建立在災(zāi)難下的依舊不放棄愛與自尊的基礎(chǔ)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