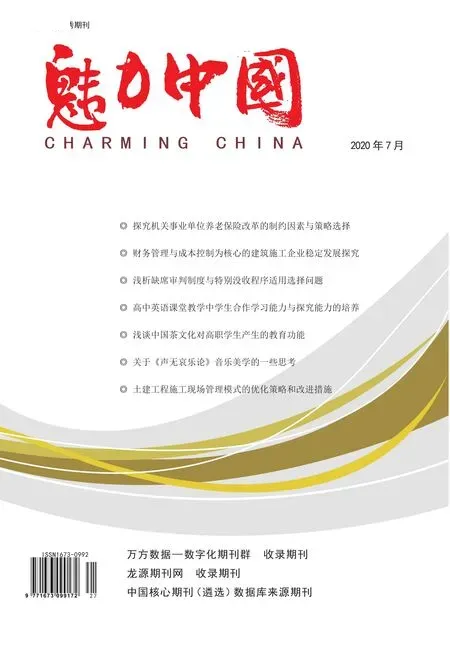英漢口譯教學(xué)選材之口音語(yǔ)料選擇
——“世界英語(yǔ)”模型指導(dǎo)下的口音難度實(shí)證研究
(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qū)永興中學(xué),浙江 溫州 325000)
口譯作為一項(xiàng)國(guó)際性交流活動(dòng),其涉及的講話人來(lái)自各個(gè)國(guó)家及各個(gè)語(yǔ)言背景。在一定情況下,鑒于英語(yǔ)在國(guó)際舞臺(tái)上的重要地位,講話人只能選擇使用“英語(yǔ)”這個(gè)“國(guó)際活動(dòng)與會(huì)議中的主導(dǎo)語(yǔ)言”(王勝蘭,2010:1)進(jìn)行發(fā)表和講話。因此,口譯譯員不可避免地會(huì)接觸到非英語(yǔ)標(biāo)準(zhǔn)發(fā)音(non-RP)或非通用美音(non-GA)的英語(yǔ)口音變體。為了在口譯任務(wù)中更好地應(yīng)對(duì)此類英語(yǔ)口音講話,口譯譯員須首先具備國(guó)際視野,提高對(duì)non-RP或non-GA 的英語(yǔ)口音變體的重視,盡可能多地了解不同英語(yǔ)口音的音位變化特點(diǎn),并合理地選擇口音語(yǔ)料進(jìn)行譯前準(zhǔn)備。對(duì)學(xué)生譯員而言,也是如此。
針對(duì)上述現(xiàn)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試圖從口音入手,通過(guò)實(shí)證研究不同口音對(duì)口譯表現(xiàn)的不同影響,從而結(jié)合“世界英語(yǔ)”模型對(duì)英語(yǔ)口音進(jìn)行難度排序,尋找英語(yǔ)口音難度規(guī)律。
一、口音與世界英語(yǔ)模型
(一)口音定義
影響口音形成的因素眾多,除了母語(yǔ)影響造成的語(yǔ)音差異之外,地理因素、社會(huì)因素、教育普及度等都對(duì)英語(yǔ)口音形成存在影響。
根據(jù)《柯林斯高級(jí)英語(yǔ)詞典》,口音指講話人在講話時(shí)擁有的獨(dú)特發(fā)音,而這種發(fā)音的獨(dú)特性可以反映講話人的國(guó)籍和社會(huì)背景等。從二語(yǔ)習(xí)得角度來(lái)看,Southwood 和Fledge(1999:335)講口音定義為“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產(chǎn)生的一種非病理語(yǔ)音,而該非病理語(yǔ)音以一定系統(tǒng)方式不同于語(yǔ)言本土講話者語(yǔ)音特征”。
(二)世界英語(yǔ)模型
隨著“世界英語(yǔ)”議題的提出,Braj B.Kachru(以下簡(jiǎn)稱為“凱齊盧”)于1985 年提出“世界英語(yǔ)”模型,以更好地像全世界呈現(xiàn)英語(yǔ)的區(qū)域性變體。該模型至今仍是全球英語(yǔ)變體分類的重要參考模型。凱齊盧的“世界英語(yǔ)”模型依據(jù)“英語(yǔ)的傳播類型、習(xí)得方式和跨語(yǔ)言和文化的功能領(lǐng)域”將全球英語(yǔ)變體分布?xì)w類到以下三圈——內(nèi)圈、外圈及拓展圈(詳見(jiàn)圖1)(1986:12)。該模型表明,在全球范圍內(nèi),非英語(yǔ)母語(yǔ)講話人的數(shù)目龐大且英語(yǔ)變體(或英語(yǔ)口音)眾多。
二、口音難度實(shí)證研究
為了幫助口譯教師在不同口譯教學(xué)階段選擇不同口音難度的英漢口譯語(yǔ)料,從而盡可能使英漢口譯教學(xué)效果最佳化,本章節(jié)旨在結(jié)合凱齊盧的“世界英語(yǔ)”模型,通過(guò)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英語(yǔ)口音難度的難度梯級(jí),為英漢口譯語(yǔ)料選擇提供參考。
(一)實(shí)驗(yàn)問(wèn)題
本文試圖在凱齊盧“世界英語(yǔ)”模型指導(dǎo)下通過(guò)英語(yǔ)口音難度的實(shí)證研究尋找以下問(wèn)題的答案:
1.學(xué)生譯員在初次接觸不熟悉英語(yǔ)口音時(shí),其口譯表現(xiàn)是否會(huì)因不同的英語(yǔ)口音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2.如果學(xué)生譯員的口譯表現(xiàn)會(huì)因英語(yǔ)口音的不同而受不同程度的影響,那么英語(yǔ)口音難度和凱齊盧提出的“世界英語(yǔ)”模型中的三圈是否相關(guān)?
3.如果英語(yǔ)口音難度與“世界英語(yǔ)”模型不相關(guān),那么英語(yǔ)口音難度有何規(guī)律可循?
(二)實(shí)驗(yàn)對(duì)象與材料
本實(shí)證研究共邀請(qǐng)16 位學(xué)生譯員作為被試。該16 位被試均來(lái)自上海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大三的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學(xué)生已完成為期兩年半的專業(yè)課程學(xué)習(xí)與近四個(gè)月的交傳口譯訓(xùn)練。考慮到被試的英漢交傳能力,本實(shí)驗(yàn)通過(guò)音頻編輯軟件,將聲明的語(yǔ)速調(diào)整至100 至120 詞每分鐘,符合Gerver(1976)和Seleskovitch(1965)(轉(zhuǎn)引自伍志偉,2008:22)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最適合英漢會(huì)議口譯譯員的語(yǔ)速。此外,為排除其他干擾項(xiàng)對(duì)實(shí)驗(yàn)結(jié)果的影響,本實(shí)驗(yàn)通過(guò)編輯,控制聲明中的長(zhǎng)難句占比和數(shù)字詞匯占比,盡可能使口音作為實(shí)驗(yàn)唯一變量。
(三)實(shí)驗(yàn)步驟與評(píng)分標(biāo)準(zhǔn)
本實(shí)驗(yàn)由以下五步驟組成:
第一步,邀請(qǐng)16 位本科大三英語(yǔ)專業(yè)學(xué)生作為被試參加實(shí)驗(yàn);
第二步,實(shí)驗(yàn)開(kāi)始前,告知被試本實(shí)驗(yàn)將涉及不同英語(yǔ)口音,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時(shí)間讓被試做好心里準(zhǔn)備并減少焦慮對(duì)實(shí)驗(yàn)結(jié)果的影響。同時(shí),為所有被試提供相關(guān)的話題信息(中文)和話題所涉及的英漢對(duì)照表達(dá)表,從而盡可能減少背景知識(shí)對(duì)實(shí)驗(yàn)結(jié)果的干擾;
第三步,十分鐘準(zhǔn)備時(shí)間后,提醒被試在實(shí)驗(yàn)隔間內(nèi)佩戴好耳機(jī),調(diào)整話筒位置,準(zhǔn)備好筆記所需工具,隨后進(jìn)行英漢交替?zhèn)髯g。五篇聲明將以同樣的順序呈現(xiàn)給被試,每個(gè)聲明分為小節(jié),每小節(jié)句子1 至三句不等;
最后,整理分析實(shí)驗(yàn)數(shù)據(jù),驗(yàn)證試驗(yàn)假設(shè)并尋求實(shí)驗(yàn)問(wèn)題答案。
(四)實(shí)驗(yàn)結(jié)果
通過(guò)數(shù)據(jù)采集與分析后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都是不熟悉口音,但是不同英語(yǔ)口音對(duì)學(xué)生譯員而言難度存在差異。其中,被試口譯表現(xiàn)得分以澳大利亞英語(yǔ)口音(內(nèi)圈)、日本英語(yǔ)口音(拓展圈)、南非英語(yǔ)口音(外圈)、印度英語(yǔ)口音(外圈)和希臘英語(yǔ)口音(拓展圈)依序下降,這也就意味著這五種英語(yǔ)口音的口音難度依序上升。
三、結(jié)語(yǔ)
本文通過(guò)實(shí)驗(yàn)研究初步發(fā)現(xiàn),英語(yǔ)口音難度與凱齊盧“世界英語(yǔ)”模型存在相關(guān)性:英語(yǔ)口音難度與模型中的圈層分布(內(nèi)圈-外圈-拓展圈)呈正相關(guān);而對(duì)于同一圈層內(nèi)的英語(yǔ)口音,其難度與輔音偏移比例呈正相關(guān)。結(jié)合實(shí)驗(yàn)結(jié)果,本文提出了“口音定位”策略與“語(yǔ)音偏移比較”策略以供口譯教師在進(jìn)行英語(yǔ)口音語(yǔ)料選擇時(shí)作參考。
然而,由于英語(yǔ)變體數(shù)目之龐大,比較而言,本實(shí)驗(yàn)研究涉及的英語(yǔ)口音種類還較為單薄,因此,經(jīng)過(guò)實(shí)驗(yàn)獲得的數(shù)據(jù)和結(jié)果僅是初步發(fā)現(xiàn),仍需要未來(lái)的相關(guān)研究予以發(fā)展和進(jìn)一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