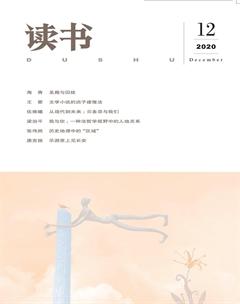音樂和詩篇喑啞的時刻
夏夜清
“后來,偶爾在暮色朦朧的時刻,我一個人坐在音樂室里,還會聽見那看不見的雙手彈奏出來的陌生的樂曲。”( [德]施泰凡·赫爾姆林:《暮色集》,張黎譯,商務印書館二0一五年版)
后來,常常憶及這些文字。譬如夜半醒來,或深為某個曲子浸染后,心間總會浮現這位父親。對我來說,他久已與愛德華·蒙克畫作中那透出深沉力量的男子重疊在一起了。那是在黃昏將逝或已逝時一個立于窗前的男人的側影,周遭素樸而光景幽暗,窗外獨有一艘火光熠熠的船在海上駛過。這幅畫曾多年懸置于父親的寫字臺上方。
其實這“看不見的雙手”來自作者的叔叔,這是個無以負擔世故繁雜獨為音樂所俘虜的人,他后來自殺了。這個異常害羞的人有著怎樣的善良啊,他從不會大聲說一句話,即便對他人略帶嘲諷的致意,也會纖柔以答。他總低垂著眼瞼,羞慚于有雜質的目光與聲音,抑或如作者所言,在他身上從無與善、愛不相容的品質。父親喜愛他,供養他,當他從遠方帶來新異的音樂時,就不啻為一個節日。兩個男人總會待在房間里相對良久。而為了達到一種更深入的交流,他們便彈起舒伯特F 小調幻想曲或其他四手聯奏曲……
可是在我,這兄弟倆總是幻化為一個人,只不過同樣充溢著音樂才智的哥哥奮力直面了人世之煩難,雖則那絕非一般的煩難。其實,他恐懼看到這個世界的爭斗,因之每每心馳山之巔、海之淵、深長的來路與祖輩的家園,直至駐足于一派恒久靜謐的世界。他是如此沉溺其間,以致當人們想與之交談,思緒回返現實的旅程總需要雙倍的時間。繼而,伴隨著不安,他的目光會充滿驚懼。仿佛這個世界依然陌生,也或許是猶太人漫長的逃亡間淤積的血液之反射吧。那是一片美神的領地,或許只有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二自我”方能馳騁其上。這是一個敏感的心靈方能有的第二自我。而在那獵犬狺狺的時代,那片原野無疑愈加悠遠了。
恍若已然化作了生命的韻律與姿勢,這投向遠方的遐思如此令人神往,以致我總想要用語言塑立他。只是通往舊日的路已然寂寥,希求在德語藝術的史料間追尋他更多的蹤跡很難,最終只能在作者的書頁間摩挲。我總難忘懷這些閃現他身影的篇章:《父子情》《弗雷迪》《赫伯特叔叔》《藝術觀》,總想跟人們說一說這位父親。這是一個有著怎樣美好風儀的人呢?瘦削、儒雅、沉靜、安詳,不喜形于色,可在深愛的人面前依然會有矜持的喜悅,神態疏遠卻不失親切和藹。粗糲的語言難傳達一二,當重讀這些篇章時,縱然看到他總坐在鋼琴前,卻依然如隔夏日的陰影。
他這一生,鋼琴陪伴的時間太多了。在那有些陽光灑落的拂曉,每天的序曲,總是從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這部音樂里的《舊約》開始的,他幾乎總在與自己的“第二自我”交談著。他有著溫柔敦厚的心,雖然在經濟領域也同樣出色,可那卻像身著粗鄙的衣服表演,他終難忘卻藝術。仿佛是個要不時穿上音樂鎧甲的人,一旦音樂消失,就會深感不安,像陷入了赤身露體的境地。他一生與鋼琴相伴的日子是那樣不尋常的密集,這使之超越了一般演奏家的專業水準。實際上,對鋼琴文獻他跋涉得既廣且深,足以擔當音樂會上出色的鋼琴家。在一個為他鄙視的時代,是音樂賦予了他對人的情感。直到人們紛紛遠離他,遠離他的家庭室內樂,包括從前他曾相助的很多有才華而困頓的藝術家。是音樂攜他橫跨了幽暗的原野、帶來寧靜的尊嚴。音樂也喚起了深邃的愛。它們如此細微,而他不知道,在孩子心里,這涓滴之愛已激起如何的回響。
人們幼年大概都有這樣的經驗,當家里來了陌生之客,自己往往是失落的,甚至不能隨便言語、上桌吃飯。孩子是那么無足輕重,那時即便是真愛他們的人,大概也不會過多在意其感受。作者童年時,家里就常有客人來,為了表達對父親的禮貌,人們當然會對他親切一番。可即便是些很斯文的藝術家,之后也仍然忽視他。但有一回,父親正與別人交談時,卻突然注視著角落里的他,隨之握住他的手換到旁側房間,將他摟在懷里,輕輕地吻他。那真是一個甜蜜又令人驚訝的瞬間,作者后來回憶,當父親把他放在地上,他發現,父親的眼里有淚水。當時他想到了什么呢?也許這里很有一種憐愛與期許存在,他知道,孩子一定感到自己受了冷落。這撥動了他內心最隱秘的琴弦,他知道孩子終將成為男子漢,會經歷很多險阻。為了人世所有那些苦辛,現在他要把孩子抱在懷里……
那是父親在孩子面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淚。他總樂于肯定教育,盡管有時也非內心所愿。當發現小兒子愛飛機,他就說:“如果你愿意,弗雷迪,你一定會成為飛行員的。”因為在“一戰”前后就飛行過的他看來,擺脫大地遠觀家園可不簡單。他當然更想讓孩子從事高尚的科學或藝術,對孩子的藝術表現他向來是不吝褒揚的。這多么不同于卡夫卡的父親,同為世俗化的猶太人,他并不擔心孩子從事饑餓藝術家的職業:
有那么幾天,父親把我喚到家中最大的房間,那里置放著收藏版畫作品的玻璃櫥,櫥里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所有他無法掛在墻上的版畫散頁。我父親尤其喜歡搜集十九世紀初期以來德國繪畫大師的作品,顯然他也收藏著許多其他的繪畫。他指給我看卡斯帕爾·達維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素描的一個細部,隆格的一張畫頁,布萊欣的一幅矯飾派風格的習作。他偶爾說上一兩句話。我總感到,他相信我樂意理解他、樂意理解他指給我看的那些藝術家的作品。我們周圍籠罩著一片寧靜、贊賞和幸福的氣氛。透過玻璃窗灑下來一抹黯淡、美麗的陽光。今天我知道,他那不多的話語,他的指指點點,對于我來說,比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重要得多,那些理論后來長時間地糾纏得我不可開交。他的沉默教會了我寬容。可我們那時卻生活在不寬容的時代。
這種置身藝術之境所獲得的美與安寧歷歷如真。相反,縱然二十世紀藝術理論層出不窮,可作者卻未找到普適的法則。在他看來,人們把已然遠離了真切感受的理論當作被證實的科學,是太過絕對的。可多少人能像王國維那般雖借助理論卻又從生命的體驗去評注作品呢?正像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已遠離了藝術原初的光暈,諸多理論又何嘗未陷入另一種“復制”?從理論到理論,仿佛愈加成為知識本身的追求。因之,這位情感深邃,有著音樂、文學與繪畫的多重素養,卻未曾失卻對作品最初的驚異與欣喜的父親方如此珍貴。他并不期許孩子改變世界,卻但愿他們在完善自我上竭力而為。當德國猶太人江河日下的時刻,作者勸父親去國外,他卻微笑著安慰說,德國是一座舒適的監獄。他問孩子需要什么,繼而勸其去劍橋,而作者卻說為了德國革命要與工人在一起。父親沉默了,繼而這場父子間的分歧又消融在莫扎特的奏鳴曲里。可是,何以不能如父親所愿呢?說到這里我們也該來認識這位作者了。
施泰凡·赫爾姆林(Stephan Hermlin),猶太德語詩人,共產黨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訪華,隨后留下的篇章有個美麗的名字:《遠方的近鄰》。《暮色集》是其晚年心曲,出版于一九七九年。這位還是中學生時就在街頭加入了共青團,終其一生對共產主義抱有虔敬的人是那么真純。他把蘇聯的弊病也視為從前腐敗社會、戰爭與內戰的遺患。然而人們卻不應苛責于他,進而懷疑最初部分共產黨人的純潔氣質,存在種種弊端的蘇聯在他所以無法想象,與其說是信仰使然,不如說同樣是獨立之精神的體現。他引用羅莎·盧森堡的話:社會主義與暴行是完全不可調和的。他后來也意識到,自己在意識形態的禁錮下,造成了對一些作家的拒絕。譬如很早聽聞并一同在西班牙戰斗的奧威爾,當他終于讀了他的書,看法就完全改變了。就像西蒙·里斯所強調的,不要以為奧威爾是反共的,他對蘇式極權主義的批判正是基于社會主義信念。因之,貝爾納– 亨利·雷威說他是一位斯大林派作家是有失恰當的。時值柏林墻倒塌,這位德里達的學生、法國新哲學的代表訪問柏林,在那篇對赫爾姆林的訪問里,怕是有著令人驚異的表達,然而談及為之忠誠一生的社會主義,他卻坦承赫爾姆林之所想與專制主義名下的一切毫無關聯。
正是有了這塊基石,《暮色集》依然不失為一本理想之書。它無非是一個有著藝術稟賦的人與人類憧憬相遇的結晶,其間它們是如此驚人地達至了美妙的統一,人們又如何感受不到這理想之美呢!而它的至為超凡之處便是語文表達。本書開篇即引用卡夫卡頗心儀的作家羅伯特·瓦爾澤的詩句:“細看暮色中的路,那是家鄉的路。”似乎已經預示了這首先是一部深具“氛圍”的現代之書,因為瓦爾澤是一位感受銳敏的作家。赫爾姆林早年閱讀時就把氛圍看得高于情節,這可以說是把握住了敘事作品所必需的精髓。一部好的作品必然具備濃濃的氛圍,它是一個世界,會把人納入其間,時時徜徉其上。即便是《共產黨宣言》,作者十三歲初識它時,依然首先是它詩意的風格而非思想讓其迷戀,以致對其意義把握并不精準——其間意味深長的是,五十歲后方驚覺,在這本至少讀過二十余遍的書里,他一直將“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攸關的話理解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如是認知恰如我國學人何兆武先生早年讀此書的感受,看來《宣言》 一書確是深具美學感染力的。《暮色集》又何嘗不是?人們也許很難理解它,在一些論家看來,那些無產階級作家無非是底層的土包子,根本不懂藝術。可赫爾姆林卻一點不似穿制服的作家,即便未曾入過大學。因為他來自一個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有一位不同凡響的父親。這里革命進入的是一個真正的藝術之國,其間雜糅著的戰爭與鮮血,是用夢幻與繪畫的空靈,乃至遠赴音樂的境界掇拾語言加以表現與彌合的。因此,作者所以被譽為海涅以來德國文學里最卓越的散文作家,也絕非因其斗爭哲學了。這位寧可一生只寫六行可立此存照的詩句而不愿全部詩篇都鐫刻在大理石上的人,也許在詩歌領域無法比肩他的同志艾呂雅、聶魯達—赫爾姆林譯過他們的詩—至少在散文上還是做到了。而這部形態卓異的書也不必句句刻上大理石,它們最動人的部分,依舊是殘酷的時代之下,關涉親情的那些感人至深的篇章。
弗雷迪怎樣了呢?這個在作者夢境之海上一直漂浮著的年輕人,我不相信凡讀到這篇作品的人會不喜愛他, 會感受不到他深情而欣悅的微笑。仿佛對世界有著不疲倦的驚訝,在他手上,一只甲蟲或蝸牛,都有自己的祈愿;一片秋葉,都像能聽到葉脈的濤聲。對身邊的事物他向來都有著非凡的關注,更不用說摯愛的飛機,他總會緊緊盯視著它,目光嚴肅而經久。女人們似乎都為他所吸引,后來在英國加入盟軍,戰友們都叫他童星(Starlet)。該如何想象富于溫情的他,轟炸祖國時的心境呢?他勇敢地犧牲了,而在幼年,當哥哥要切開他們共同養的金魚,看看它們的內臟結構時,他卻說:“你不能這樣做,它們都是生靈。”他留下的筆記流溢著對故園的眷念。這個放棄了提琴的學習,沒有在藝術的山脊上挺進的孩子,心靈卻展現出別樣瑰麗的光華。在留給哥哥最后的信上他說,希望自己投身的這場戰爭是人的最后一次戰爭,他描寫了自己同各民族死者躺在一個無涯的房間……
這不是參加過“一戰”的父親所希求的嗎?可孩子們仍然無謂地被卷入其間了。人們將恒久地生活在兩次戰爭之間嗎?作者未曾忘懷父親唯一打他的一次,那是在幼年的餐桌上,當他說德國有權收回阿爾薩斯-洛林這塊在法德間多次易手、“一戰”后尤讓德國蒙羞的土地時。只是稍晚他方才驚覺,父親對“戰爭”這一話題的禁忌,這會讓他陷入哀傷與無言。他把“一戰”獲得的勛章隨意給孩子們玩,卻禁止類似士兵的游戲。然而,作為一代已然世俗化且渴求被同化的猶太人,這個祖國卻憎恨他們。
父親知道那是一個離別的時代,每一天,人們站在高高的帆檣上向遠方的親人揮別。其實不說,每一天不也在離別嗎?可那些寒冬放大了這種離別。他流連于多年收藏的繪畫間,最終大部分還是賣了,只余下羅維斯·科林特為他和妻子畫的肖像畫等極少的幾幅。心愛的馬也不再騎了,當人們在動物園里拿馬匹取樂時,他不忍了。他默默地整理著人世的行裝,末了只余下孤身沉浸其間的音樂。
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挨過那些了無音樂的時日的。作者的一位友人,也是唯一的知情人,看見從未干過體力活的他在嚴冬還衣著單薄地砸著石頭、扛著重物。在奧蘭寧堡集中營,有幾人可以在駭人的黨衛軍面前保持無怨、超然而有禮的態度呢?宛若那些極寒之夜的雪花在鋼鐵上留下瞬息的淡淡的印痕,他銘記著那些樂章。或許在他初次目睹人類相殘時就已想好,這次一定遵從《圣經》的教誨……而這樣的時刻,是德國的哲學、音樂與詩篇喑啞的時刻。
十七歲讀到本書部分篇章時,就深感它們異常之好,而今展讀,依然深愛。這真是令人驚訝的,因為那時還沒有太多的閱讀經驗。后來,每遭遇閱讀或是藝術上的疑難,耳畔往往還會響起這位父親如是喃喃自語:“對于藝術,喜歡或者不喜歡,意味著什么呢?我相信他是一位藝術大師。人們常常不會判斷藝術作品。這要耐心等待才行。” 那時康定斯基來他家做客,想要賣給他一幅畫,可是因為不理解,他還不喜歡康定斯基……的確,對一個人,一本書,或是初見的事物,喜歡或不喜歡意味著什么呢?特別在幼年時代,是我們本身與之有著應和之物,抑或有對更高自我的向往?如果那一刻楔入內心的不僅僅是令人心碎而是一個理想的男人之形象,如果人們曾經的含辛茹苦臻至了一種美,那可否說我們內心確有珍貴的礦藏在應和來日美的一天?無論如何,在現代經典作家里,這般悲愴,卻流溢著寧靜、詩意的文字是罕有其匹的。我們如此悵惘地看著一位理想而慈愛的父親漸行漸遠:
他總是一個人騎馬。看不見的陽光照射著的薄霧彌漫在秋天的樹林里,樹上的葉片,像滑行一樣,輕輕地飄落在地上。我欣喜地望著他漫不經心地、輕松愉快地坐在馬背上。我喊了一聲:“爸爸!”可是,他未答應,仍然騎在馬上,踏著毫不減慢的碎步繼續跑著,帶著他那和善的微笑斜視了我們一眼,在略微靠近我們的時候,他只是把鞭子舉到他的帽檐上。我們靜靜地站在那里,目送他走過去,在我們身后,零零星星的馬車走在瀝青路上,車上的飾物發出叮叮當當的響聲,我們看著騎手和馬消失在金色的霧靄當中。(《父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