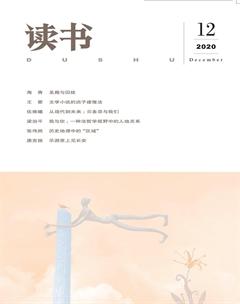字課與學書
2020-12-09 10:20:32劉濤
讀書 2020年12期
關鍵詞:結構
劉濤
晚明書家董其昌說“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鐘王, 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畫禪室隨筆·評法書》)。董其昌幼年隨父讀書,十三歲就童生試成庠生,自當早已習字,何以謂“學書在十七歲時”?董氏自道府學考試因書法不佳屈居第二受刺激,但也見出古人言“學書”異于蒙童“字課”。啟功《論述絕句·一00》自敘習字經歷,“字課”與“學書”仍加區別。
“余六歲入家塾,字課皆先祖自臨《九成宮》以為仿影。十一歲見《多寶塔碑》,略識其筆趣。然皆無所謂學書也。”
“廿余歲得趙字《膽巴碑》,大好之,習之略久,或謂似英煦齋(英和)。時方學畫,稍可成圖,而題署板滯,不成行款。乃學董香光,雖得行氣,而骨力全無。繼假得上虞羅氏精印宋拓《九成宮碑》,有劉權之跋,清潤肥厚,以為不啻墨跡,固不知其為宋人重刻者。乃逐字以蠟紙鉤搨而影摹之,于是行筆雖頑鈍,而結構略成,此余學書之筑基也。”
舊時蒙童七歲就學,習字乃日課。先摹后臨,學用筆,練結構。但定力未立,難免如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進步緩慢。十七八歲之后心智大開,又有此前字課基礎,用筆漸熟,結構能穩,學習效果倍于前。聯想西漢學吏的史學童入官學,《史律》規定須“十七歲”(《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第203 頁),當同理。
今日能書者,或髫齡習字而稱“學書”,乃不明入門階段有“字課”與“學書”之別。
猜你喜歡
小獼猴智力畫刊(2023年4期)2023-04-23 08:49:58
哲學評論(2021年2期)2021-08-22 01:53:34
中華詩詞(2019年7期)2019-11-25 01:43:04
模具制造(2019年3期)2019-06-06 02:10:54
中學生數理化·高一版(2018年1期)2018-02-10 05:20:03
影視與戲劇評論(2016年0期)2016-11-23 05:26:01
七彩語文·寫字與書法(2016年7期)2016-07-28 21:40:22
七彩語文·寫字與書法(2016年6期)2016-07-15 19:36:34
人間(2015年21期)2015-03-11 15:23:21
現代企業(2015年9期)2015-02-28 18:5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