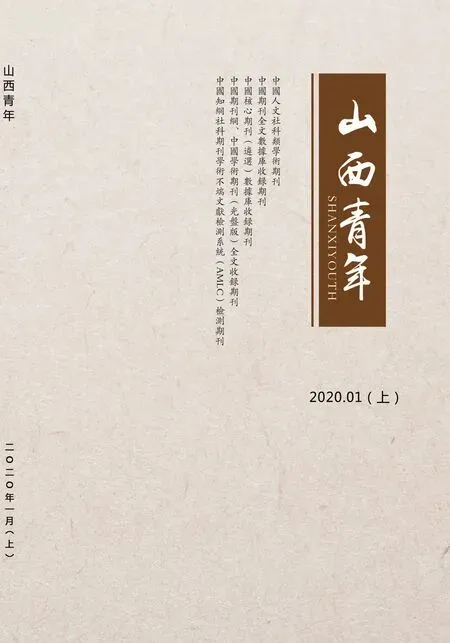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董文明
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馬克主義學院,浙江 溫州 325000
沒有自然人是否依然能夠繼續生存和發展,沒有人的自然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人是自然的婢女還是主人,自然和人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信息化時代的今天我們應當怎樣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問題不僅關乎到自然存在本身,更關乎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一、人與自然共生共榮
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和自然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因自然而實現種的繁衍和文明的發展,自然也因有了人才體現出自身的價值。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自然主宰人,還是人統治自然,這一問題一直受到人類的高度關注。
自然主義中心論從自然先在性的邏輯前提出發,提出人是自然的產物,是整個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自然界離開人類社會仍有其自身存在的內在價值,人應當給予自然更多的道德關懷而不是一味的索取。人類中心論則從人處于自然之外的邏輯前提出發,強調人是萬物之靈長,人依靠自身的力量和科技手段能從自然界獲得一切,人不是自然的婢女而是自然的主人。以上兩種理論的共同點都是把自然和人完全的對立起來,把主體和客體完全的對立起來,結果是只見人不見自然或只見自然不見人。殊不知,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自然界也因為有了人才談得上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以,人與自然是天然關聯的有機整體,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生命體,人是自然的有機生命體,人與自然共生共榮,是同一生命共同體。
二、追問“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1]這一理論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為我們認識和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一)時代鐘聲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2]任何理論都是應時代之邀,為解決歷史問題而出現的。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敏銳的觀察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再容納自己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發現資產階級連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能保障,由此指出資本主義滅亡和無產階級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20世紀上半葉,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在深刻分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提出中國要想革命成功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采取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方式,由此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面對如何使中國由站起來走向富起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問題,通過不斷實踐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面對資源、環境、生態嚴峻挑戰的局面,黨從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求的實際出發提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新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的又一重大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二)理論追溯
“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從人類生存方式出發提出,人類從“自然共同體”經“虛幻共同體”到達“真實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隨著自身生產力的變化,不斷調整著自己的生存方式,改變著人與自然的關系。從人猿揖別開始到工業革命之前人與自然處于“自然共同體”的原初狀態,這一時期受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人類更多的是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維持自身生存和種的繁衍的生活資料,人直接從屬于自然。同時,作為有意識的人類為更好的生活也在不斷突破自然,這種突破自然、改變自然的思想和行為把人類帶進到了“虛幻共同體”。“虛幻共同體”并不是虛無縹緲的假設,而是人獨立于自然之外控制自然、統治自然,是人與自然的異化。工業革命以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創造了比之前幾個時代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此時人不在屈從于自然,而是通過科學技術不斷的向自然發起一輪又一輪的進攻。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推波助瀾下自然界日益腐敗,生態嚴重破壞,人終于走向了自然的對立面,“戰勝”了自然。“戰勝”的結果就是資源趨緊、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的慘痛場景,面對此景人類終于認識到青山綠水、藍天白云才是人類得以生存得以自由發展的基礎,這時人類才逐漸進入到“真實共同體”。“真實共同體”“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種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3]。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提出未來社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4]。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同樣存在“虛假共同體”中的異化現象。“人與自然生命共同”的理論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真實共同體”這一的最高理想而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
三、建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5]。“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為我們提供了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根本指導思想。
(一)尊重自然
人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自然界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了物質的和精神的產品。人既不是“絕對觀念”的外化,更不是什么神的子孫,人是在適應自然環境基礎上,經過漫長演化而形成的高級靈長類動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6];“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7]。也正是因為如此,馬克思才說自然界是人類的無機身體。人類社會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人的個體的存在,人在自然界中為了不至于死亡就必須不斷與自然發生關系,這種發生關系的過程就是人的實踐活動。人通過實踐不斷的從自然界中獲得維持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資料。此外,自然界存在的天然的物質又作為藝術的對象成為人意識的一部分,成為人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所以,人應當對給予我們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自然抱有感恩之心、敬畏之意、報恩之情,要順應自然。
(二)順應自然
順應自然就是尊重自然規律,按照自然規律辦事。因為人是自然的有機身體,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人和自然是直接同一的。只要人與自然保持這種直接同一關系,人和自然就能相向而行共同發展,反之則會走向對立,出現異化。
異化即主體創造客體,但主體卻受客體控制,它體反應主體與客體的對立關系。馬克思從勞動入手分析了人與自然的異化現象。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是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是能思維的。人通過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斷改變著自然物的自在形式以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的這一實踐過程就是重新塑造自然的過程,就是實現自然人化的過程。可見,勞動是導致人與自然分裂的原因。人的勞動尤其是工業化以來的勞動使人認識到人自身力量的強大,依靠這種強大的力量人類不斷從外在于他的自然界獲取新的東西,以滿足自己的新的欲望和需求。在這一過程中人只看到了自身利益的實現,而過濾掉了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其結果是自然界成為異己的對象被人類占有,人成為自然的主人。此時,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于他的勞動的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肉體生存的手段”[9],人與自然出現異化。異化的消除在于人必須重新認識到人不僅具有區別于動物,重塑自然的主觀能動性,人更是自然的產物,自然不是獨立于人之外,而是與人處于同一生命體中,人的活動必須順應自然規律。
(三)保護自然
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基礎上,人類應當擔負起保護自然的重任。努力修復已被破壞的自然環境,保護好當前的生態環境,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一方面體現了自然對人的意義和價值,即自然通過自身滿足人的需要;另一方面體現了人的能力,即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恢復自然生態環境,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態的需要。這兩方面也恰是馬克思關于生產力內涵的構成要素,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一是人通過自己的勞動能力改變自然物的原有存在方式,二是自然通過自己的對象化實現自然的人化,前者是人對自然的意義,后者是自然對人的意義。由此可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是對生產力的完整詮釋,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最佳體現。
四、結語
人和自然是共生共榮的生命共同體,只有抓住這一根本旨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與自然的異化現象,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同時“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從表面上是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但從根本上仍然是在解決人和人的關系,人只有把勞動作為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時才會消除主——客二元對立,才能把自然真正納入到主體之內,徹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