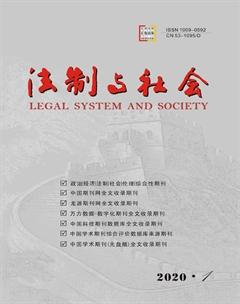聚眾斗毆罪行為屬性探析
史麗嬌
關鍵詞聚眾斗毆 行為屬性 單一行為說 復合行為說
一、聚眾斗毆罪行為屬性學說
《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對聚眾斗毆罪的客觀行為、構罪標準沒有明確定義,其僅對該罪的犯罪主體以及對應的刑罰予以明示。那么我們通常對于聚眾斗毆罪應如何理解的呢?理論通說認為聚眾斗毆罪是指為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其他不正當目的,糾集眾人成幫結伙地互相毆斗,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該理論突出聚眾斗毆罪的特點,即“聚眾”和“斗毆”。理論界因該兩個要素是否均是聚眾斗毆罪的實行行為出現了兩種學說,即“單一行為說”與“復合行為說”。該兩種學說闡述的理論直接影響犯罪實行行為的著手點及停止時態節點問題。該兩種學說觀點如下:
“單一行為說”認為:聚眾只是斗毆的形式,而不是實行行為,只有斗毆才是該罪的實行行為。行為人只需實施聚眾形式的斗毆行為這一個行為,就可構成聚眾斗毆罪。根據該觀點,聚眾斗毆罪實行行為的著手點為雙方“對峙”的時間節點,“對峙”之前進行的一系列行為是犯罪預備。
“復合行為說”認為:聚眾斗毆罪客觀上由“聚眾”和“斗毆”兩行為構成,屬于復行為犯。。聚眾斗毆罪被納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章節中,說明其和多數聚眾類犯罪一樣擾亂的是社會公共秩序。若單一的只是斗毆行為,而沒有聚眾,那么構成可能是其他類犯罪。正是因為聚眾行為的存在,才使得之后發生的危害行為更加嚴重,才會對社會公共秩序造成破壞。根據該觀點,聚眾斗毆罪實行行為的著手點為實行“聚眾”行為的時間節點。上述兩種理論學說在實際案例中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究竟哪一個理論學說對實踐更有指導意義呢?
二、以案例為例分析兩種學說對聚眾斗毆行為的界定
2018年8月,張某2在某景區內開了一家農家菜館,范某認為該餐館占用其租用土地,遂雙方發生爭執。次日上午,范某便打電話給丁某、狄某、張某,丁某又打電話給高某等數人并相約到景區附近范某自家廠區內集合,范某、丁某、狄某、張某在廠區辦公室內商量、謀劃,高某等其余人在院內等待,大約中午11點左右,集合人員到鎮上飯店吃飯。下午3點,返回到廠區內,范某指揮人發放木棍后,眾人(除范某外)相繼開車到張某2家菜館。張某1、張某2、張某3父子三人提前得到消息后,也備好燃燒瓶、石頭等,大約3點半到現場后雙方開始互投石頭、燃燒瓶,最終導致高某、張某兩人燒傷,經鑒定均為輕微傷。后人民檢察院以聚眾斗毆罪對上述所有人員提起公訴,人民法院最終以聚眾斗毆罪定罪處罰。
(一)兩種說對聚眾斗毆行為界定
結合案例,根據單一行為說理論,本案實行行為的著手點是3點半,3點半之前的聚眾行為是犯罪預備,3點半之后的行為是犯罪的實行。根據復合行為說,本案從范某打電話糾集人員開始已經為著手實施犯罪,后實施斗毆行為犯罪既遂,其給予了犯罪實施行為的存在空間,有利于區別量刑。而根據單一行為說理論,本案的著手點和實行行為之間緊密連接,雙方一動手,即構成犯罪既遂。
(二)兩種理論學說對比分析
本案中,范某系首要分子,其實施的行為有組織、指揮、策劃行為,但其沒有實際在現場實施斗毆;高某系丁某打電話糾集來的,其沒有實施聚眾行為,僅有斗毆行為,其在斗毆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系積極參加者。單一行為理論說認為采用單一行為說不會必然的擴大刑法的處罰范圍;那么在本案中范某沒有參與斗毆,那么他就沒有實施犯罪實行行為嗎?筆者認為聚眾斗毆犯罪系共同犯罪,參與實施該罪的人可能分工上有所區別,但其最終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應該共同來看待犯罪行為,處罰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系適用共同犯罪理論。對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即使其沒有在現場,沒有實施聚眾行為,但是因為其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主要作用,需要對整個犯罪承擔責任。積極參加者,若其沒有參加聚眾行為,而只是在斗毆時出現并積極實施,其承擔責任主要利用的承繼共犯理論。本案中范某、丁某實施了聚眾行為,高某等人按照策劃、指揮實施了斗毆行為,從整體行為上來說即有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單一行為說認為將聚眾行為劃入實行行為范疇即會出現“聚眾則既遂”或者“著手點提前”。事實上,“聚眾則既遂”的觀點是從結果無價值論考慮,拋開了犯罪構成要件理論;而“著手點提前”的觀點則是過于依賴客觀行為,而沒有考慮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復合行為說并不意味著將聚眾納入實行行為就意味著行為人打電話叫人就是在實行行為的著手點,也不意味著在該理論框架下,犯罪的未遂節點過早。只是在聚眾行為和斗毆行為之間出現時空節點時,復合行為說框架下的行為未遂點會有所提前,但這彌補了采用單一行為說無法明確區分犯罪未遂與既遂的弊端,同時某一情況之下的未遂節點的提前是為了更好的保護法益不受侵害。
本案中張家父子三人的定性是否印證了“單一行為說”的觀點,即該父子三人最終被定性為聚眾斗毆罪,事實上他們并沒有聚眾行為,所以聚眾斗毆罪的重點在于斗毆,聚眾只是表現形式而非犯罪行為。筆者認為,張家父子三人雖然不同于范某、丁某等人具有明顯的打電話糾集眾人的行為,但是因為其三人得知消息后,直接也準備好燃燒瓶、石頭的行為可以看出,該聚眾行為在三人之間迅速完成,三人知道彼此反映,且從三人行為來看其目標是一致的,因此該聚眾行為系迅速達成而非沒有聚眾行為。“單一行為說”通常借用“聚眾”己存在時發生的斗毆行為來駁斥復合行為說。事實上,雖然已完成的聚眾是因為聚會或者其他目的,但是一旦發生糾紛,聚眾行為會迅速發生轉化,形成一致的犯罪目的。因此,從形式上看,“單一行為說”認為不存在聚眾行為,事實上是己然成型的“聚眾”會在某一時刻迅速發生轉化,形成利用人多勢力進行毆斗的一致目的,只是該種聚眾沒有臨時準備聚眾的時空性長和明顯而己。
綜上,筆者認為聚眾斗毆罪是典型的復合行為犯罪,其要求“聚眾”和“斗毆”行為均必須存在,缺少兩個行為任一行為均不可。
三、“復合行為說”理論在聚眾斗毆罪的實踐應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對聚眾斗毆罪予以直接規定,即對聚眾斗毆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處以刑罰。該種規定方式為典型的未敘明“聚眾斗毆”的行為定義,而直接規定入罪處理的立法方式。由于這種簡單的立法方式使得不管在刑法理論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具備了對該罪名深入研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復合行為說”即在對聚眾斗毆罪深入研究的過程中產生的理論學說,該理論學說現已經被有些地市在實踐中予以應用。例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聚眾斗毆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見》中關于聚眾斗毆罪的犯罪形態的規定:“本罪屬于行為犯,且系復合型犯罪。行為人為斗毆而實施聚眾行為,屬于已經著手進行犯罪。“聚眾”后,因故最終沒有實施斗毆行為,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可以聚眾斗毆罪(未遂)認定。但是否要追究刑事責任,還應綜合考慮案件的起因、情節和社會影響等因素。行為人已經實施聚眾斗毆行為的,即構成犯罪既遂,是否造成傷亡后果,不影響既遂的成立。”該意見將“聚眾”作為實行行為,若發生“斗毆”則構成既遂,反之未遂。筆者贊同該種做法,因為從聚眾斗毆罪的立法上看,該罪更多體現的是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破壞和影響,而該罪名的特點重點體現在“聚眾”上,若將“聚眾”行為排除在實行行為之外則起不到打擊和防范作用。當然“聚眾”不僅是體現在犯罪意圖上,也要通過實行行為表現出來。對于一些雖有“聚眾”行為但在雙方尚未進行“斗毆”,最終沒有予以刑罰處罰的情形,并非是沒有構成犯罪,而是量刑時根據其情節沒有直接適用刑罰而已。而對于犯罪雖已既遂但犯罪行為尚未結束的情形,則是量刑研究中需要考慮的問題。
本文僅是立足于對聚眾斗毆罪實行行為的兩種不同學說觀點內容,結合現實案例對“復合行為說”理論的合理性予以闡述,最終借助實踐中司法應用情況得出“復合行為說”更加符合我國對聚眾斗毆罪打擊的立法原意。筆者通過本文意在為實踐中厘清行為停止時態節點,確定罪行輕重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