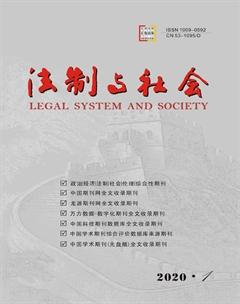執行依據不明確之彌補與救濟路徑探析
陳惠英
關鍵詞執行依據 裁判文書 司法公信 補充判決機制
一、實踐困局——裁判文書不明確引發“執行難”的現狀分析
本文的執行依據,僅指法院裁判文書。審判部門在制作裁判文書時,要充分注意其判項的權利義務主體明確、給付內容具有可執行性。司法實踐中,因執行依據不明確,造成執行工作困難,也導致了大量的執行信訪。據統計,在執行信訪案件中,因執行依據不明問題引發的信訪案件占比較高。以下通過對筆者所在S法院在該意見運行前后的一組數據來分析。(注:S法院系處于經濟政治核心區的沿海基層法院。)
從表中可以看出,2016-2017年S法院裁判不明確的執行案件大多以裁定駁回執行申請方式處理,當事人對此有異議的,通過復議、再審或者另行起訴方式解決。2018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立案、審判與執行工作協調運行的意見》規定施行,明確“執行機構發現本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書執行內容不明確的,應書面征詢審判部門的意見。審判部門應在15日內作出書面答復或者裁定予以補正。”上述規定施行后,S法院對裁判文書不明確的全部采用書面征詢審判部門意見的方式。
筆者通過親身經驗、交談了解,并參閱了有關資料,引發“執行難”的裁判問題主要為以下四類:
一是權利義務主體不明確。權利義務主體明確是裁判文書的基本要求。執行依據中出現漏列錯列被執行主體、執行標的物占有人錯誤或不明確、執行依據中包含需要案外人履行的情形的,都屬于權利義務主體不明確,必然導致無法執行。當然,隨著裁判者司法能力提高等因素,這類案件目前已比較少見。
二是裁判事項表述不完整。裁判文書中對履行方式、履行內容表述不完整。如某離婚案件中,判決婚生子歸女方撫養,男方享有探視權,但對探視時間、方式、地點等未做規定。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男方要求每周探視兩次,其中周末男方可以帶走孩子半天。女方則僅同意每月探視一次,每次不超過1小時。雙方對履行方式存在巨大差距。
三是裁判內容執行有事實或法律障礙。如某案件中,原告主張房屋所有權并要求被告一定時期內搬離,法院判決內容為自判決生效后六個月內,被告應將訴爭房屋騰空并返還原告,若逾期未返還,被告應按每個月600元的標準給付房屋使用費。法官在制作該判決文書時不嚴謹,判項內容出現限期返還房屋或者每月交納使用費的選擇性條款,執行過程中因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意見不一,無法協調,導致執行部門無法根據該判決書強制執行,案件陷入僵局。
四是裁判文書出現文字錯誤。個別裁判者制作文書時未認真校對,裁判文書出現漏字、錯字。或者在利息計算標準上表述“按年利率12%計算錯寫成“12”。或者裁判文書采用模板方式,遺漏修改當事人身份信息,誤寫性別,誤寫出生年月不在少數。
二、追根溯源——執行依據不明確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的原則性問題
作為大陸法系國家,我們的法律法規的條文是比較原則性、比較寬泛的。審判執行的依據都來自于這類法律法規,如有的條文規定“應當如何如何”,在實際操作性上就會比較欠缺。
(二)當事人訴訟請求不明確
法律所規定的責任形式通常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需要從有利于履行或強制執行的角度,來甄別所選擇的責任形式是否需要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化。部分當事人在提訴訟請求時不夠具體,若在立案、審判過程中未發現,做出的裁判文書容易出現內容不明確的情況。
(三)裁判法官執行意識不強
法院系統內部從分工合作、互相監督的角度,設立了立案、審判、執行部門,三者分立,審執分離模式下,容易導致審判人員執行意識弱化,審理過程中往往更關注事實認定、爭議焦點歸納以及法律適用,對判決后的執行工作缺乏考慮。可以說,這是導致執行文書缺乏可執行性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直面問題——征詢書面意見補正或裁定補正執行依據的弊端
為了最直接的探求裁判文書作出者的“本意”,解決執行依據(主要為裁判文書)不明確引發的“執行難”問題,最高院特別制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立案、審判與執行工作協調運行的意J酚,規定使用征詢書面意見補正或者裁定補正執行依據。筆者十分認同直接向探索裁判文書作出者探求裁判文書“本意”的做法。但對使用書面征詢意見補正或裁定補正的方式,筆者認為有以下弊端:
(一)欠缺規范,影響司法公信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補正裁定適用的范圍是判決書中的筆誤。《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百四十五條對“筆誤”的范圍定義為:“法律文書誤寫、誤算,訴訟費用漏寫、誤算和其它筆誤”。由此可見,使用補正裁定解決的是程序上的問題,該補正裁定加蓋法院公章,需要送達當事人。若涉及到實體問題,則需向審判部門征詢意見。該類征詢,雙方大部分屬于同一個法院,資料往來往往加蓋的是部門印章,不送達當事人。即使涉及的是不同法院,內部函件也不適合送達當事人。由此形成一個怪異的現象,僅僅是解決筆誤問題的補正裁定需要加蓋法院公章,送達當事人,而關涉當事人更為重要的實體利益的材料,則是加蓋了部門印章的復函,且不送達當事人。
(二)救濟缺失
權利人(一般為被執行人)的救濟權利無法得到保障。當事人對執行部門通過書面征詢裁判部門所得到的書面答復,若存在異議,這時候要啟動上訴或者再審程序都十分困難。
四、實踐出路——采用補充判決模式的優越性和可行性分析
鑒于目前采用的書面征詢意見存在文書不規范、權利救濟缺失等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采用“補充判決”這一模式加以完善。
一是補充判決的定義。補充判決,即在判決文書生效后,無論是否進入執行階段,裁判法官發現或經當事人申請,對原判決內容不明確地方重新予以明確而做出的判決。
二是筆者主張對屬于程序性缺陷的裁判文書如誤寫、漏寫、錯寫等繼續采用補正裁定方式糾正。若屬于實體性缺陷的裁判文書則應采用補充判決方式予以補正。采用補充判決模式有以下優越性和可行性:
1.規范文書適用。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和民事訴訟法法理,判決適用于對實體內容的裁斷,裁定適用于對程序內容的裁斷,從統一規則適用的角度,筆者十分認同邱星美教授提出的對裁判主文不明的救濟應當選擇適用補充判決的意見。
2.提供救濟途徑。生效法律文書作出后,若法官發現其裁判主文不明確難以執行,或者當事人在履行權利義務過程中存在爭議的,此時均可以啟動補充判決程序。當事人對補充判決不服的,參照對判決不服的救濟方式,即可以上訴也可以申請再審,這樣有利于保護其救濟權利。而一般的書面征詢意見,顯然無法承受救濟權利之重。
3.倒逼裁判法官作出明確的執行依據。書面征詢意見較補充判決更為隨意。裁判者對書面征詢意見往往不夠重視,有時還抱怨執行法官過于較真。補充判決可提高裁判法官的重視性,當事人對補充判決有異議的可以上訴或者再審,對裁判法官也是一種監督。
五、設計構想——補充判決模式的運作
(一)補充判決的適用范圍
裁判主文不明確導致無法執行的,可分為兩類,—類為程序性瑕疵,如誤寫、誤算等。一類為實體性瑕疵。如本文上述所說的裁判事項表述不完整、裁判內容執行有事實或法律障礙等。程序性瑕疵根據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解釋,適用補正裁定即可。只有裁判主文出現實體性缺陷,才適用本文所說的補充判決模式。
(二)啟動補充判決的條件
依職權為主,依申請為輔。執行依據不明確缺陷補救程序的啟動條件,也就是補充判決由誰來發起的問題。筆者認為,根據主體分類可分為三個,第一個是裁判法官。裁判生效后,無論是否進入執行,若進入執行的則在案件執行完畢前,裁判法官發現裁判主文不明確的,均可以啟動補充判決程序。第二個是執行法官。執行法官發現據以執行的裁判文書主文內容不明確導致無法執行的,應通過書面方式告知裁判法官啟動補充判決程序。第三個是當事人,當事人在判決生效后執行完畢前,對裁判主文存在分歧,無法達成共識的,可以申請啟動補充判決程序。以裁判法官主動發現或者執行法官發現后書面告知裁判法官執行依據存在可執行性缺陷后依職權啟動為主,以當事人產生爭議向執行部門或者裁判部門提出補充判決為輔。
(三)補充判決的組織形式
補充判決應以原判決的組織形式一致,即如果原來是合議制,則由原來的合議庭繼續審理。若原來是獨任審理,則由該審理法官繼續審理。如原獨任審判員或部分合議庭成員已調離原審判崗位,則通過指定其他審判員或合議庭成員的方式形成組織形式。審理中,可以再次開庭、舉證質證等。
(四)補充判決的救濟程序
補充判決是新作出的判決,與原判決具有同等的效力。補充判決應送達雙方當事人,應賦予當事人上訴或者再審的權利。若補充判決作出后,尚在上訴期限內,則雙方當事人均可上訴。若超過上訴期限,則當事人可申請再審。當然,其上訴和申請再審期間應與原裁判分別計算。
六、結語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我們黨對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近年來,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和法官綜合素質的提高,因裁判文書不明確引發的“執行難”問題雖有減少之勢,但仍然存在,我們應審慎對待,希冀通過本文能夠進一步完善執行依據不明確的處理方式,為“切實解決執行難”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