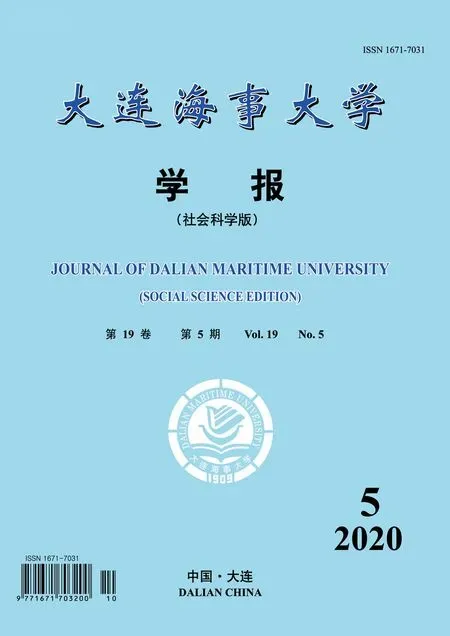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框架下的執行問題
許 卉
(清華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民商事合作的增多,國際商事仲裁以其中立、公平、高效的特點受到了國際商人們廣泛的關注與青睞,同時得益于《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在促進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獲得承認和執行方面起到的推動作用,國際商事仲裁這一爭端解決機制得到了快速發展。[1]當然,國際商事仲裁作為一種司法救濟方式,也要受到國家的司法監督,其中撤銷權就是國家對國際商事仲裁進行司法監督的一種方式。傳統理論認為,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之后,該項仲裁裁決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無法獲得其他國家法院的承認和執行。但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的國際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了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得到其他國家法院承認和執行的案例。例如,法國最高法院于1984年在Norsolor案(1)Société Pabalk Trcaret v. Société Norsolor(1984).中首次對一項已經被撤銷了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做出了執行的裁定,在此之后的法國司法實踐中,法國最高法院在諸如Jolasry案(2)Société Polish Ocean Line v. Société Jolasry(1993).、Hilmarton案(3)Société Hilmarton Ltd. v. Société OTV(1994).、S.A.Lesbats案(4)S.A.Lesbats et Fils v. Esterer WD GmbH(Dr. Volker Grub)(2007).等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爭議中,均對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了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做出了執行的裁定。除了法國的司法實踐之外,美國法院在Chromalloy案(5)Chromalloy Aero Service Inc. v.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Egypt.、奧地利法院在Radenska案(6)Do Zdravilisce Radenska v. Kajo-Erzeugnisse Essenzen GmbH(1993).、荷蘭法院在Yukos案(7)Yukos Capital SARL v. OAO Rosneft(2009).,以及比利時法院在Sonatrach案(8)Sonatrach v. Ford, Bacon and Davis Inc.(1988).中,均對已經被撤銷了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做出了執行的裁定,由此引發實踐和理論的激烈討論和爭鳴。
鑒于《紐約公約》是全球范圍內關于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專門性公約,因此有必要對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框架下的執行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依據《紐約公約》相關條款的規定,認為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可以得到承認和執行的法院主要是基于兩點理由:一是依據《紐約公約》第5條,締約國法院在該問題上具有自由裁量權;二是依據《紐約公約》第7條,締約國法院以其簽訂的其他多邊或雙邊條約或其國內法在適用上更具有優先性為由執行該項仲裁裁決具有正當性。與此相反,否定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具有可執行性的法院則認為:《紐約公約》第5條已經對拒絕承認仲裁裁決的法律事由做出了明確規定,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締約國法院就應當依據《紐約公約》第5條(e)項拒絕執行,而不是自由裁量。可見,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在《紐約公約》框架下的爭議焦點,在于締約國法院對《紐約公約》第5條是否賦予其自由裁量權的不同理解,由此導致不同締約國法院對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存在截然相反的司法態度。因此,為了解決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框架下的執行爭議,有必要對《紐約公約》相關條款進行深入研究,考察《紐約公約》締約國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上的司法實踐,同時對我國在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司法態度和未來優化路徑方面進行認真探討。
二、《紐約公約》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爭議及回應
(一)爭議的焦點:《紐約公約》第5條是授權性條款還是強制性條款
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在《紐約公約》框架下的爭議焦點,在于《紐約公約》第5條是否賦予了締約國自由裁量權。該爭議焦點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對《紐約公約》英文文本中第5條第1款中的措辭“may”的理解不同。一種觀點認為《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中的措辭“may”所表達的是“可以”的含義,應當做“授權性”解釋。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既然公約第5條第1款的措辭使用的是“may”而不是“shall”、“should”、“must”等表示強烈含義的詞,那么此處的“may”就應當解釋為是“授權性的”,換言之,公約賦予了執行地國法院自由裁量權,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自由裁量。[2]例如范·登·伯格教授指出:“《紐約公約》第5條賦予了執行地法院自由裁量權,如果執行地法院認為承認和執行該項已被撤銷的仲裁裁決是恰當的,即使該項仲裁裁決存在《紐約公約》第5條所規定的情形,那么執行地法院仍然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權對該項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3]此外,Paulsson教授也持有相同觀點,他認為既然《紐約公約》第2條、第3條和第7條的法律條文措辭都用的是“shall”,而第5條條文措辭用的卻是“may”,那么顯而易見條文措辭本身就具有不證自明的作用,即《紐約公約》第5條應當理解為是“授權性”的條款。[4]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中的措辭“may”所表達的含義是“必須”而不是“可以”,應當做“強制性”解釋。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在《元照英美法詞典》《牛津現代法律用語詞典》中,“may”有時也可以解釋為“shall”之意,法院在實踐中也常常將“may”解釋為“shall”,由此便相沿成習了。[5]也有學者通過對第5條條文句式的分析,認為第5條中的“may”是與該句后面的“only”并用,而“only”常常表示“只有”的含義,具有強制性的意味,通過對該句式的分析從而推導出第5條是強制性的含義。[6]還有學者指出,《仲裁實踐六十年》這本書的作者桑德斯教授曾經參與過《紐約公約》的起草工作,其在書中提及當時參加起草工作的情形時指出,其實《紐約公約》第5條中的“may”就是“shall”,只是最后在校對時由于疏忽才造成了今天的誤解。[7]
(二)爭議的回應:《紐約公約》第5條是授權性條款的合理性證成
1.《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的用詞本身解釋為“授權性”更為合理
首先,《紐約公約》英文文本第5條第1款的用詞“may”是有意為之而非用詞疏忽。從《紐約公約》英文條文本身的用詞來看,公約在第1條、第2條、第3條、第7條等多處都使用了帶有強制性含義的“shall”,可見公約的起草者在必須強調的問題上對文本用詞的選取和使用非常嚴謹,而在第5條規定不予承認和執行一項仲裁裁決的理由時卻在文本用詞上使用了“may”,顯然公約的起草者對“may”這一文本用詞的選取并非出于疏忽而恰恰是有意為之。雖然參與過《紐約公約》起草工作的桑德斯教授曾指出《紐約公約》第5條中的“may”就是“shall”,只是在最后校對時由于疏忽才造成了今天的誤解,[7]但是,每一項國際公約或是法律法規從最初的提出到最后的通過生效,都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法律文本每一個條文的編寫、每一個用詞的選取都要經過法律專家的反復推敲,不容疏忽,《紐約公約》的起草過程當然也不例外。《紐約公約》從起草到通過,歷經了五年的時間,在嚴謹的公約起草過程中,“《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的用詞‘may’是因起草工作疏忽而遺留下的用詞疏忽”這一觀點顯然值得商榷。
其次,《紐約公約》第5條的英文句式本身沒有帶有強制性的含義。雖然有學者提出《紐約公約》第5條條文中的“may”與“only”連用,該句式的使用使該條款表達出“強制性”的含義,[6]但是“only”在此處的用意是強調禁止擴大解釋《紐約公約》第5條所列舉的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五項理由,而不是強調該條款本身具有“強制性”這一屬性。換言之,《紐約公約》第5條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是為了禁止再擴大解釋《紐約公約》第5條所載明的這五項理由,并且允許執行地國法院通過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以其國內法或其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這些具有“更優權利”的規定為依據對《紐約公約》第5條所規定的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五項理由進行適當縮小。[8]此外,在英語語法中,也不存在“may”與“only”搭配使用構成表達句式具有強制性的這一語法記載。因此,從《紐約公約》第5條英文句式的角度分析,不能得出該條是強制性條款這一結論。
2.《紐約公約》的體系邏輯決定了公約第5條是授權性條款
《紐約公約》第7條是與《紐約公約》第5條具有密切聯系的條款,《紐約公約》第7條第1款的英文用詞是“shall not”,表達出明確的強制性。公約第7條所表達的具體含義是,“即使一項仲裁裁決依據公約其他條款可以不被承認和執行,但是只要執行地國法院依據其國內法,或者依據其與其他國家簽訂的相關多邊或雙邊協定,可以執行該項仲裁裁決,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執行地國的國內法或者其簽訂的相關多邊或雙邊協定,優先于《紐約公約》適用。正是基于這種適用上的‘優先性’,該條款又被稱之為‘更優權利條款’”[9]。該條款設立的目的顯然是使外國仲裁裁決盡可能多地在其他國家獲得執行。[10]在國際司法實踐中,法國、美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家就是通過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這一“更優權利條款”,承認和執行了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了的仲裁裁決。
正是由于《紐約公約》第7條這一強制性規定,公約第5條就必然是一個授權性條款,否則就會使《紐約公約》的條款之間相互沖突,體系邏輯無法自洽。因為如果《紐約公約》第5條做強制性條款解釋,那么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其在事實上就已經符合了《紐約公約》第5條(e)項所規定的法院拒絕承認和執行的情形,執行地國法院就必須要依據公約第5條(e)項拒絕執行該項仲裁裁決。但是如果該項仲裁裁決依據執行地國的國內法或其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可以得到承認和執行,那么此時顯然就會引起《紐約公約》第5條和第7條在法律適用上的沖突:依據《紐約公約》第5條(e)項,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必須被拒絕執行;與此同時,由于該項仲裁裁決依據執行地國的國內法或其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可以得到執行,依據《紐約公約》第7條的強制性規定,該項已撤銷仲裁裁決又必須被準予執行。可見,如果將《紐約公約》第5條解釋為強制性條款,那么公約第5條與公約第7條就會產生法律適用上的沖突,并且無法得到協調。相反,如果將《紐約公約》第5條解釋為是授權性條款,那么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雖然此時其同樣符合《紐約公約》第5條(e)項所規定的情形,但是由于《紐約公約》第5條賦予的自由裁量權,當該項仲裁裁決依據執行地國的國內法或其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可以被執行時,執行地國法院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這一強制性條款,就不會與《紐約公約》第5條產生法律適用上的沖突,避免了《紐約公約》條款之間的相互沖突,符合《紐約公約》的體系解釋邏輯。
3.《紐約公約》第5條做授權性解釋更加符合公約的宗旨和目的
首先,《紐約公約》傾向于促進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得到執行。[10]在《紐約公約》訂立之前,執行地國法院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法律依據主要是早在1927年通過的《關于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日內瓦公約》(以下簡稱《日內瓦公約》)。《日內瓦公約》針對執行外國仲裁裁決這一問題規定了“雙重執行許可證”制度,即一項外國仲裁裁決若要在其他國家得到承認和執行,不僅要求該項外國仲裁裁決在仲裁地國已成為終局裁決,而且還要求必須要由當事人先在仲裁地國法院取得執行許可證,再到執行地國法院取得執行裁決的法院裁定,只有得到這兩項“許可”之后,外國仲裁裁決才能在其他國家得到承認和執行。[11]鑒于《日內瓦公約》在適用上的局限性和復雜性,以及仲裁作為解決國際商事糾紛這一爭端解決方式的日益普遍和重要,《紐約公約》應運而生。《紐約公約》誕生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其制定的宗旨和目的是便利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得到執行,促進國際商事糾紛的解決。[3]相對于《日內瓦公約》而言,《紐約公約》為國際仲裁裁決提供了一種更加便利和簡單的程序規則,因此,《紐約公約》制定的基本出發點正是為了促進國際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得到承認和執行。[3]
其次,《紐約公約》第5條做授權性解釋有利于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得到執行,更加符合《紐約公約》的宗旨和目的。就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而言,當《紐約公約》第5條做授權性解釋時會產生這樣一種結果:如果一項已撤銷仲裁裁決依據執行地國的國內法或其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可以得到執行,那么執行地國法院應當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執行該項仲裁裁決;如果該項已撤銷仲裁裁決依據執行地國的國內法或其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不能得到執行,那么執行地國法院可以援引《紐約公約》第5條,結合該項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的具體事由以及其他考量因素,對該項已撤銷仲裁裁決是否準予執行進行自由裁量。這樣的結果顯然有助于促進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獲得承認和執行,有利于國際商事糾紛的解決,符合《紐約公約》的制定目的。
三、《紐約公約》締約國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司法實踐
(一)法國司法實踐
1.Norsolor案(Société Pabalk Trcaret v. Société Norsolor(1984))(9)Award of 26 October 1984 in ICC Case No.3131. IX Y.B.Com. Arb.(1984), 109-110.
法國Norsolor公司與土耳其Pabalk公司簽訂了一份代理協議,后來雙方發生爭議提交仲裁,仲裁庭審理之后最終做出了有利土耳其Pabalk公司的仲裁裁決。Norsolor公司不服裁決提起上訴,維也納上訴法院審理后認為仲裁庭超越權限,撤銷了部分裁決決定。然而Pabalk公司卻在法國對該項裁決提出了執行申請并且獲得了執行裁定。但是,Norsolor公司隨后向法國巴黎上訴法院提起上訴反對執行,理由是該裁決已經被維也納上訴法院撤銷。巴黎上訴法院審理后以《紐約公約》第5條為由撤回了法國法院先前的執行裁定。但是最終,法國最高法院還是基于Pabalk公司的請求,恢復了對該裁決的執行。其理由是巴黎上訴法院的撤銷決定雖然是基于《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第5項做出的,但是根據《紐約公約》第7條,法國法院有優先適用法國本國法進而促使裁決得到執行的權利,而這項權利不應該被忽視和剝奪。
2.Hilmarton案(Société Hilmarton Ltd. v. Société OTV(1994))(10)Soc. Hilmarton Ltd. V. Soc. OTV, French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23 March 1994, XIX Y.B.Com. Arb.(1994), 665.
英國Hilmarton公司與法國OTV公司簽訂了一份咨詢服務合同,隨后雙方因咨詢費用產生糾紛。英國Hilmarton公司依據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在日內瓦提出了仲裁請求,仲裁庭審理后以當事人簽訂的合同無效為由駁回了英國Hilmarton公司的申請。英國Hilmarton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日內瓦上訴法院審理后以“仲裁裁決是武斷的”為由撤銷了仲裁庭做出的仲裁裁決,并且在隨后得到了瑞士最高法院的進一步認可。然而盡管如此,法國OTV公司仍然向法國法院提出了執行該項仲裁裁決的申請。法國巴黎一審法院對該已被撤銷的裁決做出了執行裁定,并且在隨后的一段時間里先后得到了巴黎上訴法院和法國最高法院的維持判決。法國最高法院認為,一方面法國OTV公司可以援引與執行該項仲裁裁決相關的法國法律,另一方面《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502條沒有包含與《紐約公約》第5條(e)項相同的拒絕執行仲裁裁決的理由,因此法院最終以《紐約公約》第7條為由執行了該項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
(二)美國司法實踐
1.Chromalloy案(Chromalloy Aero Service Inc. v.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Egypt)(11)Chromalloy Aero Services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939 F. Supp. 907, 908(D.D.C, 1996).
美國Chromalloy公司與埃及國防部于1988年6月簽訂了一份有關飛機零部件的提供、保養和修理的合同。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因為Chromalloy公司沒有使用雙方在合同中事先所指定的特定零部件,埃及政府于1991年12月單方面解除了該合同。然而,埃及方面的決定遭到了Chromalloy公司的強烈反對,1992年,Chromalloy公司根據合同中所訂立的仲裁條款提出仲裁請求。1994年8月,仲裁庭裁決認為埃及政府的行為欠缺正當性,應當對Chromalloy公司已經完成的工作予以補償并且加計利息。Chromalloy公司于1994年10月向美國哥倫比亞法院提出了執行申請。然而,埃及政府于同年11月向埃及上訴法院提起了撤銷該項裁決的訴訟請求,并在1995年3月向美國法院提出了中止執行的申請。埃及上訴法院經過審理之后于1995年12月以“仲裁員適用法律錯誤”為由對該項裁決予以撤銷。但是,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并沒有認可埃及上訴法院的撤銷裁定,而是依然準予執行此項裁決。美國法院認為:首先,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法院本身具有自由裁量權;其次,根據《紐約公約》第7條,法院可以以國內法在適用上更具有優先性為由對裁決予以執行;再次,在本案中,埃及法院據以撤銷該項裁決的法律事由并不在聯邦仲裁法中所規定的撤銷事由的范圍之內;最后,當事人在雙方訂立的仲裁條款中已經明確約定一旦裁決做出,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對裁決提出上訴,當事人雙方的這種約定應當得到法院的尊重。最終,該項已撤銷的仲裁裁決得到了執行。
2.Baker案(Baker Marine(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12)Baker Marine v. Cheveron Nigeria Ltd. 191F. 3d 194 (2nd Cir.1999).
該案源于一起船舶服務合同爭議,三方當事人Baker公司、Chevron公司和Danos公司均是尼日利亞籍,其中Baker公司向Chevron公司的駁船提供當地補給,Danos公司則向Chevron公司提供技術設備和管理服務。后Baker公司認為Danos公司和Chevron公司均違反合同,于是根據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在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提起仲裁,這兩起仲裁的裁決結果均支持了Baker公司的申請主張。Baker公司立即向尼日利亞聯邦高等法院申請執行這兩項裁決,但是,尼日利亞法院基于被申請人Danos公司和Chevron公司的申請撤銷了這兩項仲裁裁決,其理由是第一項裁決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第二項裁決屬于“超裁”。Baker公司于是向美國法院提出了執行申請,但是美國法院以這兩項裁決都已經被尼日利亞法院所撤銷為依據而予以拒絕。美國法院在此案中做出了與Chromalloy案截然相反的決定,其理由是:首先,與Chromalloy案明顯的不同是本案當事人并非美國籍;其次,本案當事人在訂立仲裁條款時沒有約定一旦裁決做出就不得提出上訴這樣的約定,所以Danos公司和Chevron公司提起上訴的行為并未違反彼此之間的任何約定;最后,拒絕Baker公司提出的執行申請并不違背美國的公共政策。[12]167
(三)德國司法實踐
Radenska案(Do Zdravilisce Radenska v. Kajo-Erzeugnisse Essenzen GmbH(1993))(13)Do Zdravilisce Radenska v. Kajo-Erzeugnisse Essenzen GmbH, decision of 23 February 1998, in XXIVa Y.B.Com. Arb(1999), 925.情況如下:斯洛文尼亞Radenska公司與奧地利Kajo公司簽訂了一份生產和分銷軟飲料的合同,合同中約定有仲裁條款。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雙方發生爭議訴諸仲裁,仲裁庭審理后支持了Kajo公司的申請主張。Radenska公司不服裁決,向南斯拉夫初審法院提出撤銷裁決的申請,但是遭到拒絕,隨后南斯拉夫上訴法院進一步確認了初審法院的決定。Kajo公司向奧地利地方法院提出了執行申請并且得到了準許,與此同時,Kajo公司也向德國法院申請執行該項仲裁裁決。但是,斯洛文尼亞最高法院以Kajo公司存在違反相關公共政策的壟斷行為為由撤銷了上述仲裁裁決。隨后,Radenska公司以裁決已被撤銷為由請求奧地利地方法院和德國法院中止執行裁決,但是遭到奧地利法院和德國法院的拒絕。其理由是《歐洲國際商事仲裁公約》(以下簡稱《歐洲公約》)第9條并沒有規定違反外國公共政策是拒絕執行的正當依據,基于南斯拉夫公共政策而撤銷裁決并不會構成根據《歐洲公約》拒絕執行的合法理由,因此,奧地利最高法院和德國法院最終執行了該案中已撤銷的仲裁裁決。
(四)《紐約公約》締約國司法實踐評析
通過對法國、美國和德國司法實踐中涉及的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的經典案例的闡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各個國家在對待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上的司法態度和考慮因素各不相同:法國法院主要是以法國國內法來判斷仲裁裁決被撤銷是否具有合理性,并且根據國內法來決定是否執行已撤銷的仲裁裁決,而不是考慮國際禮讓或者完全為了維護本國當事人的利益,[12]161除了文中介紹的Norsolor案和Hilmarton案之外,還有多個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法國得到了執行,例如Jolasry案(14)French Supreme Court, March 10, 1993, Y.B.Com. Arb., 1994, p.662.、S.A.Lesbats案(15)Cour d’Appel, Paris, 18 January 2007, Yearbook XXXII(2007) , 297-298.、Putrabali案(16)PT Putrabali Adyamulia v. Rena Holding, in XXXII Y.B.Com. Arb.(2007), 299.等。而相對于法國的司法態度而言,美國法院在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問題上的司法態度更為謹慎,除Chromalloy案在美國法院得到了執行之外,其他諸如Baker案、Spier 案(17)Martin Spier v. Calzaturificio Technica, S.p.A., 71F.Supp. 2d 279(S.D.N.Y 86 Civ. 3447(CSH)1999).、TermRio案(18)TermRio S.A. v. Eletrana S.P 487 F. 3rd 928(C.A.D.C.2007).等在美國法院申請執行的已撤銷仲裁裁決都遭到了拒絕。美國法院重點考慮的因素包括國際禮讓、仲裁當事人是否具有美國國籍,以及仲裁當事人的仲裁協議中是否有裁決做出不得上訴的約定等內容。相較于法國和美國的司法實踐,德國在已撤銷仲裁裁決執行問題上的司法態度則更為保守,基本上適用由相關國際公約和德國國內法規定的執行制度。此外德國強調對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仲裁裁決的裁定的國際禮讓,而不是維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終局性。[12]181除Radenska案之外,德國法院并未對其他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做出過執行裁定。
除法國、美國和德國的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得到承認和執行的案例之外,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等國家也出現過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司法實踐。雖然各個國家在執行已撤銷仲裁裁決時所考慮的因素各不相同,法律依據之間亦存在差異,尚未形成國際共識,也尚未形成在對待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問題上的統一規則,[13]但是,這些最終得到執行的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案例中有一個共性特點,即這些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能夠得到執行地國法院執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執行地國法院并不認為仲裁地國法院撤銷該項仲裁裁決是基于正確的或者是合理的撤銷理由。雖然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得到執行的案例在國際司法實踐中仍然屬于“特殊”案例,尚未成為一種普遍的國際實踐趨勢,但是在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理由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情況下,執行地國法院執行該項仲裁裁決的做法正是保障仲裁公平公正的體現,是對仲裁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因此,各國應當為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保留一定的空間和可能性。
四、中國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司法態度現狀及優化路徑
(一)中國目前的司法態度
第一,依據我國現有的國內法規定,我國法院沒有自由裁量權,因此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其就已經符合了《紐約公約》第5條(e)項所規定的拒絕執行的情形,不能得到我國法院的承認和執行。我國目前關于適用《紐約公約》第5條的法律規定體現在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我國加入的〈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以下簡稱1987年《最高法關于執行〈紐約公約〉的通知》)中的第四項。依據該條款,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具有《紐約公約》第5條所列情形之一時,我國法院“應當”拒絕承認和執行該項仲裁裁決。因此依據該條規定,我國對于適用《紐約公約》第5條的規定屬于強制性條款,我國法院不具有自由裁量權。這意味著只要是在我國法院申請執行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所撤銷,那么我國法院無須考慮該項仲裁裁決被撤銷的具體理由是什么,也無須考慮該項仲裁裁決依據我國國內法或我國簽訂的其他雙邊、多邊協定是否可以得到承認和執行,都應當基于其符合《紐約公約》第5條(e)項的規定拒絕承認和執行該項仲裁裁決。
第二,我國目前所遵循的仍然是傳統的屬地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仲裁裁決受仲裁地國的司法監督,因此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我國作為執行地國,應當認可和接受仲裁地國法院的撤銷裁定,拒絕承認和執行該項仲裁裁決。屬地主義理論強調的是仲裁地國的法律秩序,強調仲裁裁決的合法性根植于裁決地國的法律,如果一項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所撤銷,那么就意味著這項仲裁裁決在該國家就已經不復存在了,另一國家就不能再認為這項仲裁裁決是有效的進而予以承認和執行。[14]有鑒于此,當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法院申請執行時,依據我國目前所遵循的傳統屬地主義理論觀點,該項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是沒有法律效力、不再存在的仲裁裁決,沒有在我國得到承認和執行的理論依據。
(二)中國目前司法態度的弊端
第一,我國目前對于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的法律規定過于絕對,使我國法院在已撤銷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上缺乏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不僅不利于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而且不利于保障仲裁的公平公正。在國際司法實踐中,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可能基于不同仲裁地國家各自不同的法律規則,以不同的理由被撤銷,其中不排除有些撤銷理由是錯誤或者荒唐的,例如以仲裁員沒有信奉某種宗教而撤銷,以仲裁員不是男性而撤銷等。如果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基于上述類似理由被撤銷,那么這顯然不僅會損害仲裁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會阻礙國際商事仲裁的發展。[3]因此,當一項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時,如果我國法院不去甄別該項仲裁裁決被撤銷的具體理由,而僅僅是依據該項仲裁裁決已經被撤銷這一表象的事實就對其拒絕執行,那么這顯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對仲裁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也不利于保障仲裁的公平公正,更不利于促進仲裁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目前所遵循的傳統屬地主義理論,在解釋仲裁地國法院和執行地國法院對同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權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存在一定弊端,不利于執行地國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權的行使。基于國家的司法主權,仲裁地國法院和執行地國法院均對國際商事仲裁裁決享有司法審查的權利,但是鑒于傳統的屬地主義理論認為仲裁裁決的效力來源于仲裁地國的法律規定,當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該項仲裁裁決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仲裁地國法院撤銷該項仲裁裁決的裁定是基于不正確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撤銷標準,這項仲裁裁決仍然缺少了在執行地國法院得到承認和執行的法律基礎。這顯然不利于執行地國的司法審查權的行使。因此,傳統的屬地主義理論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權問題上存在一定的解釋弊端。
(三)中國未來的優化路徑
第一,我國應當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與否的問題上,改變以往過于絕對的規定,賦予我國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我國最早關于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與否問題上的國內法規定是1987年《最高法關于執行〈紐約公約〉的通知》,其中第四項關于適用《紐約公約》第5條的規定過于絕對,使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法院沒有執行的空間。但是1987年《最高法關于執行〈紐約公約〉的通知》的發布距今已經有33年,國際司法實踐中也先后出現了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其他國家得到承認和執行的案例,現有法律規定發布時間的久遠與目前國際司法實踐的發展所產生的沖突與矛盾應當引起我國的重視。雖然我國司法實踐中尚未出現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法院申請執行的案例,但是我國應當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應當執行與否的激烈爭論下,針對我國現有的相關規定和制度做出基于我國情況的重新思考。在國際司法實踐中,由于各國的法律規定各不相同,一項仲裁裁決可能基于各種不同的理由被撤銷,如果一項仲裁裁決是基于不正確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撤銷標準被撤銷,為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此時對該項已撤銷的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我國應當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改變以往過于絕對的司法態度,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上,賦予我國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為我國未來可能遇到的相關司法實踐、雙邊或多邊協定的簽署,以及國內立法的制定等方面留有解釋的空間。
第二,我國應當對屬地主義理論中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權進行重新思考,正確認識仲裁地國和執行地國的關系,為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的執行問題留有一定的理論解釋空間。一般而言,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受仲裁地國的司法監督是一種普遍現象,基于對國家禮讓等因素的考慮,當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時,仲裁地國法院的這項撤銷裁定通常會得到執行地國法院的認同和接受,這直接導致該項仲裁裁決無法在執行地國法院得到承認和執行。[15]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執行地國法院不應當在任何情況下都毫無例外地認同和接受仲裁地國法院對一項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撤銷裁定,因為仲裁地國的司法監督并不必然等同于執行地國的司法監督,不同國家對仲裁裁決的撤銷標準有著各自不同的法律規定,基于國家主權原則,執行地國法院在審查一項仲裁裁決時,首先應當考慮本國的法律規定,其次才是考慮國際禮讓等其他因素。[15]況且,國際商事仲裁主要是一種關于當事人自治的私法制度,過分強調國際禮讓是沒有法理依據的,國際禮讓不應當成為拒絕承認和執行已撤銷仲裁裁決的一種絕對理由。[12]182因此,雖然我國所遵循的是屬地主義理論,但是由于我國對仲裁裁決的撤銷標準與仲裁地國對仲裁裁決的撤銷標準不一定完全一致,基于國家的司法主權,我國法院不應當在任何情況下都對仲裁地國法院做出的撤銷仲裁裁決的裁定全盤接受,否定已撤銷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
第三,我國應當利用《紐約公約》第7條這一“更優權利條款”,當一項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依據我國的國內法或我國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可以得到執行時,我國法院可以結合仲裁案的具體情況,通過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對該項已撤銷的仲裁裁決做出執行的裁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在第七章“涉外仲裁的特別規定”下的第71條規定,我國法院不予執行涉外仲裁裁決的理由是其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274條所規定的情形之一,但是《民事訴訟法》第274條沒有將“仲裁裁決已被撤銷”作為拒絕承認和執行涉外仲裁裁決的法律事由之一,因此《民事訴訟法》第274條在客觀上為我國法院在執行已撤銷仲裁裁決的問題上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更優權利條款”留有了一定的空間。[16]雖然《仲裁法》第71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74條適用的是涉外裁決,但是不排除外國裁決參照適用的可行性。[16]鑒于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74條,“仲裁裁決已被撤銷”并不是我國法院拒絕承認和執行涉外仲裁裁決的法定事由之一,因此當一項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時,我國法院不應當不加區分地僅僅依據該項仲裁裁決已經被仲裁地國法院所撤銷而拒絕承認和執行,而是應當行使我國作為執行地國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審查該項仲裁裁決被仲裁地國法院撤銷的理由。如果仲裁地國法院撤銷該項仲裁裁決的理由不屬于我國《仲裁法》第58條所規定的撤銷情形,并且執行該項已撤銷的仲裁裁決與我國社會公共利益不相違背,我國法院可以將《民事訴訟法》第274條作為執行該項仲裁裁決的“更優權利條款”,通過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對該項仲裁裁決做出承認和執行的裁定。
五、結 語
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在《紐約公約》框架下的爭議焦點在于《紐約公約》第5條是否賦予了執行地國法院自由裁量權。通過對《紐約公約》第5條用詞的解讀、對公約體系邏輯的分析和對公約制定目的的闡釋,《紐約公約》第5條做授權性條款解釋更為合理。因此,《紐約公約》締約國法院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問題上具有自由裁量權。
通過對《紐約公約》締約國的司法實踐考察可知,雖然各國法院在執行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時所考慮的因素各不相同,尚未形成統一的規則,但是已撤銷仲裁裁決得到執行的共性原因在于,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沒有得到執行地國法院的認可和接受。在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情況下,執行地國法院對該項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正是保障仲裁公平公正的體現。
我國目前在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問題上的司法態度過于絕對,不利于保障仲裁的公平公正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國應當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改變我國以往過于絕對的司法態度,為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在我國法院的執行留有一定的空間。當一項已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我國法院申請執行時,如果該項裁決被撤銷的理由不屬于我國國內法所規定的撤銷情形,并且執行該項已撤銷的仲裁裁決與我國社會公共利益不相違背,我國法院可以通過援引《紐約公約》第7條對該項仲裁裁決做出承認和執行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