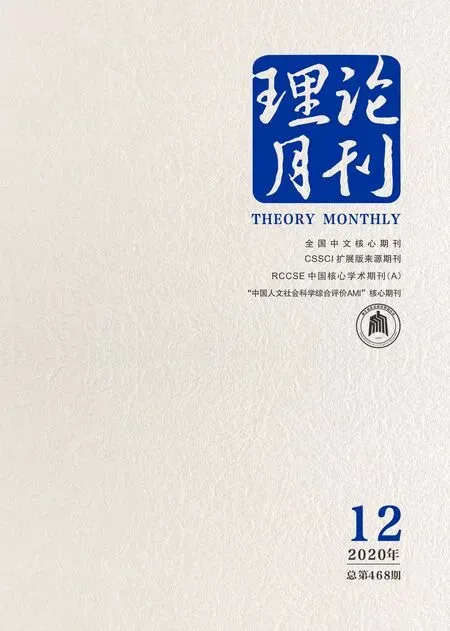《矛盾論》的生成及其革新意義
□王文虎
(武漢工商學院 公共課部,湖北 武漢430065)
在對《矛盾論》的研究中,許多研究者一方面強調《矛盾論》是中國革命的經驗總結,另一方面強調《矛盾論》與蘇聯哲學教科書的繼承關系。這些看法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學術共識。然而,這些共識有兩個不足。其一,“經驗總結說”并沒有闡明《矛盾論》的生成究竟指經驗生成還是經驗中的邏輯生成,以至于給人們一種錯覺——經驗的總結無非是總結起來的經驗而已,不具備普遍性。其二,強調《矛盾論》與蘇聯哲學教科書之間的繼承關系的看法雖然并不錯,但是卻忽視了毛澤東對蘇聯哲學教科書的改造工作。這給人一種錯覺——《矛盾論》是蘇聯哲學的復制品。而在筆者看來,矛盾論是由“矛盾論思想”以及“矛盾論術語系統”所構成的理論體系。其中,關于矛盾的思想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過程中產生的,與蘇聯哲學教科書無關。“矛盾論術語系統”主要從蘇聯哲學教科書中而來,但是毛澤東對它進行了改造。《矛盾論》的產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上的一次革新。
一、毛澤東“矛盾論思想”的生成過程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尤其是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矛盾是概括對立統一思想的重要的辯證法范疇,也是“矛盾論思想”的靈魂。它既存在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中,又存在于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原理中。對于毛澤東而言,他最早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階級斗爭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的唯物史觀[1](p379),并強調“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2](p15)[3](p1487)。后來,他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又深入研習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但此時毛澤東關于矛盾的思想已經形成。因此,《矛盾論》中的歷史科學的色彩多于自然科學的色彩。
毛澤東對矛盾范疇的使用最早見于他對中國社會實際存在的階級斗爭的分析。這種分析雖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但其中包含了一種超出唯物史觀的思想形式,即“矛盾論思想”。
發表于1925 年12 月1 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下簡稱《分析》)是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分析的歷史起點,同時也是其矛盾論思想形成的邏輯起點。在《分析》中,毛澤東用“敵”“我”“友”三個社會學概念來概括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其中,“敵”和“我”是中國社會的兩個對立面,而“友”則是介于“敵”“我”之間的中間階級。這種以“友”為中介的“敵”“我”對立的結構,包含一個超越具體經驗的概念形式,即“對立著的事物通過中介而統一”。當然,在《分析》中,這個超越具體經驗的概念形式并不是分析的對象,而是隱而不顯地貫穿于整個分析過程之中。盡管毛澤東沒有用“矛盾”“辯證法”等術語來表述它,但它卻是毛澤東“矛盾論思想”邏輯生成的原點,此后的“矛盾論思想”是這個原點的升華。而在《分析》發表之前,瞿秋白于1924年編著《社會科學概論》時已經用“互變法”代替舊譯的“辯證法”,闡述了“正反相成,矛盾互變” 的矛盾論觀念[4](p251)。這說明此時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已經有了從唯物史觀向更普遍的“矛盾”“辯證法”轉變的趨勢。不過,毛澤東當時還沒有轉向以“正反相成,矛盾互變”為特征的“互變法”(“辯證法”)。比如,《分析》中有“矛盾惶遽”一詞,但毛澤東并沒有將它同“辯證法”聯系起來,它指的是中間階級將兩種相反取向集于一身的“ 階級態度”[3](p3-9),而非“對立著的事物通過中介而統一”。在1926年1月1日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中,毛澤東對矛盾一詞的使用依舊如此[5]。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其著作中還將“沖突”當作“矛盾”的同義詞使用。例如,他在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報》第1期《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講,全世界帝國主義、全國大小軍閥、各地買辦階級土豪劣紳等一切反動政派之間因利害不同而時起“沖突”。在1927 年2 月16 日的《視察湖南農民運動給中央的報告》中,他稱農村問題是“農工沖突”“農商沖突”等等。他從沖突的角度講矛盾,似乎將矛盾與現實事物聯系起來了,但是從對矛盾這個范疇本身的使用來看,他還是將矛盾限制在主觀領域,并沒有將其作為概括現實事物的存在和發展的普適性范疇。
而到了1927 年3 月,毛澤東開始對《分析》中的潛思想本身有所言說了。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在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的階級關系和革命態度的同時,還說道:“對于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3](p18)《分析》中的潛思想在《報告》中被表述為“相反的兩種看法存在于‘一件事或一種人’中”。盡管它還沒有獲得“對立物”之稱[6](p506),但畢竟成了議論的對象。而且,圍繞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對立物”,毛澤東論述了“糟得很”“好得很”和“痞子”“革命先鋒”等階級斗爭現象。毛澤東將它們看作對立物的適例。1928 年,毛澤東終于讓矛盾從主觀領域走了出來,成為概括現實事物及其本質的普適性范疇。例如,1928 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的第一部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中,使用矛盾概念來描述事物及其本質。他說:“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斗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斗爭。故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著明天的更大的戰爭。”[3](p47-48)
至此,毛澤東“矛盾論思想”得到了由隱到顯的升華。當然毛澤東此時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指“歷史唯物論”[7](p111),即唯物史觀。可是這種“歷史唯物論”實際上已經深入“辯證唯物論”的領域之中。“相反的兩種看法存在于‘一件事或一種人’中”,這樣的看法既是歷史唯物論,又是辯證唯物論,盡管此時的毛澤東還沒有讀到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辯證唯物論。有了概括現實事物及其本質的矛盾范疇,那么毛澤東又是怎樣使之成為一個思想的系統的呢?
二、“矛盾論思想”的系統化
在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總結的過程中,矛盾范疇不僅成了毛澤東言說的對象,而且成了分析現實(如“工農武裝割據”)之發生、存在和發展的獨特的原因和條件。毛澤東不僅將矛盾實體化,以強調矛盾的客觀性,而且置之于主觀與客觀互相作用的背景下,以強調矛盾的主觀性。“矛盾論思想”由此得以系統化。
在1928 年10 月5 日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毛澤東以中國社會的矛盾為分析對象,指出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形成了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它們之間存在著的矛盾和斗爭是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斗爭的反映。這種情形便創造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堅持下來。這就將“矛盾論思想”表達成一種實體化的哲學。《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這兩篇著作闡述了如下思想:矛盾和斗爭是紅色政權存在與發展的原因與條件。白色政權這個現實的對立物存在“妥協” 與“分裂”兩種狀態,“妥協都是暫時的”,而“分裂” 則是“不斷的”。白色政權的這種“不斷的分裂”是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原因。但是發展是波浪式地推進的,有高潮,也有低谷。
毛澤東寫于1930 年1 月5 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方面分析了引發中國革命高潮的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以及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強調“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3](p101-102)。另一方面,這篇文章又將矛盾置于主觀與客觀之互相作用的背景下,既反對主觀主義,又反對悲觀主義。在講矛盾決定革命高潮時,毛澤東指出:“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3](p99)
由此可見,在1928 年至1930 年的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在實體化層面強調:矛盾在現實中存在,是事物發生、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條件,是現象背后的本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使“矛盾論思想”表現為一種以客觀性為取向的實體性哲學。在主體性的層面,毛澤東強調:矛盾既包括客觀方面,又包括主觀方面;既要估量客觀方面,又要估量主觀方面。在這個意義上,“矛盾論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追求主觀與客觀的一致的主體性哲學。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甚至稱之為“貫穿一切”的“根本的指導原則”①參見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的六十周年》,《紅旗》1981年第23期。。經過這兩個層面的建構,毛澤東以主體性為原則的“矛盾論思想” 已經頗為系統了。關于這個問題,在中共七大之前,陳毅與郭化若有一次談話,他對郭化若說:“毛主席的唯物論辯證法思想,早在井岡山時期,就已經基本建立了一個初步完整的體系,以后則是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8](p32-34)陳毅如果指的是“矛盾論思想”,那么他的看法很有道理。
不過此時,毛澤東的“矛盾論思想”還在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中。其一,“矛盾論思想”還需要進一步明確矛盾的主次關系。在1934 年1 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毛澤東開始思考矛盾的主次關系。他說:“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正在瘋狂地準備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的結果,使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尤其是日美間的矛盾,在新的基礎上開展起來,重新分配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是正在極端地威脅著全世界民眾,然而帝國主義卻又在企圖暫時緩和它們內部的矛盾。”這里講“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強調“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的結果,使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暫時緩和……”就涉及矛盾的主次之分。他在1937 年5 月3 日講:“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3](p253)其二,“矛盾論思想”需要進一步明確“矛盾”概念中的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在寫于1935年12 月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他闡述了“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沒有“純粹又純粹”的事物,“要把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上平衡的狀態”“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總是曲折的”等思想。
由此可見,當毛澤東將矛盾這個范疇擴展到事物或人時,他得出了如下結論:現實事物是對立物,沒有純而又純的事物;矛盾不僅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條件,而且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對立物的分裂是不斷的,妥協是暫時的;矛盾有主次之分,故發展是不平衡的,主次可以互相轉化,故發展是曲折的;對立物有部分與全體之分,不僅要看到部分,而且也要看到整體。這些“矛盾論思想” 的系統化為毛澤東專門述說矛盾論問題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準備。他曾論及這個問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9](p299)這里所說的有關革命經驗的總結的論文包括《實踐論》《矛盾論》,之所以沒有列舉它們,是因為這段話強調的是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離開不開總結革命經驗,而《實踐論》《矛盾論》則是超越具體經驗的哲學反思。《矛盾論》的分析對象“主要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許多新思想“主要是概括中國社會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經驗的結果”,因而“是中國現實社會矛盾運動的理論形態”[10](p13)。下一步的問題是,毛澤東以怎樣的術語系統才能將“矛盾論思想”表達出來。
三、“矛盾論術語系統”的形成
在抗日戰爭之前,毛澤東深刻而又豐富的“矛盾論思想”沒有以哲學術語的形式呈現出來,有人據此攻擊他有經驗而無理論,所以他面臨著一個以怎樣的概念系統述說其“矛盾論思想”的問題。
閱讀哲學書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1931年,他讀到《反杜林論》中譯本,從中了解了辯證法、量質互變、矛盾、否定之否定等范疇。在延安,他“想方設法搜集已譯成中文的馬列主義的書,擠出時間,不分晝夜,發憤攻讀,特別是發憤學哲學”[8](p32)。1935 年7 月的一天,他收到客人帶來的“幾本哲學新書”,學之而忘食[11](p56)。1936 年11 月至1937 年4 月,他批閱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1937 年7 月以前又讀了米丁的《辯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1939 年1 月17日,毛澤東在《致何干之》中講:“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哲學研究……”[2](p136)通過閱讀,他接受了“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觀點,了解了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對立,以及質量互變—矛盾—否定之否定的概念系統,獲得了許多規范其“矛盾論思想”的哲學術語,如“對于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之認識,乃是辯證法的本質”“辯證法中心任務,在研究對立的相互滲透即對立的同一性”“矛盾普遍地存在著”“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等[6](p65-126)。于是“對于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的思想,被毛澤東表述為“辯證法的本質”;“全局”與“局部”的關系以及“戰爭的規律”“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被歸為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之間的關系;而矛盾的主次關系分別被毛澤東以“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概念形式納入“矛盾的特殊性”的范疇之中。這樣一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的重點就由“歷史唯物論”轉移到蘇聯哲學教科書所闡述的“辯證唯物論”。
毛澤東“矛盾論思想”的術語系統的形成包括三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以矛盾為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用所學的“辯證法唯物論”概念體系分析中國革命戰略問題,寫成了以普遍(戰爭的規律)、特殊(革命戰爭的規律)、個別(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關系為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寫道:“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3](p170)戰爭、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有兩層包含關系,從概念的內涵上來看,中國革命戰爭包含革命戰爭,革命戰爭包含戰爭。這不僅有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邏輯意義,而且包含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論線路。當然,毛澤東的論述是從戰爭到革命戰爭再到中國革命戰爭,這種敘述方法包含《矛盾論》所說的“從一般到特殊”的認識論線路。關于如何處理戰爭、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三者的關系,毛澤東批評了只知一般而不知特殊的意見,同時也批評了只知特殊而不知一般的局部經驗論。他將二者結合起來,建立了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特殊的環形邏輯線路。他用這個環形邏輯線路將一般與特殊、全局與局部、客觀物質基礎與主觀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圍剿”和反“圍剿”以及戰略防御(積極防御和消極防御、反“圍剿”的準備、戰略退卻、戰略反攻、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問題貫穿起來,形成了一個既反對機械論又反對局部經驗論的方法論體系。這是毛澤東經過哲學研究之后整理其“矛盾論思想”的第一個文本,是戰爭經驗的總結,但他還沒有使用“辯證法”一詞。第二個環節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一些研究者認為,《提綱》寫于1937 年七八月間。然而據張國燾的回憶,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等人給抗日軍政大學學員講課的時間是1937 年4月,“毛澤東在那里講授哲學和戰略問題,后來他所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等文,就是以這時的講稿為基礎的”[12](p373)。《毛澤東年譜》試圖將兩種說法調和起來,提出《提綱》的編寫時間在1937 年的4—8月[13](p671)。但這不符合毛澤東本人的記憶,因為他曾回憶說,《提綱》是他在抗戰前夕準備的講課稿,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參加抗戰是1937年8月25日以后的事情。這樣看來,張氏的回憶應該是準確的。因此在1937 年4 月之前,毛澤東已經熟練地掌握“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術語,其理論水平與蘇聯哲學界基本同步,但也有超越蘇聯實體性辯證法的地方,如《提綱》中的“實踐論”和“矛盾統一的法則”兩節。第三個環節是《矛盾論》。《提綱》問世后,毛澤東將其第三章“矛盾統一的法則”抽出來進行修改,獨立成文。據郭化若的回憶,他在1938 年看到的總政打印出來的記錄稿,是經毛澤東審閱并略加修改的“矛盾統一的法則”一節。這是“矛盾論思想”脫離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的開始。20 世紀50 年代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對《矛盾統一的法則》一文又進行了修改,不僅將《矛盾統一的法則》改稱為《矛盾論》,而且內容也有很大幅度的修改。《矛盾論》脫離了《提綱》這個起點,實現了向《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所主張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道理的回歸。《矛盾論》說:“當著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后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后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3](p304-305)
最先出現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綱”在《矛盾論》中成為整理中國革命經驗中的“矛盾論思想”的“綱”:它將“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物”歸于“普遍性”的范疇,將“各個具體的矛盾”“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次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方面”歸于“特殊性”的范疇,將斗爭性歸于“普遍性”的范疇,將統一性(妥協)歸于“特殊性”的范疇,如此等等。特別要指出的是,在“普遍性”范疇里包括客觀、實踐,而“特殊性”范疇里包括主觀、理論,因此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道理也包括主觀與客觀的矛盾。通過這樣的歸置,“矛盾論思想”的概念體系就與蘇聯模式區別開來了。
有人說,《矛盾論》抄襲了楊秀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大眾哲學》又是從蘇聯哲學教科書那里被編譯過來的,所以它是抄走了樣的“二道抄”。對這個無知而又充滿偏見的說法我們必須追問:《矛盾論》抄襲的是“矛盾論思想”還是術語系統?如果是指前者,本文已經證明: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哲學教科書進入毛澤東的閱讀視野之前,其“矛盾論思想”已經形成。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們在下面將要進一步指出,“矛盾論術語系統”的形成雖然受到了蘇聯哲學教科書的影響,但是蘇聯哲學同時也是毛澤東哲學批判和改造的對象。
四、《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革新
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同屬于主流意識形態,但兩者的地位并不對等。蘇聯哲學教科書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包括歷史唯物論,但是辯證唯物論卻是更為基礎性的理論,歷史唯物論只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14](p177)。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開始接觸并接受這種“新哲學”,據此編寫了《提綱》。“新哲學”對他的影響還是很深的,他在《提綱》第三章中說:“完整的革命的唯物辯證法學說,創造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發展了這個學說,到了現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與世界革命時期,這個學說又走上了新的發展階段,更加豐富了它的內容。這個學說中包含的范疇首先是如下各項:矛盾統一法則,質量互變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雖然如此,毛澤東對這種“新哲學”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他對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共作了19 處批注,有13 處是內容復述,6 處打了問號。學術界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不過卻認為,毛澤東對蘇聯哲學教科書的態度是矛盾的[15](p5)。其實,學習與批判并存并不矛盾。毛澤東在學習的過程中對于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一些說法就已經心懷不滿,只不過當時沒有公開表露罷了。至1957年,他才公開表達了不滿,認為斯大林時期的哲學用特征論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講聯系而不講矛盾引起的聯系,講斗爭而不講對立面的統一[16](p194)。戚本禹曾提供一個細節:《矛盾論》原稿論述同一性和斗爭性的關系的時候寫了“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但陳伯達認為這是筆誤而把它改成“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如果這個細節屬實,那么我們可以說,強調“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正是毛澤東區別于斯大林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斯大林那里是特征論,而到了毛澤東這里,則是矛盾論。毛澤東將由三大基本規律和若干對偶范疇構成的“新哲學”改造為以“矛盾統一法則”解釋其他一切范疇的系統學說。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談到了這個問題:“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的并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基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環節,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于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1965年,毛澤東又多次講到這一個問題,尤其是在批閱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時,他稱三大規律并存的辯證法體系是“舊哲學”。他說:“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加以說明……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并存的方法不妥,這在列寧已經基本解決,我們的任務是加以解釋和發揮。至于各種范疇(可以有十幾種)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對立統一去說明。例如什么叫本質,只能說本質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6](p505-506)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毛澤東的看法,他們舉例說,牛頓力學也是三個規律并存,但它并不是多元論。不過毛澤東堅持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解釋其他一切范疇,由此用一以貫之的《矛盾論》取代了三大規律并列的蘇聯哲學教科書。
此外,在蘇聯哲學教科書中人的主體性沒有得到有力的彰顯,而以矛盾為核心的普遍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論體系則十分重視主體的能動性作用,強調矛盾轉化中主體的作用,指出“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3](p330)。這正是蘇聯實體性哲學模式所缺少的。這樣一來,以矛盾為核心的普遍與特殊相結合的辯證法體系就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新。
五、結語
通過本文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將《矛盾論》視為簡單的經驗堆積的“總結說”,還是將其視為蘇聯哲學教科書復制品的“抄襲說”,都是站不住腳的。雖然《矛盾論》中的思想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過程中逐步生成的,但這種總結并不是單純的經驗堆積,而是蘊含在經驗中的普遍概念形式由自發到自覺的升華過程。在此過程中,毛澤東選擇了蘇聯哲學教科書的術語系統作為表述概念的形式,然而他卻并沒有照搬蘇聯哲學教科書模式,而是對它進行了改造,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次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