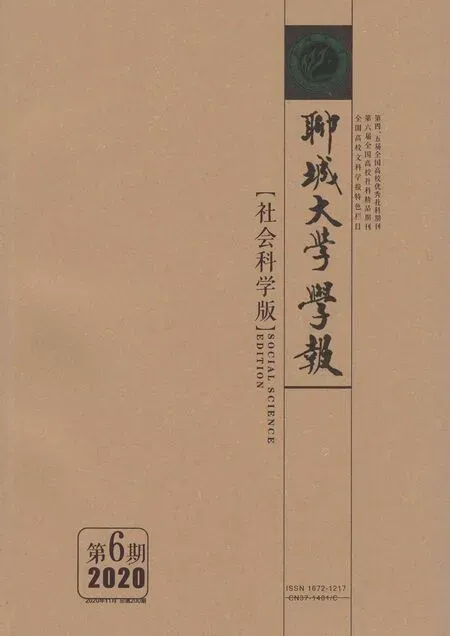1955年春河南省整頓初級社研究
李 貴
(鄭州輕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一、整社的緣起
1953年夏,全國一度出現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于10月份出臺了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對糧食進行有計劃的統一收購和銷售。由于當時全國農戶有一億多,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難度非常之大,于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變得非常迫切。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在會前和會議期間,毛澤東就農業合作化問題同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他說:“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發展”,“要分派數字”,“多了冒進,少了右傾”,“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倒錯了的,應當查出來講清楚,承認是錯誤,不然,那里的鄉干部、積極分子,就憋著一肚子氣了”。①《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6、117、119、120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會議制定了初級社發展計劃。會后,各地開始把發展初級社作為互助合作運動的中心環節。12月,中共中央進一步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初級社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經過一年的發展,到1954年底,河南省初級社達到27362個。②《中共河南省委員會指示各地整頓與鞏固農業合作社》,《河南日報》1955年1月22日第1版。期間,在河南省委的領導下,各地對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包辦代替等現象進行過一定程度的糾正。但由于合作化處在大發展階段,干部精力主要在辦社,對整頓工作抓得不夠緊,一些地區急躁冒進、建社粗糙的情況仍然比較突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強迫命令。如1954年11月,中共項城縣七區區委派干部趙明文到馮營村領導建社。他走到村東頭,碰見東頭的農民張文廣說:“西頭的走社會主義哩,你們是走還是不走,快說!”張文廣怕說“落后”,回答:“走嘛”。村東頭的農民認為自己的地壞,和西頭的成一個社,能沾點光(西頭的地好),也都去申請入社。村西頭的農民張書琴、張國均等去問趙明文:“咱們不是光西頭的組織一個農業合作社嗎?東頭的農民為啥也來申請呢?”趙明文大發脾氣,說:“看你們小農自發思想多嚴重,光興您活著,叫別人死……”這樣一訓斥,不通的也“通”了。①高家典:《在辦社工作中強迫命令造成的惡果》,1955年4月14日,第2版。滎陽縣司馬鄉擴社建社時,對入社的表揚,不愿入社的批判,宣傳不入社是自發勢力,致使部分中農入社不自愿,生產消極。②馬任平:《司馬鄉在鞏固社的工作中是怎樣貫徹階級政策的?》,《河南日報》1955年2月6日,第2版。宜陽縣五區王眷鄉第一社轉社時,四戶中農有顧慮不愿轉,鄉干部威脅說:“統購就是鞭子,你單干不轉社就多購你糧食,用鞭子趕著叫你轉。”③惠明深:《中共宜陽縣委不重視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領導》,《河南日報》1955年1月27日,第2版。四戶中農嚇的無可奈何地轉了。
(二)干部水平低,有松勁情緒,生產管理混亂。如長葛縣劉莊鄉的一個新建農業社社長程金牛,不知如何組織勞動力干活,苦悶地說:“在建社訓練班中學習的賣完了,社建成了,就是410畝地,男女勞力幾十個,指揮不開。”④張繼光:《中共長葛縣委召開新、老社長會議,集中交流鞏固農業合作社的經驗》,《河南日報》1955年1月28日,第2版。襄城縣第一區方窯鄉是該縣合作化試點鄉,全鄉657戶,1954年冬季新建了8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上原有的5個老社,全鄉有394戶入社。社建成后,正是“三九”天氣,大雪初晴。工作組和鄉支部普遍產生了松一口氣的思想,說:“建社是大事,生產、鞏固社是常事,社建成任務完成了,可該歇歇吧。”⑤李茂春:《要鞏固社必須抓好生產——襄城縣方窯鄉鞏固新建農業合作社的經驗》,《河南日報》1955年1月28日,第2版。宜陽縣一區石村鄉第一社,209個勞動力冬季很少有人搞農業生產,卻有八九十個勞力用將近90萬元的本錢上山捉狐子,有8人用16萬元買檁條、目椿架起涼子捉魚。全社積肥6萬斤的計劃,卻只完成了1.2萬斤。⑥惠明深:《中共宜陽縣委不重視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領導》,《河南日報》1955年1月27日,第2版。
(三)存在一些三類社。⑦中國共產黨在開展工作時,常將工作對象進行分類、排隊,以區別處理。通常分為三類,一類是好的,二類是一般的,三類是落后的,“三類”往往是工作的重點。三類社大都是在上級部門催促下匆忙成立的新社,基本不具備辦社條件。如獲嘉縣368個新社中,有15個三類社。這些三類社的特點一般是:基礎差,骨干弱,思想發動差,“四評”搞的粗糙,遺留問題突出。少數社基本沒有建成,既不像社又不像組,大部社員入社不自愿。六區落安營第三社土地、牲口均未評議,農具雖然評了價,但社員又各自搬回家去了。集體做活時為了講“厚道”,不進行評工計分。二區三位營一個社,副社長和部分社員已經到社外另找對象進行生產。⑧張明殿:《在整頓、鞏固農業合作社中應特別加強對三類社的領導》,《河南日報》1955年3月23日,第2版。南陽縣互助合作重點常莊鄉,全鄉除于新春社經過1954年秋收前整頓上升為一類社外,有9個二類社、2個三類社。二、三類社的共同特點是骨干少、弱,社員覺悟低,經營管理混亂,死分死記,社員生產情緒不高。三類社尚未樹立起貧農優勢,如第九社,13個管理委員中,貧農5人,中農8人,1954年種麥時,適宜種小麥的早茬地,種成豌豆大麥,麥播只完成計劃的63%;賬目也相當混亂。⑨李振華、蘇中鋼、張長義、李西坤:《南陽縣互助合作重點常莊鄉存在嚴重問題》,《河南日報》1955年3月31日,第1版。可以看到,當時對三類社的界定,除了一般的基礎薄弱、管理混亂之外,也把領導成員的階級構成作為重要參考指標。這與中共的階級斗爭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在此前開展的改造落后鄉運動中,毛澤東對此就有所闡釋。①1953年9月,毛澤東提到:“梁漱溟又攻擊我們的農村工作‘落后’,下級干部‘違法亂紀’。現在鄉村里面,所謂落后鄉確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為反動分子、憲兵特務、會道門頭子、流氓地痞、地主富農混進來當了干部,把持了鄉村政權,有些人還鉆到共產黨里來了。在嚴重違法亂紀的干部當中,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還有些是蛻化變質的干部。所以,在落后鄉,主要是打擊反革命分子的問題,對于蛻化變質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國,好的和比較好的鄉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對于這種情況,我們要心中有數,不要上梁漱溟的當。”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4頁。在此后全省乃至全國的農村整社中,從領導成員的階級構成方面界定三類社將成為一種固定模式。
由于上述問題,一些農民要求退社,如淮陽縣大張營鄉8個初級社,有186名社員要求退社,占社員總數的25%。②中共商丘地委:《關于正確處理退社農民問題的指示》(1955年4月29日),商丘市檔案館藏,1-1-28。對于農民的訴求,一些地方并未遵守“退社自由”的原則,而是設置層層障礙來阻撓,如夏邑縣韓守禮自發社中農社員韓文田,入社時牲口投資84元,出社時只準帶走20元,軋花車入社時作價300元,出社時僅作價180元。③中共商丘地委:《關于正確處理退社農民問題的指示》(1955年4月29日),商丘市檔案館藏,1-1-28。個別地方直接把退社說成是“破壞社會主義”,甚至把要求退社的社員關起來反省。④《如何正確地對待要求退出農業社的社員》,《河南日報》1955年4月26日,第3版。這就侵犯了部分農民尤其是中農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安。與此同時,農村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也全面展開。由于1954年夏季全國許多地方遭受嚴重水災,糧食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而糧食收購卻比原計劃多購了100億斤,以至于有些地方(包括河南)挖了農民的口糧。⑤《鄧子恢傳》編寫組:《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3頁。兩種因素交織在一起,致使1955年初農村形勢驟然緊張起來,河南及全國其它地區的一些農民開始破壞性的宰殺耕畜和砍伐林木。
二、整社的過程
面對被毛澤東稱為“生產力起來暴動”⑥1955年3月中旬,毛澤東聽取鄧子恢、杜潤生等匯報農村互助合作和糧食征購情況時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55頁。的嚴峻形勢,1955年1月4日,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向中共中央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制訂一個全國性的章程,明確農業合作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以規范干部行為,消除群眾顧慮;二是合作化運動轉向控制發展、著重鞏固階段。⑦《鄧子恢傳》編寫組:《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4頁。中共中央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于1月10日發出了《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54年新成立的合作社中,“有相當部分是無準備或準備很差的條件下成立的”。因此,“整頓和鞏固這40幾萬個社,已經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河南已決定從5萬個社減為4萬(1955年合作社發展計劃——引者注),這是適當的”。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一九五八—一九八一)》(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277、278頁。隨后中共中央又連續發出《關于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通知》、《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河南省委積極響應中央決策,于1月17日發出了《集中力量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要求各地、縣委集中力量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2月5日至26日,省委又召開了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檢查了1954年秋季以后,大部分老社中存在的盲目擴大偏向和新建社不鞏固等情況,要求整社工作,應發動社員制定切合實際的增產計劃,改善勞動組織和評工記分制度,健全財務管理制度,杜絕貪污,保證增產。①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南省志·共產黨志》第13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4頁。
3月22 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發出《關于鞏固現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60萬個,完成了預定的計劃。不論何地應停止發展新社,全力轉向春耕生產和鞏固已有社的工作。”“有些地方怕數字減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貫徹自愿原則,這是不對的。”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一九五八—一九八一)》(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308、309頁。此后,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轉入停止發展、全力鞏固階段。5月4日,河南省委也再次發出《關于大力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認真做好整社工作。
可以看出,短短幾個月內,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多次發指示并召開會議研究解決農業社的鞏固問題,這一方面反映了黨對整社工作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農村形勢確已非常嚴峻。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河南各地著手對新老農業社進行整頓。1955年1、2月間,鄭州、新鄉、安陽、南陽、洛陽等5個專區和64個縣先后召開了有新、老社長、駐社干部等參加的鞏固社的座談會議,總結交流經驗,具體布置如何結合生產做好鞏固社的工作。信陽、商丘、許昌3個地委也都召開了鞏固社的會議,許昌地委還組織了經驗報告團,到各地傳播鞏固社的經驗。安陽地區各縣還特別注意了對三類社的整頓提高,配備了295個較強的縣、區干部,幫助做三類社的鞏固工作。③《我省各地繼續貫徹省委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精神,開始重視新老社的整頓鞏固工作》,《河南日報》1955年2月3日,第1版。以下是幾個整社的具體案例:
襄城縣第一區方窯鄉的13個初級社建社遺留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各種組織不健全,思想比較混亂。社員有三種情況:少數社員特別是婦女產生了依賴社的思想,她們說:社建成了,有社長有委員,可用不著咱操心了,社里叫咱干啥就干啥。有的看到社里生產沒有頭緒,認為還不如自己單干時生產搞得好,思想動搖。方林寺社社員方群說:“我看社里亂七八糟,明年光等吃照顧糧了。”大部分社員積極要求搞好生產,社員方方說:“社建成了,不趕快搞生產,明年可有著急的時候了!”工作組和鄉支部摸清了這些情況后,首先召開了黨支部會,總結建社成績,評選模范,鼓起干勁。然后針對存在問題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扭轉松勁思想。在此基礎上開展了“四查、四算、三找”,討論搞好生產的辦法。四查:查人力——當前全鄉1102個男女勞力沒有全部投入生產;查畜力——全鄉有290頭牲口閑著;查肥料——全鄉6500車糞沒有送地;查農具——春耕生產需用的農具未修好。四算:算增產——全鄉6590畝麥子,每畝上兩車追糞,可增產四十斤,全鄉共可增產26360斤,可買雙鏵犁200部;算時間……“三找”,運用村算大賬,社算小賬,戶算細賬的方法,扭轉了干部和群眾的松勁情緒和社員的混亂思想,鼓起了大家搞好生產的信心。在普遍開展宣傳發動的同時,工作組干部和黨員分頭深入到13個社,組織社員開展冬季生產。以黨員王書江所在社為例,該社首先召開社務委員會,進行農活站隊,研究送糞和積肥的具體辦法,修訂了冬季生產計劃,將全社97個男女勞力組成送糞、積肥、撒糞、檢查農具、副業等小組,開展競爭。第二天,男女社員都積極行動起來了,一天送糞14車,積肥15車,積尿1500斤,積草木灰120斤,掏雞窩糞500斤。④李茂春:《要鞏固社必須抓好生產——襄城縣方窯鄉鞏固新建農業合作社的經驗》,《河南日報》1955年1月28日,第2版。
長葛縣到1月10日,已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468個,其中大部分是冬季新建的。1月28日,中共長葛縣委召開新、老社長會議,將新老社混合編組,相互解答問題,交流鞏固農業社的經驗。先進第二農業社社長王振法介紹了如何當好社長,共同第一農業社社長孫小狗介紹了經營管理經驗,光明第一農業社社長馬福海介紹了如何確保增產,東方第一農業社社長王國福介紹了如何管理好財務工作等。羅莊鄉新建金星第四農業社過去死分死記,兩個人一天只鍘草300斤,擔煤沒人去,社干部不負責任。社長馬喜周聽了老社介紹經驗后說:“俺社生產搞不起來的根,就是沒建立責任制,死分死記,不能獎勵勞動,回去后把勞力組織成隊,社干部分工負責,實行按件論工,我再深入生產過程檢查。”經過相互交流經驗,每個老社都和周圍的兩三個新社建立了聯系。①張繼光:《中共長葛縣委召開新、老社長會議,集中交流鞏固農業合作社的經驗》,《河南日報》1955年1月28日,第2版。
當然,各地整社并非都是一帆風順,也有不太成功的例子。同樣的政策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反差,是因為干部們的領導水平和工作方法不同。襄城、長葛等地整社干部通過深入調查,了解了社員群眾的思想,采取疏導的方法交流經驗、化解矛盾,使農業社鞏固了下來。平輿縣紅星農業社負責整社的主要領導則作風蠻橫,用強迫手段打壓退社群眾,雖然暫時穩定了農業社,但問題卻愈積愈多,矛盾愈積愈深,為以后的鄉村治理埋下了嚴重的隱患。
三、結語
總體而言,1955年春河南省的整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全省收縮減少了247個不成熟的初級社,其中多半轉為了互助組。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一九五八—一九八一)》(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401頁。截至6月份,全省4.4萬多個初級社經過整頓的達到3.1萬多個,占總社數的71.9%。經過整頓,一些社管理混亂的情況得以扭轉,三類社數量大大減少。據南陽專區對整頓過的431個社的統計,整頓前,一類社占38.7%,三類社占18%;整頓后,一類社占62.9%,三類社僅為3.2%。③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農業合作化運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頁。同時,河南省的農業社還到國家多方面的扶持。中國人民銀行和信用合作社在1955年上半年給予全省農業社近2000億元的農業貸款,平均每個社得到500萬到700萬的經濟援助。河南省供銷合作社為農業社準備了大批春耕生產資料,雙鏵犁比1954年多供應了7000多部,水車增加了好幾倍。省各級農林部門替農業社訓練了20萬名農業技術員、雙鏵犁手和會計人員。④《我省四萬多農業社受到國家多方面扶持》,《河南日報》1955年2月3日,第1版。農業社的發展逐步轉入健康軌道,大多數社都增了產,社員也增加了收入,河南省農村的緊張狀況隨之緩和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