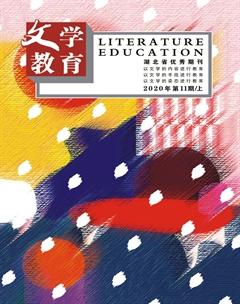論《浮生六記》中沈復人生悲劇性的成因
內容摘要:《浮生六記》是由清朝文人沈復寫就的一部散文記事佳作,蘊含著沈復為子、為夫、為父多重身份轉換中的人生思索,透露出深刻的悲劇意蘊。借助細讀其文本來探尋沈復人生悲劇性的內因與外因,剖析其性格悲劇、社會悲劇、命運悲劇的多元疊加,籍此解讀沈復作品背后的復雜內蘊。
關鍵詞:《浮生六記》 沈復 悲劇性 成因
《浮生六記》是沈復對其一生的自述,本六卷,因保存不善,今只余前四卷,后兩卷系后人偽作。沈復自謂“浮生若夢”,觀其所作前四卷,卷一曰“樂”,卷二曰“趣”,卷四曰“快”,唯卷三一部記“愁”。可見在他的意識中,愁僅占人生的一小部分。但細細探究,我們可從“樂”、“趣”、“快”中看出“愁”的伏筆,而這個“愁”正是沈復悲劇性的后半生。魯迅先生認為文學藝術起源于勞動、來源于生活,在悲劇對生活的美學關系問題上,魯迅指出了人們都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幾乎無事的悲劇”[1](93)。所以在沈復自認為平順若夢的一生中,卻暗含其人生悲劇性。雖然有父母親族,最后卻落得個離心不睦,有家不得歸;雖有恩愛的妻子陳蕓,但是“恩愛夫妻不到頭”;雖有一雙兒女,卻落得個女兒未及笄就為人童養媳,兒子年僅十八便夭亡的結局。
關于悲劇的成因,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美學家主要將其歸為“命運悲劇”和“性格悲劇”。“命運悲劇”也就是由于命運的不可抗拒,而導致人的災難和死亡;“性格悲劇”,則是指人自我斗爭的悲劇結局同性格的關系極大。[1](94)魯迅則認為,造成悲劇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制度。[1](95)從此三方面對沈復的人生進行探究,可以深入解析其人生悲劇意蘊的內、外因。
一.命運悲劇
《管子》有云:“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四民也”,將中國古代社會分為四個階層,在《群書治要》中也多次提到士、農、工、商,可見這種劃分方法是歷代所認同的。[2](276)這種觀念決定了“士”為最高。明清之時,奉行八股取士,考的是四書五經,而這些經義“既非經傳,復非子史”[3](908),因此所取之士多半空有滿腹經綸,而無實干經驗,使得他們需要專業的行政人員來輔助,也就形成了私人幕府。這些幕府里的幕僚并不是正式的官員,而是相當于師爺的角色,并不受命于朝廷,而是受聘于州縣,他們薪金也由官員私人承擔[4](2)。人人都知科舉之難,正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寒窗苦讀數十年也未必混得一官半職,因此很多下層文人都選擇了入幕這條相對簡單的道路,既不辱沒斯文,也更容易就職。沈復其父沈稼軒就是如此,而他對沈復的人生規劃也是子承父業,因此沈復在命運的安排下走上幕僚的道路。
但沈復自詡文人,而非“士”,他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相反他身上文人的清高氣質,使得他看不起官宦權貴,不愿與之為伍。寄居蕭爽樓時,他提出四忌:“談官宦升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5](45)可見,不只是沈復,連他身邊的友人也多是瀟灑豪士,對入仕很是不屑。還有一次他和友人一起到寺廟游玩,寺中僧人向其一行人詢問“城中有何新聞?撫軍在轅否”[5](45),其中一友人“忽起,曰:‘禿!拂袖徑出”[5](45),沈復同另一友人也“忍笑隨之”[5](45)。更是佐證了這些文人的清高和對世俗官場的不屑一顧。
沈復雖然沿著命運的安排成為了一名幕僚,但又由于他志不在此,導致他自己對這個職業并不熱衷,使得他一生幕無定所,按沈復記載“余游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5](69)。這樣的漂泊經歷自然不可能完成“立業”,更不能給妻兒一個穩定的家。
沈復也并不是沒有嘗試過反抗命運,他在游幕期間也曾兩度經商,但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是在二十六歲,沈復“自績溪之游,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因易儒為賈”[5](79),由于官場黑暗他不愿與之為伍,便同姑丈袁萬九合伙販酒,然而不到一年,遇林爽文之亂,折本而歸。另一次是他三十一歲時赴粵經商,這一次小有收獲,并且在廣東過了一段花天酒地的生活,適時“合幫之妓,無一不識,每上其艇,呼余聲不絕,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5](89)”,最后自然是揮霍一空。
二.性格悲劇
沈復是一個“天真”的人,在家有父親的幫扶,不愁吃穿生計;娶妻后有妻子的包容,包辦衣食,補貼家用;妻子死后有朋友的愛護,借其錢財,贈其小妾,使得他始終活在浮生大夢中,從來都是個少年心性,身上有著豪俠之氣。但他是完全不考慮自身情況的豪俠。
沈復對親戚豪俠。他曾經讓陳蕓典當銀釵湊錢十金借給姐夫范惠來,在二人想搬離華氏的住處自立門戶卻無錢可用的情況下,若非蕓娘提醒他可以借此向姐夫討個人情,他也就將這事忘得一干二凈了。可見他豪爽的性格使然,絲毫不顧及自己的生計。
沈復對手足豪俠。他對弟弟更是縱容無度,弟弟害陳蕓背了黑鍋,夫妻二人被逐出家門,在蕓娘死后沈復回到家中,弟弟以父親仍余怒未消的理由將沈復又勸回了南方,父親的死訊也被弟媳攔著未告知沈復,要不是女兒來信,他連奔喪都不知情。在沈父死后,他回到老宅祭拜父親,弟弟又假借上門討債人之口,暗示沈復不要爭遺產。沈復依然選擇縱容,說“大丈夫貴乎自立,我既一身歸,仍以一身去耳!”[5](65)轉身進了深山。最后還是他女兒看不下去,拿了一些祖父的遺物給他。在赴崇明代筆好不容易賺了“二十金”后,回家祭拜父親,弟弟借沈復兒子逢森之口讓其出錢二十金以資喪事,沈復想都不想就把剛到手的報酬全部要交給弟弟,還是友人夏揖山看不下去了,幫他出資一半。讀之,真是令人可悲又可氣,悲其被弟弟啟堂排擠,氣其不顧自身情況的慷慨大方。
沈復對友人豪俠。他在陳蕓死后一度窮困潦倒到無處可住,連陳蕓的安葬費都是友人胡省堂贈得十金,之后他甚至在陳蕓墓前向她“佑求一館”,卻將代庖所得的“二十金”給陳蕓扶靈的費用轉手借給了失館的張禹門,只因他是同鄉,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妻子的遺骨無法歸故里,自己也無住處的凄慘境況。
沈復作幕時幕無定所,不被雇主重視。為商時時運不濟,又耽于享樂,可見其并沒有經商才能。平時要靠蕓娘里外打點,做女紅補貼家用。但是他的性格卻是為人豪俠。對親戚豪俠,對朋友豪俠,從來不計較金錢上的得失。自己在生活中也是豪爽不知節制的,稍微有些收入便為了享樂而大肆揮霍,在無錢可花的時候即使“典衣沽酒”也要喝個淋漓暢快。這樣的性格必然會導致他悲劇的結局。
三.社會悲劇
沈復的人生悲劇源于命運,源于性格,也源于社會。沈復是當時社會中的異類。從《浮生六記》的開篇就可以看出來,第一卷大膽命名《閨房記樂》,在那個封建禮教的時代,如此放浪形骸不可謂不驚駭。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系,而于正式男女關系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于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此后來沈三白《浮生六記》之閨房記樂,所以為例外創作,然其時代已距今較近矣。”[6](103)可見沈復的特例。
沈復為當時社會所不容,但又依賴于社會,他離不開封建家庭的庇護,一旦被逐出家門就失去了經濟依托,變得舉步維艱。沈復曾兩次被逐出門,如果沈復真的是一個灑脫不羈離經叛道的人,被逐出家門后他大可自立門戶。但沈復不然,離家后寄居在友人家里,生活拮據并得過且過。兩年后,沈復的父親得知前因后果,一句:“前事我已盡知,汝盍歸乎?”[5](51)就使沈復迫不及待地帶著妻子回到了父親的羽翼之下,可見沈復表面上不拘禮法灑脫不羈,實則在內心卻認同當時的家長制,對封建家族極其依賴,父親一說原諒,他便立馬忘記了之前的所有不快,欣然回歸到家族的庇佑下。
他對于父權制的不反抗,本質上就是對封建禮教的變相認同,看似灑脫不羈的對于誤會的不解釋,其實是對封建家族的畏懼妥協。正是由于他自己都要依賴家長,更不能指望他承擔起為人夫、父的責任。結局自然是這個小家分崩離析。沈復的人生悲劇也是他在封建社會中的必然結局,他對于封建制度的妥協也正是他悲劇的根本原因。
四.結語
沈復后半生的悲劇性即源于內,也源于外。沈復不滿命運的安排,但也無能反抗;他性格豪俠,卻從來不考慮自身情況;他灑脫不羈,為社會所不容,卻又依賴著封建家族。正是“命運”、“性格”、“社會”三重因素的矛盾作用下,使得沈復坎坷半生,讓人不免嗟嘆唏噓。但在沈復眼中,他的一生卻充滿“閑趣”,宛若大夢一場。少年時,父親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環境,使他打下牢固的文學基礎;成年后,妻子的支持讓他衣食風雅,即使事業失敗得到的也是諒解和包容,為他打造了輕松的學習環境;兒女的懂事、善良,讓他毫無后顧之憂,人到中年還得以攜小妾游歷琉球等地,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
家人對他的保護,讓其回顧一生時,眼中多是生活的“閑趣”,對于“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5](49)他的回答是“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5](49)他不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具有悲劇性的,反而用浪漫的筆觸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浮生六記》。我們或該慶幸,正是這樣“一個謙卑而渺小的生命能快樂的過一輩子”[7](67)才讓我們看到“宇宙間之至美”[7](67)。
參考文獻
[1]夏明釗著,我的魯迅研究[M],東方出版中心,2013.第93-95頁
[2]蕭祥劍著,群書治要五十講[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第276頁
[3]顧炎武.日知錄校注[M].陳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第908頁
[4]陳穎超.《浮生六記》與清中期下層文士生活[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07.第2頁
[5]沈復.浮生六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6]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1.第103頁
[7]周質平著,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九州出版社,2012.06,第67頁
(作者介紹:景煒,喀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