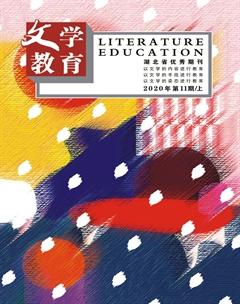象征主義的潛意識揭示:論《藥》的“矛盾”內涵
內容摘要:魯迅的《藥》可謂之“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從中途起筆,言語凝練,體現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啟蒙特色。《藥》中多層次的矛盾交織,表現了魯迅苦悶求索的心路歷程和復雜矛盾的心情,也反映了時代的矛盾狀態,構成了這部小說象征主義的潛意識揭示。本文試從命運與時代、困境與擺脫困境的徒勞、理性精神與感性追求三個角度來闡述《藥》的“矛盾”內涵。
關鍵詞:魯迅 《藥》 矛盾
一.命運與時代
《藥》中典型性人物的性格命運反映了人與時代的矛盾,自然而然構成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華老栓悲劇的命運并不由于他的罪惡,而是他的愚昧。作為一個救孩子的父親,人倫之本能讓這個形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目的與動作的內在矛盾,抽象倫理之間的對立,荒謬的認知和矛盾的心理變化,使這個可悲形象的片面性顯露無遺。生活的苦難催化了他精神的病態,歷史和社會的原因造就了他的愚昧。魯迅透過華老栓一家的命運折射了時代和民族的歷史軌跡。而夏瑜這樣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在社會和時代不具備種種使得個體進行的實踐得以成功的條件的情況下,并不能實現他們的本質力量。雖然從性質上講是“善”和“美”的,但革命者的實踐與“真”發生了嚴重的沖突,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反映了個人能動性和時代局限性之間的矛盾。魯迅一方面把人物放在中國現實的關系中再現,用阻拒性的言語勾勒出當時未經徹底革命的閉塞動蕩的吃人社會這一典型環境;另一方面,映射出在典型在環境中生存并腐蝕的典型思維,把時代問題暴露出來。從而通過對國民落后思想和冷漠態度的批判,導向對舊民主主義革命不徹底性和悲劇性的思索,揭示了未覺醒的民族是導致革命走向必然失敗的原因之一。作品中沒有對革命熱情的贊美,也沒有對國民的憤怒鄙視,可以說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魯迅將對民眾的批判與同情,對革命者的痛惜與哀嘆都化作冷靜地側目與旁觀,以冷的視角展現烈的沖突,有如醫者對待病體與死亡的冷靜,冷到發熱,冷到讓人害怕,個人的命運在時代的冷酷中變得蒼白無力。
二.困境與擺脫困境的徒勞
魯迅稱自己的小說“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①作為新文學的先驅,魯迅始終在用文學去揭社會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在追尋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中,魯迅敏銳洞悉了中國思想的舊與劣。從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開始,批判的矛頭直指罪惡的封建制度。《藥》也是同一時期的新文學作品,提出了療救中國的問題,完成了對封建思想意識和封建愚民政策吃人本質的深層揭露,深化了封建思想吃人的總主題。身陷落后黑暗的舊社會,魯迅在擺脫困境的求索中不斷碰撞,在反叛和變革精神的洗禮下不斷反思。狂人的質疑和呼喊,昭示了大膽懷疑和否定的積極精神。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結合的創作方法,塑造了“人血饅頭”的意象,活脫成像,把對肉體和鮮血的踐踏上升到對思想和靈魂的褻瀆,運用象征、隱喻的創作手法,一語三關地寄寓了擺脫困境的戰斗深意。小說中典型的茶館環境囊括了各類人物的嘴臉,看客的空虛與麻木,民眾的卑怯勢利和是非不分,暗示了辛亥革命的悲劇,體現了“人非人”的荒誕形態。在封建愚民政策奴役下的壓抑社會里,清醒地追求“真”,就被視作“反”,夏瑜是,魯迅又何嘗不是,在寂寞里奔馳的勇士成為了笑柄和被誣蔑為瘋子,反抗即是徒勞。社會的病態似一面鏡子,使雙方都能窺測到自己的病容而引起療救。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藥呢?思想的洗禮和民眾的覺醒。魯迅從整個國民的思想和精神出發,圍繞思想痼疾進行典型創作,一針見血地暴露了人、社會、革命的三重困境,引導人們在笑與哭的同時反思并自省,同時也鮮明指出了革命首要任務是進行國民改造。最后墳上兩位母親的偶遇中花環和烏鴉的曲筆,體現了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思想。正如魯迅在《野草·希望》中表達的心情:“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②從“困境和擺脫困境的徒勞”這一對矛盾理解,這樣的安排是“絕望中的希望”與“希望中的絕望”相互作用的結果,適應了讀者的精神心理需求。
三.理性精神與感性追求
隨著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文學思潮和哲學思潮的涌入,現實主義、象征主義、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叔本華悲觀哲學等都對魯迅的文學創作思想起到重要的影響。③一方面魯迅強調作品對國民的啟蒙作用,又以此抒發自己內心的憤懣與希冀。“生物進化論與階級斗爭觀念”、“個性解放與群眾創造歷史觀念”成為了他創作思想的主旋律,表現了五四時代的叛逆和自由。棄醫從文背后是魯迅在失望中的關注中心由救治病人的疾苦轉化為三個問題:一是怎樣才是最理性的人性?二是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④辛亥革命的失敗使魯迅一度失望,《狂人日記》的發表沖破了沉默,強調了生存斗爭、新陳代謝、精神發展等要素。從魯迅主張的“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⑤體現的也是斗爭圖強意識,他堅持與滯礙的庸眾對抗,呼吁著精神界的戰士,以達到推動中華民族思想解放的目的。《藥》從言語、形象、意蘊三個文本層次增加增加了讀者的想象和補充,表達著對社會人生的探索與思考,貫穿著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批判精神,在理性層面加深了對現實革命斗爭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當罪惡和丑陋讓這世界變得沒了中心、主宰和理性,魯迅就化身為孤獨的流浪者,一面理性地舉著新思潮的旗幟,一面懷有無路可走的感性情懷。《藥》處處可見令人窒息的壓抑描述,訴說著感傷的悲情。哪怕是文中最輕松熱鬧的談藥部分,眾人嬉笑聊天的場景,還有對小栓病情“包好!”的判斷與安撫,看似是店里的“活氣”與刑場的“死氣”形成鮮明的對比,對買藥與吃藥可怕氛圍起到了緩和作用。實則悲從中來,形喜而實悲,死亡不僅變得無意義,人生也成為了多余。蘊藏著作者深深的無奈和悲哀的主觀感性思想。透過文字,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孤獨、煩悶、憂愁的魯迅,類似海德格爾所說的“煩”。只有在這樣的感性境界里,魯迅才能感受到真實的自己,也才能超越自己的界限,實現對社會和未來的追求。既然當下沒有可憑借的力量,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不能證明它的存在,但仍可滿懷期待。所以魯迅雖然不知道這世界是否可改造于將來,但卻先行發露各樣的丑與惡,撕下那虛偽的假面具。表現了魯迅苦悶求索的心路歷程和復雜矛盾的心情,也反映了時代的矛盾狀態,構成了這部小說象征主義的潛意識揭示。
注 釋
①魯迅:《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七卷,第389頁。
②魯迅:《野草·希望》,《魯迅散文集野草》,第20頁。
③④朱棟霖:《中國現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2頁,第29頁。
⑤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6頁。
(作者介紹:蔣樹青,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無錫衛生分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