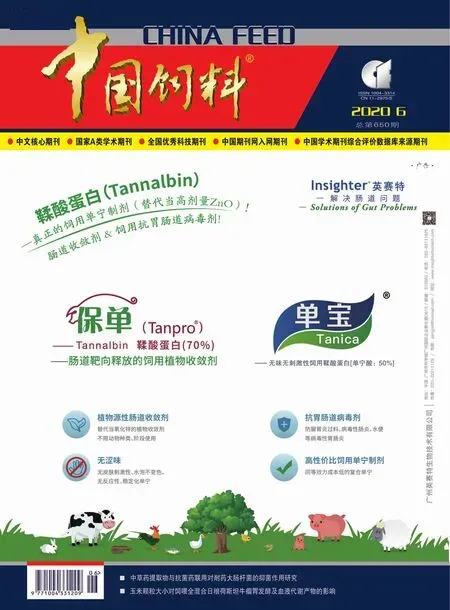飼料、動物及動物產品貿易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高尚君,孟令巖
(濟寧學院,山東曲阜 273155)
1 前言
在過去的60年里,全球畜牧業的變化尤為顯著。肉類生產從1970年的1.2億t增加到2010年的2.7億t,在同一時期,牛奶產量從4億t增加到6.9億t以上。發展中國家的肉類和牛奶量的年增長率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其中肉類發達國家增長1.9%,發展中國家增長8.1%,牛奶發達國家增長0.7%,發展中國家增長4.1%(李江華等,2017)。這些變化是由需求因素和供給因素共同驅動的。
2 飼料、動物及動物產品貿易現狀
2.1 需求驅動 發展中世界,特別是拉丁美洲和亞洲新興國家的人口變化、城市化和經濟增長正在迅速改變該地區糧食消費模式。發達國家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實現了糧食轉型,而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現在遵循類似的模式,但速度明顯加快。Popkin(2006)研究表明,新興國家的過渡期縮短至20年,其他發展中國家縮短至40年。這種食物過渡過程包括兩個步驟,第一個是定量,它對應的是熱量攝入的增加,而所有食物的熱量增加比例是相等的。第二種通常被稱為食物過渡,它是定性的,一旦能量需求飽和,飲食結構會發生變化,如人均谷物和蔬菜消費量減少,而糖、脂肪和動物產品的消費量增加。
當今,推動發展中國家糧食過渡進程的因素與過去發達國家相同,只是現在這個過程更快,因為這些驅動因素在發展中國家比過去在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這種加速可以通過大型超市的增長率來說明。從1950年到本世紀頭十年的50年間,它們與大型食品制造商共同改變了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市場,從1990年到2015年的20多年時間里,中美洲、拉丁美洲和亞洲也發生了類似變化(Reardon等,2016)。當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同,國家之間或同一國家不同家庭的飲食仍然存在差異,這可以從歐盟各國的肉類消費情況看出。盡管存在部分趨同,但人均消費水平仍存在顯著差異,就牛肉而言,德國的人均年消費量為13 kg,而法國超過26 kg。就豬肉而言,英國人均年消費量為28 kg,而德國和西班牙分別為56和60 kg以上,就家禽而言,德國和意大利的人均年消費量約為15 kg,西班牙和英國約為28 kg(Combris,2016)。
2.2 需求和供給同時驅動 畜牧業變化的主要驅動力是需求。人口、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伴隨著日益復雜的食物鏈與越來越多的加工食品,是推動糧食需求的主要因素,最終推動畜牧業的發展。但所謂的養殖業發展驅動也有供應方面的根源,特別是在遺傳、營養和育種方面的改進。與此同時,許多新技術被開發出來,改變了畜產品生產和加工,可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Narrod等(2011)認為,在過去的十年里,發展中國家已逐步開始建立更專業的畜牧養殖方式,雇傭大量勞動力,企業資本注入和購買力提高,形成一個更加統一的動物產品質量標準。
2.3 通過動物貿易、動物產品和飼料谷物來滿足食品需求 糧食轉型和養殖業發展的一個典型和直接后果是國內谷物利用從人類消費轉向動物飼養,而第二個后果是發展中國家的肉類和牛奶產量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得多,以滿足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為強勁的國內需求。聯合國糧農經濟組報道,2010~2019年間,發展中國家的牛肉消費增長前景為20%,而發達國家為7%(FAO,2012)。但這種積極的生產趨勢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正在滿足國內民眾對動物、肉類和奶制品日益增長的需求。縱觀歷史,發達國家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動物、肉類和牛奶的供應者,即使一些發展中國家部分地區能滿足越來越多的國內需求,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消費也超過了生產。因此,他們需繼續依靠進口來滿足自己對動物和動物產品的需求,以適應國內消費的增加。我國在動物和動物產品貿易方面(包括乳制品)的增長速度在過去二十年中是國內生產的2倍。這意味著,盡管動物、動物產品貿易只占大約12%的生產或消費,但這一比例在過去20年里一直在增加,這是最基本的需求,而最終的目的是實現全球糧食安全。針對上述方面,貿易尤其重要,因為它不僅局限于動物和動物產品,還包括飼料原料。
當然,這種動物及其產品的消費、生產和貿易趨勢也掩蓋了世界各區域和產品功能的差異。阿根廷、巴西、印度、中國和泰國的情況與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中東)形成對比,因為所考慮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公司的進出口差額以數量或價值界定的區域貿易差額在第一類國家中有所改善,但在第二類國家中則惡化。針對牛肉,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凈出口國,如印度現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牛肉出口國,其不斷擴大養殖規模,生產效率提高,相對于巴西更具有價格優勢(USDA,2012)。與其他肉類形成對比,特別是豬肉和禽肉類,發展中國家是凈進口國(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豬養殖國家,也是最大的消費國,每年也會進口部分豬肉)。此外,即使某個發展中國家的動物產品貿易平衡有所改善,這種積極的趨勢也會掩蓋谷物和其他飼料原料平衡惡化的事實。
3 發展趨勢
3.1 飼料、動物和動物產品貿易的安全 正常情況下,新興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動物產品消費會繼續上升。實踐中,發展中國家將推動全球對所有農產品需求,包括活的動物及其產品,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對牲畜產品的人均需求增長近一倍。許多發展中國家將繼續依靠進口直接和間接地滿足日益增加的需要,其中直接進口是因為國內畜牧生產的增加不足以滿足需求增加,而間接進口是因為滿足國內需求的養殖規模需要進口更多的飼料原料。
作者推測,未來可以以可持續的方式利用供需杠桿來實現養活地球上的人類,包括發達國家和全球富裕家庭降低肉類消費,減少整個食物鏈中的食品浪費,尤其是在分配和最終的消費層面。同時,貿易和環境應密切聯系在一起,而今天的情況并非如此,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條例框架內。由于發展中國家大多數貧困人口是農民或農村家庭,面臨的挑戰是確保貿易規則不損害當地農業生產增長,而農業生產增長是減少貧困和營養不良,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必需的。這意味著運作良好的,針對衛生、教育、農業和農業食品的部門機構需要精心設計宏觀經濟政策,如發達的基礎設施和足夠的投資(賀麗潔,2017)。
3.2 促進和穩定貿易 貿易安全問題尤其重要,因為農產品貿易(特別是動物和動物產品貿易)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品種(牛肉、綿羊/山羊肉、豬肉、禽肉和奶)上,且進出口都是如此。在牛肉出口市場中,印度、巴西、阿根廷、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占主導地位,而在進口方面,美國排在首位,其次是俄羅斯、日本和歐盟。就禽肉而言,巴西和美國目前占全球出口的70%以上。以豬肉為例,美國和歐盟目前占全球出口的55%左右,其次是加拿大(約20%)和巴西(約13%),在進口方面,日本、俄羅斯和墨西哥占進口總量的50%。這些數字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很容易受世界市場動蕩的影響。
3.3 改善關于畜牧業生產、貿易能源和環境足跡 生產肉、蛋、奶依賴于對越來越多的谷物原料,且由于谷物原料的運輸成本低于動物,用進口的谷物原料飼養動物比直接進口動物成本低。盡管未來幾十年運輸成本可能會增加,但作者推測這種優勢至少在未來20~30年不會消失。根據FAO(2012)報道,世界谷物產量的1/3用于飼喂動物,但國家、動物品種和生產系統的不同也存在巨大差異。在養殖業不斷發展的進程中人們越來越擔心,在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日益缺乏的情況下,所有這些演變可能對世界糧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用谷物原料飼喂動物是比較浪費的,因為其轉化率低(生產1 kg肉平均需要3 kg谷物原料),同時用谷物飼喂動物也會對環境造成影響。Bouwman和Booij(1998)提出了一個關于全球飼料使用和貿易中氮含量的估計,其研究結果表明,谷物和其他飼料的凈貿易量占世界動物總氮消耗量的比例顯著,但很小(為4%~7%)。但他們預計由于貿易擴張,這一比例將在未來幾十年上升。此外,大量谷物用于動物養殖也會引發一系列問題,如高蛋白飲食引發的健康問題,動物集約化生產排放的氨和硝酸鹽帶來的環境污染、溫室效應問題。
另一方面,肉類和奶制品是蛋白質、微量元素和維生素的重要來源,許多非常貧困和貧窮家庭通過增加動物產品的消費來改善營養缺乏。作者也認為,農產品價格在未來幾十年可能會處于高位,這不僅針對谷物等飼料原料,而且也針對肉、牛奶和奶制品。雖然畜牧生產者將受益于高價格,但同時他們也將面臨飼料原料價格上漲帶來的收益損失。
4 結語
就活動物及其產品貿易而言,需要解決以下幾方面的挑戰:(1)國際貿易規則,特別是市場準入方面;(2)食品安全問題,國際貿易對疾病傳播的促進作用及各國為防止疾病傳播而制定的規則(貿易規則可以防止發展中國家從事動物和動物產品的國際貿易);(3)協調環境和動物福利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