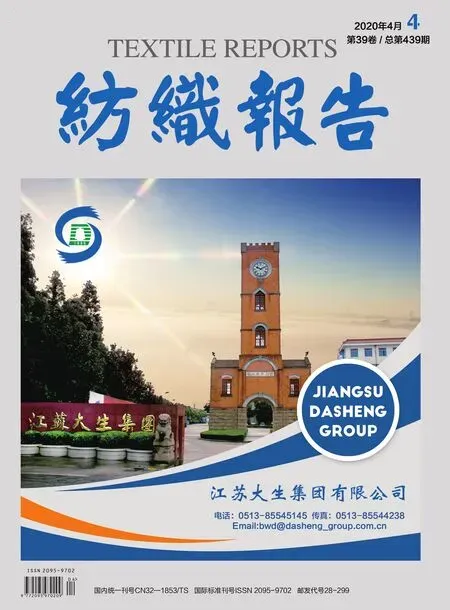永續設計與時尚再造的應用與探索
趙 琛
[Chiu-Design(Paris)Studio,法國 921000]
早在2005年,Schorand Juliet的研究就指出,時尚工業是世界上最不永續的產業之一。服裝行業指望消費者因價格低廉而購買更多衣服,是不可持續的。
環境永續與企業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假設消費者都具有環保及綠色消費行為的概念,對于自己所購買的產品,是否在意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這會不會影響消費者對該商品的購買意愿與沖動購買程度,甚至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忠誠度呢?有沒有想到過去買一件便宜的衣服,竟然會造成一個國家的勞工失業,同時助長著另一個國家的勞工被血汗剝削?
可喜的是,時尚界這幾年興起永續風,年輕設計師開始使用回收資源再制新衣;“買少但買好”成為大家新的消費趨勢。在守護環境的同時,也為時尚文化注入新活力。
1 永續時尚/道德時尚/時尚再造—在全球與中國
(1)“道德時尚”(Ethical Fashion)以較廣義的理解方式,主張的是在利益最大化之余,又能將對環境的沖擊最小化。較狹義的又分為“公平貿易”和“有機”兩種原則,前者在生產流程上講求勞工的合理待遇,而后者則是追求有機自然且對環境無負擔的制作工法。道德時尚的概念也經常與“綠能時尚”和“慢時尚”并為一談,在這個環保與人倫意識漸強的時代更獲重視[1]。
時尚再造是集中設計概念,以舊創新以及從環保出發,Recycle(再造)與Upcycle(回收藝術或升級再造,即把便宜的東西轉化成昂貴的物品,賦予它更高的環保價值)并行,回收業界也要向upcycling方向發展,重新給予舊衣產品生命周期,以達到節能及環保的大原則。眾多品牌開始選擇以有機面料替代皮草與合成材料,并從供應鏈上尋求排除污染的方法,二手衣回收也已初具規模。
在環保未成為時裝界的議題之時,Stella McCartney已提倡不用皮草、皮革及PVC,并積極發掘可持續發展、對環境無害的物料來制衣,證明時尚與環保可以共存。品牌采用的合成物料如尼龍、聚脂纖維等全是由廢料再生而來,例如Econyl再生尼龍是由工業塑膠、廢棄布料和魚網循環再造,而再生聚脂纖維則是由廢棄膠樽循環再造,變成天橋上的人造皮革大衣、手袋。2017年開始,Adidas by Stella McCartney系列的運動外套、運動鞋就全以再生聚脂纖維制成,同樣舒適耐用[2]。
(2)在中國,環保產業初具雛形,環保時裝在中國服飾市場仍處于消費主義盛行期,消費者消費意愿強烈,但消費意識還不夠成熟。由于可持續時尚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反消費主義”的體現,因而推廣可持續時尚仍然需要更多時間。但無論是從生產、消費還是傳播的角度來看,中國可持續時尚已經起步,一旦人們打通了可持續時尚與商業邏輯之間的橋梁,這一理念對于國內服飾品牌或許是一次新的機遇。特別是在當下經濟活躍的中國市場,可持續時尚缺乏的并不是成熟的市場條件,而是創新的時尚革新營運模式和真正有吸引力的產品[3]。
2018年哥本哈根時尚峰會一場以中國可持續時尚為題的小組討論,國內服飾品牌第一次登上可持續時尚的國際討論平臺,可以看到以下國內幾個服飾品牌在可持續時尚方面已經開始了初步實踐。
鄂爾多斯:希望在保證草場生態環保的基礎上,通過優化垂直供應鏈,加強產品追蹤與預測,更加精準地控制庫存,以減少資源閑置與浪費,也在通過強調產品耐用度和情感價值來增強產品的可持續性,例如在門店中提供產品回收與修理服務。值得關注的是,擁有垂直供應鏈的鄂爾多斯都在產業鏈多個環節觸及可持續時尚,從生產到設計,從情感價值到銷售,而不僅是單一層面。
江南布衣:最初選擇使用天然環保面料的動機是防止競爭對手抄襲。價位更高的環保面料在品質上與其他產品拉開距離,隨著近年來中國市場消費升級的趨勢擴散,消費者越來越看重品牌價值,對可持續時尚趨勢更為敏感也更愿意接受。江南布衣對可持續時尚的解讀也是回歸產品,將產品打磨得更具獨特性與吸引力。
2 挑戰:快時尚
據外媒報導指出,若快時尚在時尚產業中的領頭羊角色再不改變,時尚產業2050年碳排放量可能將占全球碳預算(Carbon Budget)的1/4。
快時尚提供時尚流行款式及元素,以價低款多為特點,常年吸引顧客購買。在當今快速以舊換新的步調及大量平價品牌沖擊之下,眾多品牌有別于以前以春夏秋冬四季區分上新款式,而加入每周推新款的快時尚行列中。然而,即使眾多消費者意識到快時尚所帶來的問題,但當在產品喜好和環境拯救之間做選擇時,大多顧客并不會為保護地球而犧牲自己的需要,經常因為即興的沖動而購買一堆不需要的東西,而價格始終是主要影響消費者對于服飾購買意愿的考慮因素之一(奧地利周報2019-02)。
經濟學家托馬斯·賽德拉切克Tomá? Sedlá?ek曾提到“時裝產業復制了市場經濟癥侯群”,全球每年大約生產800億件服裝,全球生產聚酯纖維大約500萬t,同時,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要丟棄相當于20 kg的各式衣服。出于推崇獲利的目的,在成本上不但把工廠遷至第三世界國家(比如孟加拉國國的工廠)壓榨當地勞工,且衣物材質大多選用廉價物料。
尤其近兩年人工智能的崛起,機器人大量應用于服裝生產行業中,它們可以完成服裝生產的各項任務,包括裁剪、縫紉和檢驗質量等,這將進一步降低服裝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二手衣物里摻雜著大量根本不適合捐獻給他人的衣物,將這些衣物分類所需要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即使捐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過量的“善意”近期也被證實反而毀滅了當地的制衣產業[4]。
3 機會:慢時尚
摩根士丹利2019年10月的一份報告數據顯示,去年美國服裝市場已經進入了結構性衰退。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服裝服飾的銷售正以驚人的速度往線上轉移,對傳統服裝銷售發起了巨大挑戰,同時也令消費者能夠更加容易購買到更多衣服。“快餐時尚”帶來的幸福感也達到了頂峰,買的越多也越麻木,消費者對購買新衣的滿足感和幸福感已在邊際遞減之中[5]。
今年新冠肺炎帶來的疫情,迫使經濟處于停滯狀態,似乎喚醒了許多企業的反思。許多品牌因為疫情帶來的停滯,重新思考未來企業的運營模式及品牌定位。而消費者面臨失業和收入下降的局面,因此他們會減少購買非必需物品如服裝、家具、電子產品等,這對百貨業和服裝業造成了不小的損害[6]。
在中國尚未形成蓬勃發展之勢時,慢時尚已逐漸成為歐美國家對時尚的成熟認識。2020年,全球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更令消費者開始厭倦僅停留在頻繁出新、設計新潮的快時尚服飾。這時,以經典、持久、獨特為特色的慢時尚回歸了,節儉再度成為生活的主旋律,消費者考慮更多的是商品的長期價值。例如作為慢時尚主要標志的經久耐用的定制時裝;以每款每色只制作一件的特別作法,令消費者重新重視一針一線的縫制等。慢時尚的興起,讓消費者更有意識地選擇自己的消費行為,進而做出符合自己信念的行動。無論是以實質的消費支持永續的品牌,或將快時尚的單品反復穿搭、不隨意丟棄,令時尚與永續兩個看似相悖的元素達到共存。
4 結語
身為兼顧創意與社會責任的服裝設計師,應如何賦予回收再制品實用又不失潮流的新價值?循環將是時裝行業的唯一出路,所有商品必將遵循升級回收、再生和二手商業模式。企業抵消碳足跡并積極回饋社會勢在必行,品牌必須改變經營方法向越來越有意識的消費者族群證明其真正致力于永續時尚的發展。期盼著設計師、企業從產品循環(原料、生產、加工、零售到消費者使用再到丟棄)的每個環節都能想到可持續發展理念,將永續的理念植入產品設計的最前端,就能為這個社會節約更多的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