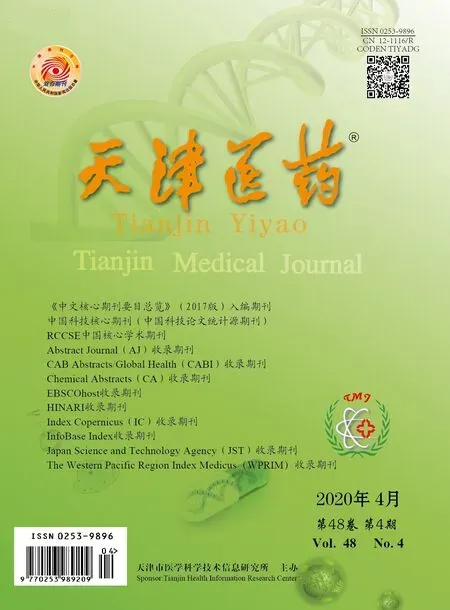小膠質細胞與膿毒癥腦病的研究進展
莊欣琪,謝克亮,于泳浩△,盧悅淳,呂國義
膿毒癥腦病(sepsis associated encephalopathy,SAE)是由膿毒癥引起的彌散性腦功能障礙,主要表現為情緒異常、記憶受損和認知障礙等[1]。SAE是膿毒癥患者的常見并發癥,嚴重影響患者預后和生活質量[2]。目前臨床上仍缺乏治療SAE的有效手段,其根本原因在于SAE的發生機制尚未闡明。近期研究發現,小膠質細胞作為中樞神經系統內的免疫細胞,在膿毒癥條件下發生活化與極化狀態改變,可促進中樞炎癥反應,與SAE關系密切[3]。本文就小膠質細胞與SAE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小膠質細胞概述
小膠質細胞起源于胚胎時期的卵黃囊髓系祖細胞,在血腦屏障形成之前遷移進入大腦[4]。它與外周巨噬細胞同屬造血細胞起源的單核巨噬細胞,也是中樞神經系統內唯一的免疫細胞。小膠質細胞占大腦細胞總數的5%~12%,雖數量較少,但在腦內各部位均有分布[5]。在整個成年期,小膠質細胞可保持增殖能力,但與大多數造血譜系細胞不同,其更新速度非常緩慢,一些小膠質細胞的存活壽命甚至長達20年[6]。小膠質細胞形態具有高度可塑性,并與其生物學功能密切相關。在中樞神經系統處于穩定狀態時,小膠質細胞胞體較細小,并伸出纖細的分枝狀結構。既往認為,這是小膠質細胞的“靜止”狀態,但近期研究發現,此狀態下的小膠質細胞以動態方式不斷地向周圍伸展和收縮,以此方式不斷“掃描”周圍微環境,從而對中樞神經系統進行“監控”[7]。當中樞神經系統發生出血、感染或創傷等病理改變時,小膠質細胞迅速活化,胞體增大,呈阿米巴樣,突起變短甚至消失,并具備遷徙和吞噬能力[8]。
活化的小膠質細胞依據抗原標志物和功能分為兩種表型:M1表型和M2表型。M1表型是小膠質細胞的經典激活途徑,主要表達CD16、CD32和CD86等表面抗原,分泌白細胞介素-1(interleukin,IL-1)、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促炎因子,介導炎癥反應,并產生細胞毒性作用。M2表型是小膠質細胞的替代激活途徑,主要表達幾丁質酶3樣蛋白3(chitinase 3 like protein 3,Chi3l3)、精氨酸酶1(arginase-1,Arg-1)和CD206等表面抗原,分泌IL-10、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1,IGF-1)和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等抗炎因子,抑制中樞炎癥反應的過度發生[9]。M2表型小膠質細胞還能分泌神經營養因子,對神經元發揮保護作用[10]。M2表型小膠質細胞又可進一步細分為M2a、M2b和M2c表型,M2a表型主要參與組織修復與再生,M2b表型通過表達抗炎因子參與免疫調節,M2c表型能夠吞噬并清理腦內細胞碎片[11]。
2 小膠質細胞活化與SAE
2.1 基礎研究 多個基礎研究表明,膿毒癥可引起腦組織小膠質細胞活化,進而導致中樞炎癥反應和SAE的發生。Szollosi等[12]將125I標記的小膠質細胞特異性轉運蛋白配體注射入小鼠體內,應用單光束發射計算機斷層影像技術(single photonemissioncomputed tomography,SPECT)研究膿毒癥對中樞小膠質細胞代謝的影響,發現誘發膿毒癥5 h后,大腦區域125I攝取量顯著提高,表明膿毒癥可引起小膠質細胞代謝增強,從而間接證明其發生了活化。Xiong等[13]研究發現,膿毒癥小鼠海馬組織中TNF-α和IL-6等炎癥因子水平升高,小膠質細胞活化標志物離子鈣接頭蛋白分子-1(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or molecule-1,Iba-1)表達增強,Morris水迷宮實驗發現膿毒癥小鼠逃避潛伏期延長,靶象限穿越次數減少,由此推斷膿毒癥小鼠海馬區發生了小膠質細胞活化和炎癥反應,并伴有學習和記憶能力受損。為進一步證實SAE與小膠質細胞的關系,Tang等[14]將膿毒癥小鼠按是否發生認知功能障礙分為“認知障礙易感組”和“認知障礙非易感組”,發現“易感組”小鼠前額皮質和海馬區炎癥因子和小膠質細胞活化水平顯著高于“非易感”組。對各組小鼠應用小膠質細胞活化抑制劑米諾環素后,“非易感組”認知功能變化不明顯;而“易感組”的認知功能出現恢復,并與“非易感組”接近,由此證實了小膠質細胞活化與SAE之間的聯系。Ye等[15-16]研究也發現,抑制小膠質細胞活化和中樞炎癥反應,可以部分逆轉SAE所致的認知功能損害。
2.2 臨床研究 與基礎研究結果相類似,多個臨床研究也證實了小膠質細胞活化的存在。Warford等[17]提取膿毒癥尸檢患者右側額葉白質,使用免疫組化染色法觀察小膠質細胞活化標志物CD68和CD45的染色情況,并使用實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 應(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qPCR)和酶聯免疫吸附測定(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對TNF-α、IL-1β和IL-6等炎癥因子進行檢測,發現膿毒癥患者的白質區域小膠質細胞活化數量增加,炎癥因子的表達和分泌增多。Densteadt等[18]研究表明,膿毒癥患者的大腦灰質亦發生了小膠質細胞活化。最近的一項研究中,Zrzavy等[19]提取了膿毒癥患者完整的灰質-白質切片并進行免疫組化染色,發現小膠質細胞的活化程度在不同區域存在差異,且位于白質的活化小膠質細胞數量多于灰質;同時發現,在膿毒癥急性期,小膠質細胞M1表型標志物表達顯著升高,M2表型標志物表達變化不明顯,據此判斷膿毒癥急性期小膠質細胞以促進炎癥反應的M1表型為主。此外,Westhoff等[20]也研究了小膠質細胞在膿毒癥患者大腦不同區域的活化程度差異,發現膿毒癥組活化小膠質細胞數量高于對照組1.5倍(海馬區)、2.2倍(殼核)和2.5倍(小腦)。上述研究結果證實,膿毒癥患者大腦發生了小膠質細胞活化,且在不同區域可能存在差異。
3 小膠質細胞活化對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
3.1 刺激星形膠質細胞活化 星形膠質細胞在中樞神經系統內廣泛分布,對神經元和少突膠質細胞起保護和支持作用。Liddelow等[21]發現,活化小膠質細胞分泌的IL-1α、TNF-α和補體C1q是刺激星形膠質細胞活化的重要介質,活化的星形膠質細胞發生形態改變,喪失對神經元和少突膠質細胞的保護和支持作用,并最終導致兩者的死亡。Rothhammer等[22]研究發現,小膠質細胞分泌的轉化生長因子-α(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α,TGF-α)和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B(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B,VEGF-B)能夠作用于相應受體,使星形膠質細胞活化并介導中樞炎癥反應的發生。
3.2 抑制突觸可塑性 突觸可塑性是指突觸連接強度可調節的特性,是學習記憶活動的細胞表現形式。若突觸可塑性被抑制,學習記憶功能將受到影響。Yang等[23]觀察成年大鼠小膠質細胞活化對突觸可塑性的影響發現,活化小膠質細胞介導的中樞炎癥反應可導致海馬區神經元內突觸素、突觸后致密蛋白95(post synaptic density protein 95,PSD95)、谷氨酸受體2(glutamate receptor 2,GluR2)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2(N-methyl D-aspartate receptor 2,NMDAR2)表達降低,電生理檢查發現長時程增強(long-term potentiation,LTP)受到抑制,水迷宮實驗也證實了學習記憶功能受損,從而證實小膠質細胞活化可對突觸可塑性產生干擾作用。此外,新生大鼠小膠質細胞活化也對突觸發育和可塑性造成影響。Lin等[24]將脂多糖注射入新生大鼠,發現小膠質細胞活化和中樞炎癥反應可導致海馬區突觸素、突觸體相關蛋白(synaptosomal associated protein,SNAP)表達降低,神經元樹突棘密度和突觸內囊泡數量減少,由此推測新生大鼠小膠質細胞活化可造成突觸發育障礙和可塑性降低,并影響后期智力發育。
3.3 損傷髓鞘結構和功能 髓鞘是包裹于神經細胞軸突外的膜性結構,具有絕緣和提高神經沖動傳導速度的作用,是神經沖動正常傳導的重要保障。Aryanpour等[25]研究發現,小膠質細胞活化介導的神經炎癥反應可導致小鼠胼胝體區髓鞘結構和功能改變,髓鞘堿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MBP)和勒克司堅牢藍(Luxol Fast Blue,LFB)染色顯示胼胝體區髓鞘完整性破壞和神經脫髓鞘病變,透射電鏡觀察發現髓鞘排列紊亂、大量崩解并伴有軸突水腫的發生,同時小鼠學習記憶能力也相應降低;在抑制小膠質細胞炎癥反應后,上述病理和功能改變得到恢復,由此推測小膠質細胞活化可對神經髓鞘結構和功能造成損傷。此觀點隨后得到Liu等[26]的進一步證實,他們用脂多糖刺激體外培養小膠質細胞發生活化,并采集條件培養基孵育少突膠質細胞,發現后者凋亡顯著增加,而由于少突膠質細胞是構成髓鞘的主要成分,該實驗在細胞水平驗證了小膠質細胞活化對髓鞘的影響。
3.4 影響下丘腦功能 下丘腦含有大量的神經內分泌細胞,它們通過分泌神經激素,對正常生理功能和內環境穩態發揮重要調節作用。Da Costa等[27]研究了小膠質細胞活化對下丘腦的影響,發現抗凋亡蛋白B細胞淋巴瘤-2(B-cell lymphoma-2,Bcl-2)和B細胞淋巴瘤-xL(B-cell lymphoma-xL,Bcl-xL)表達減少,內源性凋亡途徑被啟動,神經內分泌細胞的大量凋亡導致精氨酸加壓素分泌減少,認為這可能是膿毒癥患者發生低血壓休克的原因之一。Santos-Junior等[28]研究也發現,膿毒癥大鼠下丘腦小膠質細胞活化的同時,膽堿能神經元胞膜和胞漿內的乙酰膽堿水平降低,據此推測這可能與小膠質細胞介導的下丘腦炎癥反應造成神經內分泌細胞損傷有關。
4 信號通路對小膠質細胞的調節作用
4.1 信號通路對小膠質細胞活化的調節作用 目前認為,小膠質細胞的Toll樣受體4(Toll like receptor 4,TLR4)/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路在介導小膠質細胞活化過程中起重要作用[29-30]。TLR4能夠識別病原微生物產生的蛋白質、核酸和脂類等抗原分子并發生激活,繼而通過細胞內接頭蛋白——髓樣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或β干擾素TIR結構域銜接蛋白(TIR domain containing adaptor inducing interferon β,TRIF),進一步使下游NF-κB發生活性轉化并轉移至細胞核內,增強下游炎癥因子基因的轉錄與表達,促進小膠質細胞活化和炎癥反應的發生[31]。也有研究發現,激動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受體也可經由NF-κB通路調節小膠質細胞活化[32]。此外,混合譜系 蛋 白 激 酶 3(mixed-lineage protein kinase 3,MLK3)/p38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 MAPK)通路也可能對小膠質細胞活化具有調節作用[33]。
4.2 信號通路對小膠質細胞表型的調節作用 目前,調控小膠質細胞表型的信號通路尚未明確。Wang等[34]研究紅景天苷對小膠質細胞的影響時發現,其表型由M1向M2轉換,使用自噬抑制劑或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抑制劑可逆轉其表型轉化,故推測AMPK/自噬通路可能對小膠質細胞表型具有調節作用。Jin等[35]研究也表明,增強自噬可使小膠質細胞表型由M1向M2轉化,且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自噬通路介導了這一過程。由此可見,改變自噬水平可能對小膠質細胞表型具有調節作用。此外,沉默信息調節因子2相關酶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factor 2 related enzyme 1,SIRT-1)或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共激活因子1(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1,PGC-1)通路可能也參與了小膠質細胞表型的調節[36-37]。
5 展望
目前,對小膠質細胞的研究尚不深入,且存在諸多不足與局限:如對小膠質細胞活化與表型狀態的測定多集中于腦組織提取物檢測和病理切片鏡檢,尚缺乏活體條件下的可靠檢測方法;對小膠質細胞的調控,特別是對調控表型的信號通路尚不明確。近期研究表明,小膠質細胞表型改變亦與SAE存在聯系[37-38],以調節小膠質細胞表型作為研究方向可能為治療SAE提供新的思路。此外,糾正小膠質細胞對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也可能為SAE的治療提供目標參考。除了為治療提供方向,小膠質細胞的活化程度與表型狀態亦可能作為預測SAE或判斷其進展程度的評價手段應用于臨床。所以繼續深入研究小膠質細胞活化與SAE的關系,探討小膠質細胞表型改變對SAE的影響,研發小膠質細胞靶向調節藥物并應用于臨床,可能會為SAE的治療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