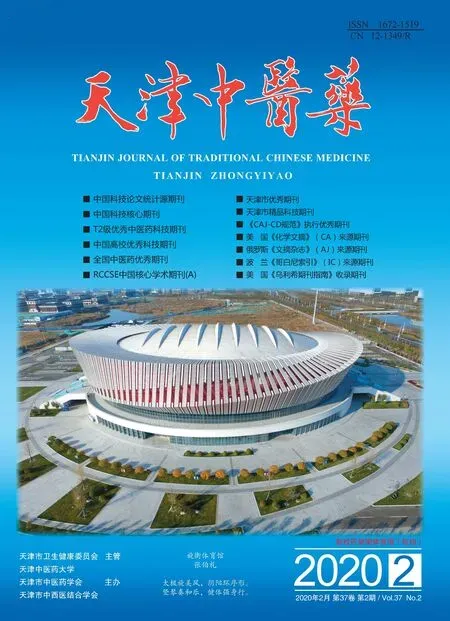嶺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臨床表現的初步分析
戴 敏,肖閣敏,王擁澤,李 林,楊躍武,謝和平,李永偉,王 威,吳英姿,胡宇旋,楊宏志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中醫科,廣州 501630)
自2019年12月起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了許多不明原因的肺炎,隨著疫情進展,中國發現這是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即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收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1 791例(江西省、陜西省、甘肅省各核減1例),重癥病例1 795例,累計死亡病例259例,累計治愈出院病例243例,共有疑似病例17 988例[1]。
在這次疫情發生后,中醫藥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印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先后發布了4個版本,對全國開展中醫藥診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起到了指導作用。根據筆者目前有限的資料分析,本次疫病為“濕毒疫”,關鍵病理因素為“濕”。這一點與王玉光等[2]研究武漢市的病例資料所得結果一致。但嶺南地區氣溫較高,所以濕從熱化的可能較大,本院5例病患中,病情加重者即為濕隨熱化。因目前病例較少,具體病機及演變過程與其他地區的差異尚需進一步觀察總結。
1 臨床資料分析
1.1 一般資料 截至2020年2月1日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共收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5例。其中男3例,女2例。年齡分布分別為:30~39歲2例,40~49歲 1例,50~59歲 1例,60歲以上 1例。
1.2 臨床表現
1.2.1 癥狀表現 主要表現為乏力,肌肉酸痛,干咳,發熱,惡寒或不惡寒,消化道癥狀也比較明顯(包括納差、惡心、嘔吐/腹瀉),或發病早期或發病過程中,口干或口苦。這些癥狀與武漢發病患者表現基本一致。
1.2.2 舌象方面 5例患者中采集到4份舌象,均有不同程度的舌苔厚膩,黃或微黃膩2例,白膩2例;舌質中,舌尖紅1例,其余為淡紅。
2 患者詳細四診資料
2.1 病例1 患者女性,46歲。因“發熱7日”于2020年1月24日入院。
患者于入院7 d前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8.3℃,無伴畏寒、寒戰,無咽痛、咳嗽,無肌肉酸痛等不適,至湖北省天門市診所就診,診斷不詳,予“頭孢”抗感染2 d后,熱退,后未監測體溫,1 d前,患者出現咽痛、咳嗽,咯少許白痰,測體溫37.3℃,并有胸悶不適,入院3 h前到本院發熱門診就診,查血常規、肝腎功能等無明顯異常,胸部CT可見雙側中下肺散在小斑片灶,不除外病毒性肺炎可能,予以收入院治療。入院后查雙肺呼吸音稍粗,未聞及干濕啰音;予以奧司他韋、阿比多爾、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療。1月25日初篩新型冠狀病毒陽性,加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片(克力芝)治療。1月27日確診。
流行病學史:患者為湖北省天門市人,在廣州居住,13 d前至武漢市旅游2 d后返回天門市,1月23日乘高鐵到廣州。與患者同游武漢的朋友5 d前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否認野生動物接觸史或野生動物檔口暴露史,否認禽類市場暴露史。
1月26日中醫會診,癥見患者已無發熱,25日曾有惡心,嘔吐少量水樣物,無發熱惡寒,無汗出,口干、口苦,納尚可,二便正常。舌象:舌暗紅,苔白膩中厚。診斷:濕瘟,少陽濕熱,太陽肺熱。治法:和解少陽,化濕透熱。處方:柴胡9 g,黃芩9 g,法半夏9 g,太子參 10 g,甘草 9 g,草豆蔻 6 g,厚樸 6 g,茯苓 15 g,藿香 10 g,陳皮 9 g,皂角刺 10 g,桃仁 9 g,葶藶子15 g,麻黃9 g,苦杏仁9 g,石膏20 g,天花粉15 g,共3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
后患者病情逐漸好轉,1月27日夜間至28日上午患者嘔吐胃內容物3次,嘔吐后無明顯不適。查舌暗紅苔薄白膩。后停用中藥(已服藥2 d)。1月29、30日間隔24 h連續2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
2.2 病例2 患者男性,37歲。因“發熱伴咳嗽4日”于2020年1月22日入院。
患者入院4 d前開始出現發熱,體溫37.8℃,伴有乏力、咽干、咳嗽,無痰,無鼻塞、流涕,無惡寒、寒戰,無腹痛、腹瀉,無關節肌肉痛,無心悸、胸悶,無氣促,1 d前體溫升至38.3℃,乏力加重,伴全身酸痛,至社區醫療中心就診,查血常規無異常(未見化驗單),予以奧司他韋及退熱藥治療,體溫可降至37℃,全身酸痛減輕。入院后查CT示雙肺散在小斑片狀影。血常規示淋巴細胞偏低。入院后查體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干濕啰音。予以莫西沙星(拜復樂)、替考拉寧及奧司他韋、阿比多爾抗感染治療,丙種球蛋白支持治療,干擾素α-2b霧化。并于1月25日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期間患者仍低熱37.5℃左右。
流行病學史:患者有一般接觸史:患者同事于1月2日由武漢返回廣州,該接觸者無明顯發熱癥狀。患者妻子于1月22日出現咳嗽癥狀。
1月26日中醫會診,癥見低熱,周身乏力,胸悶,吸氣時陣咳,夜間劇,無惡寒,無汗,納差不欲食,口干,稍口苦,無腹痛腹瀉,無頭痛、咽痛、咽癢,有咽干,眠差難以入睡。小便可,泡沫多,大便1次/日,便質正常,已無肌肉酸痛。自訴發病初期有惡寒發熱,平素畏寒畏風,易感冒。舌象:舌淡、舌尖紅,苔薄白膩。診斷:濕瘟,太陽肺熱,胃腸濕熱。治法:透熱宣肺,化濕止瀉。處方:柴胡9 g,黃芩9 g,法半夏9 g,太子參 15 g,甘草 9 g,桔梗 9 g,干姜 6 g,枳殼 9 g,麻黃 9 g,葶藶子 15 g,苦杏仁 10 g,石膏 20 g,大棗10 g,天花粉 15 g,皂角刺 10 g,梔子 10 g,淡豆豉15 g,薏苡仁 24 g,金銀花 15 g,連翹 10 g,共3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
1月27日隨訪,患者服藥后腹瀉2~3次/日,發熱惡寒,體溫持續39.0℃左右,咳嗽加重,胸悶,無氣促呼吸困難。患者遂停用中藥。自行服用連花清瘟膠囊后覺胸悶緩解。
2月1日復診,患者已無發熱、咳嗽等不適癥狀。查舌暗紅,苔薄白膩。
2.3 病例3 患者女性,56歲,以“間斷咳嗽2日”于2020年1月25日入院。
患者入院2 d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咳嗽,每日2~3次,干咳,無咳痰,無發熱、頭痛、頭暈,無胸悶、氣促,無呼吸困難等不適,入院當天在本院門診就診,胸部CT示雙肺炎癥,不除外病毒性肺炎可能。入院后1月26日發熱,體溫38℃,無畏寒、寒戰,血常規提示白細胞總數3.37×109/L,單核細胞比10.1%,C反應蛋白(CRP)7.1 mg/L。予以奧司他韋、阿比樂爾、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左氧氟沙星等抗感染治療。
流行病學史:患者長期定居武漢,1月19日到廣州探親,家人均暫無發熱、咳嗽等不適。否認野生動物接觸史或野生動物檔口暴露史,否認禽類市場暴露史。
1月26日中醫會診,癥見低熱,無惡寒,無汗出,口干,無口苦,納可,腹脹,大便爛臭,1次/日,余無不適。舌象:舌尖紅,苔微黃膩。診斷:濕瘟,太陽肺熱,腸熱氣滯。治法:透熱宣肺化濕。處方:麻黃9 g,苦杏仁 9 g,石膏 20 g,甘草 9 g,柴胡 9 g,黃芩 9 g,法半夏 8 g,太子參 9 g,大棗 9 g,葛根 15 g,黃連5 g,桔梗 9 g,金銀花 20 g,連翹 20 g,梔子 15 g,淡豆豉 15 g,知母 10 g,天花粉 15 g,皂角刺 9 g,藿香9 g,石菖蒲9 g,枳殼15 g,草豆蔻6 g,共3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
后患者仍有發熱,于1月28—29日出現高熱,最高39.1℃,伴畏寒。腹瀉,但連續2次核酸檢測陰性,停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加用鹽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沐舒坦)。1月30日患者體溫38.1℃,復查床邊胸片考慮雙肺肺炎,不除外病毒性肺炎。血常規示白細胞總數4.64×109/L,淋巴細胞絕對值0.74×109/L。血氣分析:氧分壓 71.1 mmHg(1 mmHg≈0.133 kPa,下同),二氧化碳分壓 47.8 mmHg,氧合指數339。CRP 91.4 mg/L。繼續目前治療,未繼續服用中藥。
2月1日復診,患者無發熱,咯白痰,輕微胸悶,納眠可,無口干、口苦,大便干,小便正常。
2.4 病例4 患者男性,64歲。因“發熱伴肌肉酸痛1日”于2020年1月22日入院。
患者入院1 d前開始出現發熱,無伴畏寒、寒戰,測體溫38.3℃,伴有雙下肢肌肉關節酸痛,無咽痛、咳嗽、咳痰,無腹痛、腹瀉,無胸悶、心悸,自服板藍根沖劑,癥狀無改善。體溫進行性升高,1月22日到本院急診就診,查血常規未見明顯異常,肝腎功能無異常,CRP 43.2 mg/L,胸部CT提示“右肺上葉、右肺中葉可見散在小斑片灶,考慮為肺炎,不除外病毒性肺炎可能”。收入院后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啰音。予以阿比多爾、莫西沙星、奧司他韋、替考拉寧等治療。1月25日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無發熱,加用干擾素α-2b霧化,同時患者胸部CT示肺部炎癥較前進展,加用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甲強龍)40 mg,每日1次。
流行病學史:患者為武漢人,一直在武漢居住,曾到附近菜市場購買豬肉等,入院2 d前從武漢乘高鐵來廣州與家人團年,發病前14 d內未接觸發熱患者。1月21日上午乘地鐵5號線轉1號線,當天中午飯前及飯后均有發熱。否認野生動物接觸史或野生動物檔口暴露史,否認禽類市場暴露史。
1月26日中醫會診,癥見患者刻下無發熱,無惡寒或寒戰,無肌肉關節酸痛,無汗,納可,無口干口苦,無腹痛腹脹等,眠可,二便正常。舌象:舌暗紅,苔厚白膩。診斷:濕瘟,太陽肺熱夾濕。治法:清熱宣肺化濕。處方:麻黃6 g,苦杏仁9 g,石膏20 g,甘草 9 g,蜈蚣 6 g,葶藶子 15 g,葛根 15 g,黃芩 9 g,黃連 6 g,藿香 9 g,金銀花 20 g,大棗 9 g,石菖蒲9 g,蘆根 20 g,皂角刺 10 g,天花粉 15 g,連翹 20 g,共3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
后患者仍有低至中度熱,1月27日夜間出現畏寒,監測體溫正常,后未再出現畏寒。根據病原學調整治療方案為停用莫西沙星、阿比多爾,繼續予以干擾素α-2b霧化,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甲強龍)40 mg,每日1次,以及維持替考拉寧,加用丙種球蛋白。1月28日患者再次發熱至38℃,1月29日體溫最高39.3℃,伴有頭暈,予以高流量吸氧后指脈氧可升至96%。低流量吸氧指脈氧93%以下,符合重型病例診斷標準,加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停用激素及丙種球蛋白。復查血常規白細胞及降鈣素原較前有所升高,不排除合并細菌感染,抗生素調整為頭孢哌酮舒巴坦。
1月29日中醫會診,癥見患者仍發熱,困倦乏力,身酸痛,干咳,昨日水樣便8次,今日1次,伴明顯氣促。
1月31日中醫會診,癥見患者仍有發熱,熱峰較前升高,今晨體溫39.8℃,無伴畏寒,咳嗽,咯少許白痰,無胸悶、氣促,無腹痛、腹瀉,無心悸、胸痛等。由于患者已告病重,年高未能視頻舌診。
2月1日復診,患者已轉入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
2.5 病例5 患者男性,34歲,因“發熱、肌肉酸痛2日”于2020年1月26日入院。
患者于1月24日夜間開始出現發熱,體溫達38.5℃,伴畏寒、胸悶、全身肌肉酸痛,肌肉疼痛以腰部為甚,有咽干,無寒戰,無咽痛、鼻塞,無咳嗽、咳痰,無呼吸困難,無腹痛、腹瀉,當時未就醫,自行服用“退熱藥”后出汗并熱退。次日又發熱,體溫達38℃,肌肉酸痛及胸悶加重,上兩層樓即氣促,無咳痰,胃納差,又自行服用“退熱藥”。1月26日晨起體溫再次升至38.5℃,肌肉酸痛及胸悶同前,自覺有輕微頭暈,無頭痛,為明確病情至本院發熱門診就醫,急查血常規、CRP、咽拭子流感抗原正常,胸部CT提示雙肺肺炎。入院后查體體型肥胖,雙肺呼吸音低。既往有肥胖癥、脂肪肝、高脂血癥、睡眠呼吸暫停等基礎疾病。予以阿比多爾、莫西沙星治療。
流行病學史:患者最近2周先后到上海、武漢逗留,其中2020年1月18—20日在武漢武昌區居住,曾開車到漢陽區某超市購物1次,否認到華南海鮮市場或其他肉菜市場逗留,2020年1月23日開車回廣州。武漢到廣州的旅途中妻子、兒女同行,其中妻子同一天出現發熱,兒女至今無發熱。
1月26日中醫會診,癥見刻下患者發熱38℃,伴惡寒,無汗,動則氣促,頭暈,口干不苦,納尚可,腹瀉3~5次/日,大便較臭,小便黃。查舌淡紅,苔黃厚膩,舌尖花剝,有裂紋。診斷:濕瘟,太陽肺熱夾濕—熱重于濕,熱已傷津。治法:清熱宣肺化濕兼養陰。處方:麻黃6 g,苦杏仁9 g,石膏20 g,甘草9 g,桔梗 9 g,金銀花 20 g,連翹 20 g,蘆根 20 g,牛蒡子9 g,淡竹葉 9 g,魚腥草 20 g,柴胡 9 g,法半夏 9 g,大棗 9 g,太子參 15 g,知母 10 g,天花粉 15 g,藿香9 g,石菖蒲 9 g,草豆蔻 6 g,共 3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
后患者仍發熱,最高39.4℃,發熱時伴頭暈不適,伴咳嗽,持續胸悶同前,無腹痛腹瀉。1月29日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臨床分型為普通型。由于患者有高脂血癥等基礎病,有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克力芝)治療禁忌癥。1月29日中醫會診,癥見患者仍有高熱,無明顯畏寒、寒戰,最高體溫39℃,伴有干咳,氣短,無心悸,自覺精神較前改善,無腹痛、腹瀉,小便正常。查舌略紅,苔白厚膩,舌尖花剝較前減少,有裂紋。1月30日患者仍反復高熱,最高39.5℃,無伴明顯畏寒寒戰,仍有干咳、氣短,納差,無惡心嘔吐,無胸痛,精神、睡眠欠佳,1月29日床邊胸片示雙肺炎癥。1月30日加用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甲強龍)80 mg,每日1次,靜脈滴注,加用干擾素α-2b霧化治療,繼續予以莫西沙星、阿比多爾、丙種球蛋白等治療。期間患者未規律服用中藥。
3 病因病機
綜合患者自起病以來的臨床表現及發展變化,初步總結如下:患者出現乏力、肌肉酸痛和胃腸道表現多提示本病病位在脾、胃、大腸,即消化道;咳嗽、氣促等提示病位在肺,即呼吸道,屬表里同病。本病多屬實證,或寒或熱。根據舌象,舌膩提示濕;黃膩提示濕熱,白膩提示寒濕;口干,大便臭提示濕熱;病情變化較快,容易重癥化符合疫毒的特點;舌暗紅提示瘀;因此涉及的病理因素為:濕,熱/寒,毒,瘀。
3.1 病因病機分析 元代朱丹溪說:“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皆相似者,名曰瘟疫病也。”2019年入冬以來,華南地區氣溫一直居高不下,非其時而出現其氣,結合病理因素可定為“濕瘟”,考慮其傳染性較強,也可定為“濕毒疫”。無論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辦公廳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制定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治療方案(試行第四版)[3],還是王玉光等[2]的研究結果,均明確指向“濕”邪,這一點在本院的病例中也可以明確驗證。感受外風夾雜“濕毒疫”,受本難知,因發知受,從陽則化熱,從陰則化寒。因為天氣變化,或人體體質傾向,或失治誤治,而從天化,從人化。故,可見有風濕熱者,有風寒濕者。根據筆者的觀察由于嶺南地區氣溫較高,所以濕從熱化的可能較大,本院5例病患中,病情加重者即為濕隨熱化。濕性重濁黏滯,因此從目前的流行病學分析看,本病潛伏期相對較長,病程長,治愈較慢;臨床表現則為肢體酸痛,沉重,乏力等。濕性趨下,所以患者有的表現為下肢酸痛乏力,或者出現腹瀉。毒則指疫毒,提示其傳染性和對人體的危害性,目前很多資料[4]均已表明,其傳染性較強,但毒性弱于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SARS)。至于瘀的表現主要為舌暗紅,無論是寒濕或濕熱,均可阻礙氣機,影響氣機的運行,導致血瘀。當然后期肯定有“虛”的一面,只是本次病例觀察的時間較短,暫時沒有發現。
3.2 病機轉變預測 五運六氣提示2019年氣溫高,庚子年屬于秋金風寒甚,節后開始降溫下雨潮濕,風寒濕重,嶺南地處南方濕熱,多氣雜至,疫毒人傳人,風重而善行數變,太陽少陽病風寒濕速變肺熱實變而易成膿毒。加之春節期間飲食油膩,居家隔離,缺少運動,陽郁濕阻,病機變化將更加復雜。重癥可能出現濕瘟之太陽病肺熱實變膿毒證合少陽陽明氣分病。
4 小結
5例患者中有1例病情危重,也是此次入院患者中年齡最大的1位,預后不佳,其病機特點是初起舌暗紅,苔白厚膩,熱重于濕,一度臨床好轉,數天后脾胃肺腸濕熱加重呈高熱持續不退,并下利多次,病情加重預后不佳。而其余4例病情相對較輕,其病機特點是風濕熱并重,未表現為風寒濕。5例患者初期均未表現風寒征象。高齡患者是危重患者這一點與其他地區表現一致,高齡人群風險最高。根據5例患者表現,濕邪貫穿始終,因此,治療過程中一定注意不可過用寒涼或糖皮質激素類引起外邪內陷,使病情加重或病勢遷延慢性化。
由于此次疫情在廣東散發,本院收治患者病例數少,觀察時間短,且為避免感染未能脈診,缺少脈診資料,筆者的分析只是初步判斷,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總結。將這5例患者資料列出,也是拋磚引玉,希望中醫界同仁共同努力,打好這個攻堅戰,充分發揮中醫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