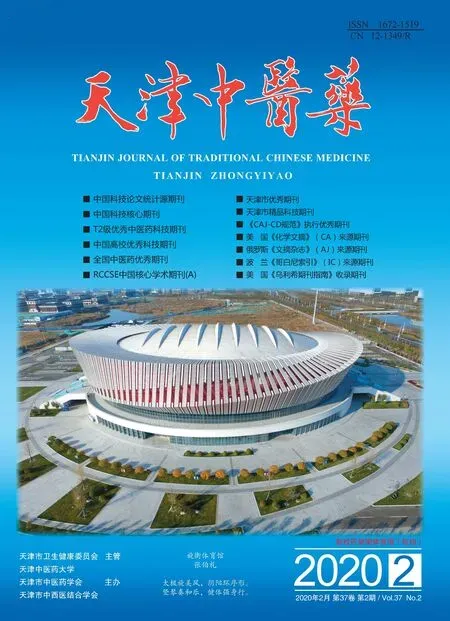胃癌前病變信號通路及相關中醫藥治療的研究進展*
張曼玲,時昭紅,劉 云,趙文櫻子
(1.湖北中醫藥大學,武漢 430065;2.湖北中醫藥大學附屬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武漢 430022)
流行病學研究顯示,中國腫瘤的發病率及病死率排名中,胃癌均列前3位[1]。胃癌是多因素導致的多階段疾病,遺傳、幽門螺桿菌(Hp)感染、不良的飲食、生活習慣[2]等因素均參與胃癌前病變(PLGC)的發病。Correa[3]首先提出,胃癌的形成過程為:慢性胃炎→胃黏膜萎縮→胃黏膜腸上皮化生(GIM)→上皮內瘤變→胃癌,這一觀念得到廣泛認可并沿用至今。其中慢性萎縮性胃炎(CAG)、GIM、上皮內瘤變/異型增生(Dys),即PLGC,是炎瘤轉換過程的關鍵階段。
PLGC的西醫治療,以定期隨訪、改善飲食結構為主,配合根除Hp、非甾體類藥物(NSAID)、補充微量元素、葉酸[4]等,但其確切療效尚不確定。中醫認為,PLGC多虛實夾雜,臨床以肝胃郁滯、濕熱內蘊、胃絡瘀阻、胃陰不足、脾胃虛弱證多見,普遍認為脾虛與血瘀是本病的關鍵病機環節,臨床需將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在辨證準確的基礎上,結合內鏡及病理診斷酌情加減。PLGC病程較長,常守方治療并隨訪,故中成藥在此病的運用也十分廣泛,如胃復春片、摩羅丹、左金丸、欣胃顆粒等,治療此病均有一定療效[5]。中醫“既病防變”的理論,與西醫試圖延緩其發展為胃癌的治則相契合,加之個性化方案和整體治療,在PLGC的治療中獨具優勢。臨床與基礎研究均證實,中醫藥治療PLGC的療效確切,且具有多靶點作用。筆者列舉了PLGC發病常見的信號通路,并綜述了基于這些信號通路的中醫藥治療研究進展,以期為臨床用藥提供參考。
1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通路
EGFR為跨膜受體酪氨酸激酶家族,在正常機體胃黏膜的上皮細胞、固有膜細胞及黏膜肌細胞均表達,以胃黏膜上皮細胞的表達最強。表皮生長因子(EGF)及其相關肽轉化生長因子(TGF-α)是EGFR最主要的配體,一旦配體與EGFR結合,在酪氨酸激酶區磷酸化活化,即啟動一系列級聯反應,如增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存活素、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信號通路等的表達,導致受體本身及細胞內酪氨酸殘基的磷酸化,促進細胞的增殖、分化[6]。EGFR參與胃黏膜修復,調節黏膜細胞生長發育,修復受損的黏膜,參與胃腸上皮細胞分化增殖和成熟,而EGFR的過表達會導致細胞過分化,正常的上皮細胞發生異型增生并進一步發展[7]。EGF和TGF-α及其共同受體EGFR參與了胃上皮細胞增殖分化的調控,與 CAG[8-9]、GIM[10]、Dys[11]的發病密切相關。
中醫藥治療可能通過干預EGFR通路發揮治療PLGC的作用。符嬌文等[12]通過動物實驗[單功能烷化劑甲基硝基亞硝基胍(MNNG)結合情志刺激、饑飽失常法造模]發現,半夏瀉心湯可通過介導EGFR、B 淋巴細胞瘤-2(Bcl-2)蛋白表達,誘導“病態”細胞凋亡,重新恢復細胞增殖和凋亡之間的平衡,從而逆轉PLGC;魏玥等[13]通過喂養CAG伴Dys模型大鼠(MNNG+氨水溶液+雷尼替丁顆粒)發現,益氣化瘀解毒法可抑制EGFR的高表達及EGFR/MAPK細胞信號傳導通路的異常激活,這可能是其逆轉PLGC、防治胃癌的有效作用機制之一;周杰[14]通過實驗發現,黃芪多糖能通過降低EGFR、環氧合酶-2(COX-2)等的表達,改善CAG大鼠(MNNG+饑飽失常造CAG模型)胃黏膜病變、抑制胃癌細胞增殖;顏莉等[15]通過臨床觀察發現,摩羅丹可以顯著減低CAG患者EGF和EGFR的表達,且臨床療效顯著;另外,在外治方面,TODISCO等[16]發現艾灸療法能通過抑制EGFR/ERK等蛋白表達,抑制細胞凋亡,減少胃黏膜異生。
2 JAK/STAT信號通路
JAK/STAT信號通路,即Janus激酶-信號轉導子與轉錄激活子通路。JAKs是細胞質內非受體可溶性蛋白酪氨酸激酶,已發現JAK1/2/3及TYK2廣泛存在,JAK3僅存在于骨髓和淋巴系統中。STATs屬于胞質蛋白、信號轉導子和轉錄激活子、核轉錄因子,已發現STAT1/2/3/4/5a/5b/6幾種亞型,其中STAT3在人類腫瘤中最常見。JAK是STAT3最重要的上游蛋白,各種細胞外信號刺激后,JAK以磷酸化的方式活化酪氨酸殘基,形成STAT停泊位點,STAT與受體結合后,JAK使STAT磷酸化激活形成二聚體,并進入細胞核內,與靶基因的啟動子相結合,調節下游基因的轉錄活性。在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此通路持續活化,調節下游靶基因的表達,如Bcl-xL、Bcl-2、Fas、Cyclin D1、Mcl-1、Survivin、c-Myc等,促進腫瘤細胞增殖,抑制細胞凋亡,參與腫瘤免疫逃逸,抑制免疫功能,導致腫瘤的發病、擴張。ISHII等[17]發現大鼠胃黏膜中STAT3信號的缺失導致Hp感染時上皮細胞增殖、萎縮和化生減少。目前研究認為,JAK/STAT信號通路通過在腫瘤細胞增殖、免疫抑制、炎癥、干細胞和轉移前生態位中發揮作用[18],參與胃黏膜上皮內瘤變[19]發病。
謝晶日等[20]實驗發現,欣胃顆粒對PLGC大鼠(采用MNNG為主的復合因素造模)胃黏膜組織病理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可以下調STAT3、p-STAT3的表達以達到對抗PLGC作用;李慧臻等[21]通過動物實驗發現:半夏瀉心湯通過抑制PLGC大鼠(改良MNNG+復合法造模)胃黏膜組織STAT3信號通路,促進抑癌因子的表達,從而抑制PLGC的發生發展;王坤等[22]實驗發現,穴位埋線療法可能通過提高CAG大鼠(MNNG+饑飽失常法)胃黏膜組織SOCS 3的表達,抑制JAK2-STAT3的異常激活,從而降低靶因子Cyclin D1、Bcl-2的表達水平,改善大鼠CAG情況;韋維等[23]發現,安胃湯可能通過調節CAG大鼠(MNNG)JAK1/STAT3信號通路關鍵因子 JAK1、STAT3、c-myc、SOCS-3的表達,緩解炎癥并防治CAG;藺煥萍等[24]實驗得出:自制中藥合劑參佛胃康可能通過下調PLGC大鼠(MNNG造模)胃黏膜組織中VEGF、STAT3和HIF-1α的表達,逆轉大鼠胃黏膜組織病變;王坤等[25]發現穴位埋線法(脾俞、中脘、足三里)可改善CAG大鼠(MNNG+不規則飲食)胃黏膜的病理改變,可能與其上調胃SOCS 3蛋白表達、抑制JAK2/STAT3信號通路的激活有關。
3 PI3K/Akt/mTOR通路
蛋白激酶Akt的活化包括PI3K依賴和PI3K不依賴2種,PI3K依賴的活化通常要依賴PI3K上游的各種細胞因子、生長因子的活化、物理刺激等,再磷酸化激活PI3K/Akt。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是PI3K/Akt通路下游的信號分子,促進細胞生長和增殖。mTOR由mTOR、GβL、mTOR調節相關蛋白、mLST組成,能磷酸化活化下游的信號分子,如mTOR信號基序蛋白(TOS)、蛋白激酶P70S6K1、Sox2、EIF4E結合蛋白1等。Akt和mTOR通路之間可經反饋和負反饋調節彼此連接,這種機制制約了他們過度激活,可遏制不受控制的細胞增殖。而腫瘤微環境下的PI3K基因常廣泛突變,突變的PI3K易活化,高度活化的PI3K/Akt/mTOR通路可與蛋白激酶 MAPK、核轉錄因子-κB(NF-κB)、磷脂酶 PLCγ、轉錄因子AP-1、促凋亡因子p53構成細胞信號通路網絡,進一步促進細胞增殖,抑制細胞凋亡。消化系統惡性腫瘤等常存在PI3K/Akt/mTOR信號通路的持續異常激活,胃黏膜損傷,BADARY等[26]觀察臨床患者胃黏膜病理情況,發現mTOR的表達與CAG、GIM和Dys相關,推測PI3K/Akt/mTOR通路的活化參與PLGC的發病。
劉嘉誠等[27]發現半夏瀉心湯能通過影響PLGC大鼠(改良MNNG+復合法)胃黏膜組織微環境中的PI3K/Akt/mTOR信號通路中的啟動子、調控器及效應子,阻斷PLGC的發生發展;王鮮嬋等[28]通過動物實驗得出結論:消痰散結方能通過下調PI3K/Akt/mTOR信號通路的相關蛋白PTEN的表達,抑制該通路的活性,從而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劉寧寧等[29]通過細胞實驗(H.pylori感染的MKN45細胞)發現,健脾解毒方可抑制H.pylori誘導的HUVEC血管新生及細胞VEGF的表達,調控PTEN/PI3K/AKT信號通路,可能是其防治胃癌的重要作用靶點。許文彬等[30]發現,清熱化濕方可能通過調控PI3K/AKT信號,下調beclin-1及CDK1表達,誘導細胞自噬而發揮防治胃癌的效用;王晨光等[31]發現針灸急性胃黏膜損傷大鼠胃經穴位可升高胃黏膜細胞PI3K/Akt信號通路中PI3K、PKB、PAK表達,促進胃黏膜損傷修復,抑制其發展為PLGC。
4 NF-κB/Bcl-2通路
細胞凋亡和細胞增殖失衡在PLGC發生中有重要意義,NF-κB/Bcl-2通路常參與抑制細胞凋亡的過程。正常情況下,NF-κB存在于胞漿內,與IκB結合處于失活狀態,細菌、病毒等刺激后,NF-κB與IκB分離,進入細胞核內與特異性位點結合而發揮作用,而Bcl-2啟動子上具有可與NF-κB發生特異性結合的位點,NF-κB與之結合后,通過轉錄途徑促使Bcl-2表達上調,TNF-α也參與其中,此時NF-κB和Bcl-2的表達均上調,共同抑制細胞凋亡,介導胃癌的發生發展。
肖高春[32]通過臨床試驗,發現健脾和胃方能夠通過下調NF-κB/Bcl-2通路指標,有效促進細胞凋亡,一定程度上預防胃癌發生;朱昱翎等[33]發現,健脾通絡解毒方可通過抑制NF-κB/Bcl-2通路促進細胞凋亡,治療CAG伴腸上皮化生(IM)或伴有Dys,阻斷PLGC發展為胃癌的進程;潘俊娣等[34]認為胃蘇顆粒可改善CAG患者胃黏膜病變,其作用機制可能與上調胃黏膜TFF2、下調胃黏膜NF-κB的表達有關;1項臨床隨機對照試驗[35]發現,相比西藥常規治療,中藥辨證論治可改善PLGC患者的臨床癥狀,同時有效降低Bcl-2、Ki-67異常表達,即證實中藥辨證可通過抑制NF-κB/Bcl-2通路達到治療PLGC的目的。
5 Shh信號通路
Hedgehog(Hh)基因是由 Nüsslein-Volhard、Wieschaus首先在果蠅體內發現[36]。目前,已知哺乳動物體內表達3種同源基因,分別為Sonic Hedgehog(Shh)、Desert Hedgehog(Dhh)和 Indian Hedgehog(Ihh),Shh信號通路包括:分泌型信號糖蛋白Shh、膜結合受體patched(Ptch1)、跨膜信號蛋白Smoothened(Smo)、位于Smo胞質尾區的神經膠質瘤相關家族鋅指轉錄因子(Glis)及其調節蛋白[37]。
研究發現,Shh、Smo、Gli1、Cyclin D1 及 Cyclin E1在大鼠PLGC組織中高表達,而Ptch1及SuFu則正好相反[38]。Hh信號通路在慢性胃炎向PLGC過程中起重要作用,H.pylori引起的黏膜炎癥和相關炎癥可通過Hh通路導致壁細胞萎縮、腸化生進展[39]。其中Shh在壁細胞中高表達,Shh通路通過調動干細胞的增殖分化、壁細胞分泌胃酸作用,調節胃上皮細胞的成熟和分化,與PLGC的發生關系密切[40]。CAI等[41]通過觀察 PLGC 大鼠(MNNG 造模)Shh、Ptch1、Smo、Gli1、Gli水平,發現 Shh 信號通路在 PLGC形成過程中被激活,提示Shh信號通路參與PLGC的發病與進展。另外,Shh還參與Nf-κB[42]、TGF-β、Akt/mTOR[43]等信號通路的激活從而誘導PLGC。
趙唯含等[44-45]通過動物實驗(幽門彈簧法制備慢性萎縮性胃炎大鼠模型)研究證實,黃芪、三七及其配伍(益氣活血法)能明顯改善CAG大鼠胃黏膜病變,其機制可能與激活Hh信號通路相關;丁峰[46]通過實驗發現,綠茶提取物可通過下調Shh(SMO/Gli-1)信號通路抑制胃癌細胞增殖及誘導調亡。
6 黏蛋白通路
上皮層是胃黏膜防御的第一道防線,由一層黏液覆蓋,保護胃黏膜上皮免受胃酸、蛋白酶和致病菌的侵害。黏蛋白(MUC)家族是是一組高度O-糖基化的糖蛋白,包括跨膜型和分泌型,其中分泌型MUC是胃黏液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上皮細胞分泌,包括MUC2、MUC5AC、MUC6等,在不同的胃組織中表達各異:在正常胃黏膜組織中,MUC5AC分布于表面小凹上皮,MUC6位于深部腺體,呈陽性表達,而MUC2幾乎不表達;在腸上皮化生的腺體中常可見到MUC2的表達,研究顯示MUC表達水平與胃黏膜腸化的亞型有一定相關性[47];在胃癌組織中,MUC5AC、MUC6呈弱表達,MUC2呈高表達。既往的研究表明MUC異常表達與PLGC及胃癌的發生發展均有關聯[48]。
饒晶等[49]通過臨床試驗,發現健脾清熱化瘀方可通過上調胃黏膜MUC5 AC蛋白的表達,改善PLGC患者癥狀,增強胃黏膜的保護,減輕GIM和Dys;嚴丹等[50]通過隨機對照試驗得出結論,養陰清熱通絡方聯合西藥治療PLGC患者效果顯著,可明顯增加MUC5 AC陽性表達;張啟龍等[51]通過喂養胃黏膜受損大鼠,發現小半夏湯對胃腸黏膜損傷具有防治作用,同時可上調組織MUC5 AC的表達,其機制可能與促進黏膜杯狀細胞分泌黏蛋白、促進黏膜上皮細胞增殖有關。
7 p53信號通路
P53基因是研究最廣泛的抑瘤基因,通過調節靶基因的轉錄、調節細胞周期、抑制細胞凋亡從而維持基因組穩定。該基因的突變與人類50%以上的腫瘤相關,主要是獲得新功能的突變、雜合性缺失等。當DNA損傷時,野生型p53水平增高并活化,能結合靶基因啟動子,促進靶基因表達p21(作為中介物)等,p21可結合、滅活cyclinA/CDK2復合物,將細胞阻滯在G1/G0期,不能進入S期,直到脫氧核糖核酸(DNA)損傷得到恢復,能抑制細胞增殖分化;如果DNA損傷不能被修復,野生型p53持續升高,引起細胞凋亡,避免細胞演變成腫瘤細胞。而p53基因突變,或野生型p53基因蛋白被抑制,DNA受損細胞存活,并進入S期,對致瘤因子、促生長因子敏感,則可能成為失控的腫瘤細胞。
p53在腫瘤發生發展不同階段的表達有差異,過去多認為p53在胃癌發展中是一個晚期事件,在PLGC、早期胃癌組織中很少表達甚至不表達[52],后有報道顯示p53在CAG、GIM、早期胃癌[53-54]中均有異常表達,且p53的不同亞型有差異性表達[55]。突變是腫瘤抑制基因失活的主要機制之一,在胃癌中p53的突變頻率達到32%,研究顯示P53的突變可能與Hp感染相關[56],Hp陽性的患者根除Hp治療后,突變型p53蛋白的表達率從66.7%降至14.3%。
ZHANG等[57]與CAI等[58]通過喂養PLGC模型動物(MNNG造模)發現:黃芪甲苷Ⅳ能緩解PLGC大鼠胃黏膜腸化,其機制可能與調節p53表達相關;熊潭瑋等[59]發現,加味柴芍六君方、胃復春均可改善PLGC大鼠胃黏膜病變,同時抑制p53、Survivin的表達;1項臨床隨機對照研究[60]發現萎胃湯能夠改善CAG患者的癥狀、胃鏡征象、病理情況,降低外周血清及胃黏膜組織中COX-2、P53的蛋白表達量,增強胃黏膜屏障防御和自我修復能力;加味香砂六君子湯被證實可降低大鼠胃黏膜p53 mRNA的表達,具有治療PLGC的作用[61];魏玥[62]發現,益氣化瘀解毒法能通過逆轉p53基因的突變,促進p53發揮其原有抑制腫瘤的作用,從而達到治療CAG伴Dys大鼠,逆轉PLGC的目的。
8 討論
PLGC是胃炎發展至胃癌的中間環節,SONG等[63]統計32年間40余萬患者胃黏膜的活檢結果,發現約有1/256胃黏膜正常者、1/85胃炎患者、1/50的CAG患者、1/39的GIM患者、1/19的Dys患者在20年內發展成胃癌,提示在PLGC階段及時干預,對于延緩病程甚至逆轉病變具有重大意義,也是胃癌二級預防的重要部分。
目前PLGC的藥物治療仍存在爭議,2019年歐洲PLGC管理共識[64]將Hp根除治療列為高質量證據的治療手段,但只在胃炎、GIM階段能顯著降低胃癌發生風險,而其他藥物治療,包括COX抑制劑、抗氧化維生素的補充、非甾體類藥物均列為弱推薦;值得一提的是,共識首次提出中成藥摩羅丹治療PLGC具備一定療效,但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及機制研究作為支撐,指出中醫藥治療PLGC的潛力所在。依據PLGC的臨床表現,可納入中醫“胃脘痛”“痞滿”等范疇,外感六淫、情志不暢、飲食不節、素體脾虛均會導致發病,目前對于PLGC的中醫藥治療未統一,多數醫家從虛[65]、從瘀[66]論治。另外,由于PLGC常緩慢進展,有些患者甚至沒有任何癥狀,需久病緩圖,故摩羅丹、胃復春、增生平等中成藥廣泛應用于臨床,但相關的機制研究較少。整體而言,當前PLGC的治療無規范化的模式,機制研究也不夠深入,因此進一步探索其確切機制,從而有的放矢是當前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
筆者從PLGC的發病機制切入,綜述了導致發病的常見信號通路以及基于此信號通路中醫藥治療的研究進展。當前,運用中醫手段治療PLGC的顯著療效及良好的安全性已得到廣泛認可,也不乏相關的臨床研究及機制探索,但綜述發現:相關的臨床試驗普遍質量不高,尚缺乏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雙盲的臨床試驗;機制研究不夠深入;另外,對中藥的有效單體、劑量劑型與療效相關性的研究較少,有待進一步挖掘。筆者認為,中醫藥治療PLGC,應師古而不泥古,一方面,在充分傳承中醫經典的基礎上,利用當前先進的內鏡及病理技術,將傳統辨證與內鏡、病理下辨證相結合,將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改善癥狀與截斷逆轉相結合,優化遣方用藥方案,提高臨床治愈率,最大化發揮中醫藥獨特優勢;另一方面,應在當前PLGC發病機制國內外最新研究的基礎上,深入探索中醫藥治療PLGC中的確切機制及發揮作用的靶點,為臨床用藥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