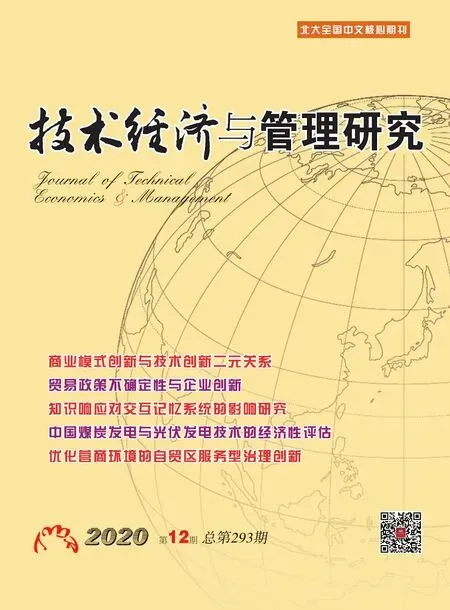知識響應對交互記憶系統的影響研究
——基于知識權力視角
雷 軼,陳云川
(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330063)
一、引言
在知識更新與技術迭代急速加快的背景下,創業者越來越多地依賴團隊來提高創新能力與存活率。然而,實踐中常有“全明星創業團不如一般團隊成績好”的現象。交互記憶系統理論從微觀過程視角洞察團隊內部的知識分布、整合及應用,為創業團隊管理提供了獨特的解釋。Dai 等認為交互記憶系統(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以下簡稱TMS) 是對不同領域專業知識的編碼、存儲和檢索的分工合作系統,是協調成員間相互依賴專業知識的有效機制[1]。當創業團隊形成高效的TMS 時,成員可以相互了解知識存儲的位置(如了解專業知識位置) 并檢索該知識以支持團隊任務(如協調任務),同時當創業團隊成員對彼此的專業知識有信心時,成員更愿意將其他成員的專業知識綜合到團隊的知識庫中。此外,團隊也可以識別有關特定主題的專家,并將任務分配給將最佳執行者,這可以提高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美國哈佛大學Herman 教授研究了多個森林火災消防員犧牲的案例后發現,團隊內部有效交互傳遞火災中的信息,隊友相互信賴彼此的消防技能,促使消防員主動靈活調整滅火行動方案,是確保消防員安全完成任務的關鍵因素。
Akgun 等指出TMS 為創業團隊提供了一個隱形的“知識處理平臺”,特別是對于經常從事復雜、非常規和創新任務的知識密集型團隊,成員能在這個平臺進行知識交流與知識交換,同時促進新思想與新知識的產生,團隊的TMS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知識管理的效果[2]。圍繞TMS 具有知識管理的本質這一問題,國外學者在近兩年開展了一系列前沿的研究,Huang 等實證了團隊的知識分享行為對TMS 有積極正面作用,而知識整合對TMS 與團隊績效具有中介作用[3]。Olabisi and Lewis 實證了TMS 對團隊內知識轉移具有促進作用,而專業知識流動對TMS又有積極正面作用[4]。這些研究為正面理解團隊TMS 的形成機理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參考。然而,這些研究普遍忽略了不同創業團隊具有不對等的知識資源影響力的情境,以及團隊內部存在推諉裝傻等故意隱藏知識的反分享行為,隨著知識權力、知識分享和知識隱藏等概念的興起,它們是否同時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創業團隊TMS 的形成?對此,研究者迫切需要進一步的回應與解釋。
文章擬在知識管理理論框架內,以國內眾創空間的眾創團隊為研究對象,從知識權力視角下探索眾創團隊成員在面對隊友的“知識求助”時,其選擇“知識分享”或“知識隱藏”的響應行為是如何作用團隊的TMS。具體而言,文章嘗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知識權力是否影響眾創團隊形成TMS?知識分享是否影響眾創團隊形成TMS?知識權力是否調節知識分享對TMS 的影響?知識隱藏是否影響眾創團隊形成TMS?知識權力是否調節知識隱藏對TMS 的影響?
二、理論述評與假設提出
美國心理學家Wegner 最早用知道誰知道什么(know who know what)來描述親密人群中的交互記憶現象[5],經過30 余年的演化拓展,TMS 已成為學者研究團隊知識分布、知識整合及知識應用的主要工具[6]。從已有文獻來看,對團隊TMS 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理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內:一是成員知識異質性[7]、專業知識深度[8]、自信傾向、心理安全感和年齡性別等團隊內部個體屬性特征方面探索對TMS 的影響;二是從團隊知識分布與知識共享、團隊溝通與信任[9,10]、團隊任務相互依賴、團隊斷裂帶[11]、共享心智模式與行為信任[12]等團隊整體屬性方面探索TMS 的形成機理;三是從外部急性壓力和壓力源[13]、外部社會網絡或網絡關系[14,15]、組織領導風格[16]和組織自尊[17]等團隊外部因素方面探索對TMS 的影響。
目前,部分學者關注到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喪失感會抑制知識分享行為,以及知識隱藏是團隊TMS 形成機理的障礙性因素。然而,從知識權力視角下探索眾創團隊的知識隱藏與知識分享行為如何影響團隊TMS 還存在很大研究空間。文章構建了知識權力視角下知識響應對TMS 影響的概念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知識權力視角下知識響應對TMS 影響概念模型
1.知識權力對TMS 的影響
社會學者Latiff 和Hassan 在研究穆斯林世界興衰過程中首先提出了知識權力的概念[18],現已成為網絡權力理論中的核心概念,特指知識節點(組織、團隊或個體) 由于擁有異質性或關鍵性知識資源而對其他知識節點產生的支配能力與控制能力[19,20]。
當前,國內學者主要聚焦于研究企業網絡體系與技術創新網絡中的知識權力,如核心企業知識權力的作用[21],知識權力的影響因素、形成機制與測度模型[22]。部分學者從知識分享或知識網絡理論視角研究知識權力,如探索知識權力對網絡分裂斷層與知識共享關系的調節作用,知識權力對多重知識網絡演化的影響,知識權力非對稱對知識共享行為的直接影響等[23]。團隊層面中關于知識權力的研究主要有,李衛東和劉洪實證了研發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喪失較強時會抑制知識共享行為[24],而潘偉和張慶普則實證了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喪失較強時會提高知識隱藏行為[25]。
國內外尚未有專門探索知識權力影響TMS 形成機理的研究文獻,但從其概念內涵與TMS 的子維度來看存在緊密關聯。TMS 包括3個維度:維度1—專長度是結構要素,體現團隊成員所擁有知識資源的專門化以及差異化程度;維度2—可信度是對專長度行為的認知要素,體現個體對團隊其他成員專長和能力的信任;維度3—協調度是建立在專長度與可信度基礎上的行為要素,體現了團隊成員在工作中對彼此專業知識的整合[26]。因此,TMS 的3個維度并非平等關系,而是遞進的關系[27]。團隊成員知識權力的基礎就是擁有關鍵核心的知識資源,這與TMS 維度1 體現知識資源專門化與差異化的專長度直接關聯。同時,知識權力的非對稱性表現在隊員相互影響力與控制力存有差異,這與TMS 的維度3 體現團隊成員在工作中對彼此專業知識整合的協調度也存在密切關聯。另外,具有更強知識權力的團隊,意味著成員的專業知識具有更高的專業門檻,這要求成員需要更多的相互交流學習,以此提高個體對團隊其他成員專長和能力的信任,這與TMS 的維度2 可信度存有內在關聯。綜上而言,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眾創團隊的知識權力對團隊TMS 有直接的正向影響,即眾創團隊的知識權力正向影響TMS 的專長度(H1A)、可信度(H1B)與協調度(H1C)。
2.知識分享對TMS 的影響
知識分享意愿是指知識擁有者愿意將自己的工作經驗、工作技術以及對事物的看法傳遞給他人的意愿與行為。基于社會互動視角,許多學者證明了團隊成員之間的知識共享、協調和交流有助于形成TMS。例如,Ren 和Argote 的研究證明了社交互動流程對于TMS 的發展很重要,原因是建立強關系和分享更多知識可以幫助團隊成員準確地了解彼此之間的專業知識;Hongli 等和Dokko 等的研究證明了要了解彼此的專業知識,團隊成員必須保持積極的社交互動過程。
基于知識管理視角,許多學者實證分析了知識分享有助于提高TMS 的效能。Kotlarsky 等證明了團隊成員的知識界限對TMS 的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而Ren 和Argote 的研究發現知識共享可以減少知識界限,并幫助成員識別彼此的專業知識。最近有兩項研究支持知識分享直接影響TMS 的形成,Jin 等的研究發現TMS 的成功或失敗通常取決于團隊成員的關系和知識共享[28],而Huang 等基于臺灣55個研發團隊樣本,實證分析了團隊的知識分享對TMS 有積極正面影響。
從知識分享視角探索TMS 的形成機理是當前研究熱點,但尚未有專門探討知識權力與知識分享影響TMS 形成機制的文獻,比較接近的研究是李衛東和劉洪實證分析了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喪失感會阻礙成員的知識共享意愿,從而降低成員的知識共享行為。從管理實踐來看,當成員感知到自己具有較高知識權力時,在具有共同團隊目標愿景下將促使更多的知識分享行為[24]。綜上而言,文章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H2:團隊成員的知識分享行為正向影響團隊TMS,即眾創團隊的知識權力正向影響TMS 的專長度(H2A)、可信度(H2B)與協調度(H2C)。
假設H3: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正向調節知識分享對團隊TMS 的作用力度,即眾創團隊的知識權力正向調節知識分享對TMS 的專長度(H3A)、可信度(H3B)與協調度(H3C)。
3.知識隱藏對TMS 的影響
知識隱藏是由知識分享理論衍生出來的新構念,特指員工面對同事知識請求時故意隱瞞或刻意掩飾的行為,主要包括佯裝不知、推諉隱藏和合理性隱藏三種方式[29]。員工通常為了避免暴露知識隱藏行為而有顯示率較低的特點,但知識隱藏行為在團隊中普遍存在[30]。一項來自美國對1700 余名員工的調查表明,76%的員工存有對同事隱藏知識的行為。國內外就知識隱藏的內在結構,知識隱藏行為會引發同事間不信任循環而導致團隊創造力下降以及工作時間壓力[31]、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對知識隱藏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研究[32]。
目前,國內外尚未有從知識權力視角下探索知識隱藏影響TMS 的文獻,僅有一項知識隱藏對團隊TMS 影響的專項研究,以及多項與本研究存在內在關聯的TMS 研究。陳帥與陳偉的兩項研究表明,在員工間交換知識的前提下,團隊斷裂帶會對TMS 產生負面作用;Hood 等探討了心理安全感對TMS 的作用[33];Pulles 等的研究發現,在員工愿意輸出知識,并保證知識充分流動的情境下,團隊成員之間的網絡聯結對TMS 的可信度和協調度產生顯著影響[15];李浩和黃劍就知識隱藏對團隊TMS 的影響做了專門研究,揭示了團隊知識隱藏是TMS 的一個重要的阻礙性前因變量[27];潘偉和張慶普實證了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喪失感較強時會促進知識隱藏行為發生[25]。同時,具有較高知識權力的成員更可能成為同事請教咨詢的對象,也就更有可能發生知識隱藏行為的可能性。綜上而言,文章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4:團隊成員的知識隱藏行為負向影響團隊TMS,即眾創團隊的知識隱藏行為負向影響TMS 的專長度(H4A)、可信度(H4B)與協調度(H4C)。
假設H5:團隊成員的知識權力正向調節知識隱藏對團隊TMS 的作用力度,即眾創團隊的知識權力正向調節知識隱藏對TMS 的專長度(H5A)、可信度(H5B)與協調度(H5C)。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文章以入駐眾創空間的眾創團隊為調查對象,主要基于兩個原因。首先,自2015年國家大力推動雙創工作后,眾創空間已成為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載體,各地的眾創團隊成立時間差距不大,也就是說眾創團隊的TMS 基本處于同一時間起點,這為文章提供了可比較時間跨度的樣本;其次,眾創團隊需要頻繁與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和其他創新機構進行技術交流、信息共享以及聯合解決問題,很明顯眾創團隊從屬于適合文章研究的知識密集型行業。與此同時,考慮到眾創空間的發展參差不齊,文章對研究對象的界定包括以下三個條件:一是至少是省科技廳部門以上認可的眾創空間;二是眾創團隊的正式運行時間不能低于兩年;三是眾創團隊成員必須超過3人。文章據此選擇了杭州夢想小鎮、江西先鋒天使咖啡、上海Imagine 創想空間等88個眾創團隊的386個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樣本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樣本基本情況表
2.問卷調查與變量測量
研究采取兩種問卷調查方式,一是研究人員現場發放現場回收。研究人員現場對眾創團隊充分講解了測試的背景與目的,努力營造出一種輕松平和的環境,特別介紹知識隱藏行為與相關術語,指出知識隱藏行為并不是一種“不好”的行為,確保調研對象能真實準確填寫調查問卷;二是在當地眾創空間聯盟組織和政府部門的協助下,研究人員通過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人員留有電話、微信或qq 等工具講解相關術語,以保證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對英文翻譯過來的測量條目均使用回譯法,對于個別存在差異的條目,項目組和翻譯人員經過反復商討最后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問卷共回收448 份問卷,剔除了62 份雷同和回答不全等無效問卷后,供研究使用的有效問卷為386 份。
(1) 知識權力
知識權力的測度,文章借鑒已有關于知識權力的權威文獻,采用Pahlberg 和Galaskiewicz 從影響知識控制力和知識影響力兩方面的4個測量條目,結合文章中知識權力內涵和眾創團隊的特性進行了相應的修正。量表通過“在您看來,對您所在團隊可確定的知識權力評價如下(評價分值從“1=根本沒有”到“5=非常同意”)”的李斯特5 點法衡量。其中,知識控制力的2個條目為“貴團隊所擁有的技術知識是難以模仿的”和“貴團隊如果退出當前工作,會給其他團隊(或組織) 的創新帶來極大不利”,知識影響力的2個條目為“在技術交流中貴團隊對其他團隊(或組織) 會產生很大的壓力”和“很多其他團隊(或組織) 模仿貴團隊的成功經驗”。
(2) 知識分享
許多學者根據研究的需要開發了較多的知識分享量表,整體而言,可分為對知識分享意愿和知識分享行為的測量。文章研究的重點在知識分享行為方面,采用了國內廖國鋒和吳建平兩位學者提出的知識分享行為的5個測量條目,其中第5個條目“在撰寫文件時,我愿意將知道的記錄下來供同事參考”不適合本研究情景,予以凈化刪除。量表通過“您對所在團隊可確定的知識分享行為評價如下(評價分值從“1=根本沒有”到“5=非常同意”)”的李斯特5 點法,衡量采用的4個條目分別為“我經常鼓勵同事提出好的看法及建議,以提升技術水平”、“我經常幫助同事解決問題”、“同事有問題時,我會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和“對于不易說清楚的事,我會為同事示范”。
(3) 知識隱藏
知識隱藏問卷改編自Connelly 等編制的共12個題項條目,問卷包括推托隱藏、裝傻隱藏和合理化隱藏三個維度,量表通過“當同事向你詢問某些知識時,你采取的行為如下(評價分值從“1=根本沒有”到“5=非常同意”)”的李斯特5 點法,如推脫隱藏條目為“我可能會同意幫助他,但并不真的打算這樣”、“我可能會同意幫助他,但會給出與其所需不同的知識”等;裝傻隱藏條目為“我會說我不知道,盡管我知道”、“我可能會說我對這個話題所知不多”等;合理化隱藏條目為“我可能會解釋我愿意告知他,但有人不希望我這樣做”和“我會解釋這項信息是機密的,只有特定項目的相關人員可以獲得”。
(4) 團隊交互記憶系統
國外對團隊交互記憶系統的測量主要是基于Lewis 等開發的量表上修訂完善,文章測量交互記憶系統的量表借鑒了Lewis 等的研究,并以張志學等和莫申江等的量表15個條目略加修改。量表通過“您對所在團隊如實評價如下(評價分值從“1=根本沒有”到“5=非常同意”)”的李斯特5 點法,如專長維度包括“團隊每個成員都具有與任務有關的某方面的知識”和“團隊每個成員各自負責不同方面的工作”等;可信維度包括“我能夠坦誠地接受團隊其他成員的建議”和“我信賴團隊其他成員掌握的知識”等;協調維度包括“一起工作時我們團隊內部協調得很好”和“我們團隊對該做什么很少產生誤解”等。
四、數據分析
1.描述性統計與信效度
文章主要采用Cronbacha 系數和條目的CITC 值來檢驗調查數據的一致性與穩定性,知識權力、知識分享、知識隱藏和團隊TMS 的團隊層面數據均使用個體Likert 量表的數據匯總而來,從統計數據來看,4個變量的35個測量條目的Cronbacha系數均大于0.75,CITC 值均大于0.5,符合團隊內個體成員評分數據整合加總的合理性檢驗標準,具體數據如表2 所示。

表2 研究變量的均值、方差及相關系數(N=386)
另外,文章主要采用坎貝爾等人提出的收斂效度與區分效度對問卷數據進行效度檢驗。具體而言,通過RMSEA、NNFI和CFI 這3個指標來衡量數據,正如Hu 和Bentler 主張的那樣,一個好模型的RMSEA 應該接近或低于0.06,而NNFI 和CFI 應該達到或超過0.95。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后發現,3個自變量的χ2值為790.52(df=383),CFI 為0.94,NNFI 為0.93,RMSEA 為0.08。因此,即使RMSEA 不是非常理想,但從統計上而言基本還是可以接受3個自變量的模型。之后運用相同的方法,對團隊交互記憶系統的3 維度模型(專長性、可信度和協調度) 進行驗證性分析,統計結果表明3個不同維度非常清晰。統計數據顯示:χ2/df=2.96,CFI=.93,NNFI=.92,RMSEA=.08,專長性與可信度的相關性為.49,與協調度是.34,可信度與協調度.52,χ2的差異檢驗表明,當限定兩兩相關值為1 時,Δχ/Δdf 的范圍從22.77/1(p<.01)到523.85/1(p<.01),模型質量顯著變差。
2.控制變量
文章主要探討團隊交互記憶系統受到知識權力、知識分享、知識隱藏3個自變量的影響。因此,文章力求排除成員屬性和團隊屬性等變量對結果變量的作用,然后再獨立考察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研究將對人口統計學變量和團隊屬性等變量的數據,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來檢驗它們對TMS 的影響是否顯著時,當該變量的顯著性小于0.1 時時該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模型將在排除控制變量對TMS 的影響后,單獨考察知識權力、知識分享、知識隱藏3個自變量對TMS 影響。在單因素方差分析時,當組間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根據檢驗方差齊性與否來決定多重比較的方法,在方差具有齊性時采用LSD 多重比較方法,在方差非齊性時則采用Tamhance 法對均值進行兩兩比較。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和LSD 多重比較方法后,文章將年齡、團隊規模、團隊年齡、營業額作為控制變量。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并不把學歷作為控制變量,主要是學歷與本研究的知識權力自變量存在重疊交叉的領域。一般而言,學歷越高的團隊成員一般擁有更豐富更前沿的知識資源,其知識權力也越強越大。
3.知識權力對TMS 的影響
文章運用SPSS23.0 檢驗知識權力對TMS 的直接效應,進而判斷假設H1 的合理性。具體說來,首先引入年齡、團隊年齡、團隊規模和營業額4個控制變量,再引入知識權力自變量,從相關系數表2 來看,由于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表明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可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的具體結果如表3。數據顯示,在控制了年齡、團隊年齡、團隊規模和營業額后,知識權力對專長性(β=.16,p<.01)和協調度(β=.17,p<.01)均具有正向作用。對于指向專長性維度而言,控制變量解釋了其中的3.0%方差變異,在此基礎上,知識權力自變量解釋了專長性維度的1.0%方差變異,F 檢驗可知此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0.01 水平上是顯著的。對于TMS 協調度維度而言,控制變量解釋了其中的5.1%方差變異,而知識權力解釋其中的2.2%方差變異,并在0.01 水平上是顯著,且通過F 檢驗。然而,對于TMS 中可信度維度而言,F 檢驗可知在0.1 水平上都是不顯著。因此,假設H1中眾創團隊的知識權力正向影響TMS 的專長度(H1A)與協調度(H1C)得到驗證支持,正向影響可信度(H1B)并未得到驗證支持。
4.知識分享對TMS 的影響
研究數據顯示,在控制了包括知識權力、年齡、團隊年齡、團隊規模和營業額后,知識分享對專長性(β=.28,p<.01)、可信度(β=.19,p<.05)和協調度(β=.14,p<.1)均具有正向作用。對于指向專長性維度而言,知識分享自變量解釋了專長性維度的9.0%方差變異,而且通過F 檢驗可知此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0.01 水平上是顯著的。對于TMS 中可信度維度而言,知識分享自變量解釋了可信度維度的6%方差變異,F 檢驗可知此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0.05 水平上是顯著。對于TMS中協調度維度而言,知識分享解釋其中的5%方差變異,并在0.1 水平上是顯著,且通過F 檢驗。因此,假設H2 得到驗證。
另外,從表3 可以看出,在放入交互項(知識權力×知識分享)之后對專長性的方差貢獻從13.1%提高到18.2%,交互項對專長性的方差貢獻率是5.1%(b=0.18,p<0.01),且均通過F 檢驗,說明了知識權力能對知識分享與TMS 之間具有調節效應。與此類似,交互項對可信度的方差貢獻率3.3%(β=0.069,p<0.05),對協調度的方差貢獻率為2.1%(β=0.069,p<0.1),且均通過F 檢驗。因此,假設H3 均得到驗證。

表3 知識權力、知識分享和知識隱藏與交互記憶系統的交互效應(N=386)
5.知識隱藏對TMS 的影響
數據顯示,在控制了包括知識權力、年齡、團隊年齡、團隊規模和營業額后,知識隱藏對可信度(β=-.17,p<.01)和協調度(β=-.1,p<.05)均具有負向作用。對于TMS 中的可信度維度而言,知識隱藏自變量解釋了可信度維度的8.0%方差變異,F 檢驗可知此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在0.01 水平上是顯著。對于TMS 中協調度維度而言,知識隱藏解釋其中的4%方差變異,并在0.05 水平上是顯著,通過F 檢驗。然而,對于指向專長性維度而言,知識分隱藏自變量F 檢驗在0.1 水平上都是不顯著。因此,假設H4 中眾創團隊的知識隱藏負向影響TMS 的可信度(H4B)與協調度(H4C)得到驗證支持,正向影響專長性(H4A)并未得到驗證支持。
從表3 可以看出,交互項(知識權力×知識隱藏)對專長性具有顯著負向關系(β=-0.18,p<0.05),可信度的方差貢獻從14.2%提高到17.2%,交互項對專長性的方差貢獻率是2%(β=-0.20,p<0.05),且均通過F 檢驗,與此類似,交互項對協調度的方差貢獻率5%(β=-0.31,p<0.01),均通過F 檢驗。因此,假設H5 均得到驗證。
五、研究啟示與局限
作為一項針對創業團隊關于知識管理領域方面的研究,文章結論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具有啟示與價值:
一是創業團隊的知識權力對團隊TMS 的形成機制有重要影響。這突破了以往研究默認創業團隊具有同等均值的知識資源影響力與控制力的假設,文章視角新穎且更符合團隊的真實情境,為許多知識管理學者秉持“創業團隊的知識資源及影響力是創業成功與否的關鍵變量”觀點提供了實證支撐。
二是知識分享與知識隱藏是兩個獨立的變量。有學者從概念內涵和組織行為層進行了辨析與討論,認為這兩個變量并非同一軸線上的相互對立端,知識分享與知識隱藏行為常常同時存在或同時消失。然而,文章首次實證分析了兩個變量雖然存在較大重疊交叉領域,但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變量,即在控制了知識分享變量因素后,知識隱藏仍然能解釋團隊TMS 的方差。
三是對于管理實踐者而言,減少團隊的知識隱藏行為并不意味著有高水平的知識分享行為,管理者需要避免團隊中的佯裝不知型與推諉隱藏型知識隱藏行為。其次,當面對“知識求助”時,團隊成員無論選擇“知識分享”還是“知識隱藏”行為,都直接影響團隊TMS 形成高效的。再次,管理者需要充分培育及運用團隊的知識權力,以此更有效促進團隊形成高效的TMS。
與此同時,兩個未證實的研究假設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首先,知識權力與可信度的關系非常微弱,一種可能性是眾創空間創業團隊個體有50%為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且部分成員為剛大學畢業不久后的從業人員,他們在知識權力屬性方面比較微弱,主要依靠或遵從眾創團隊已有知識權力的屬性,這與成熟型團隊成員經過知識互動與知識整合形成新的知識權力存在較大不同。另外,知識隱藏與專長性的關系也非常微弱,這與已有研究認為知識隱藏是TMS 的一個重要的阻礙性前因變量并不完全一致,這與眾創團隊成員相當年輕,加入眾創團隊時間不長有關聯,原因是其專長性主要由入眾創團隊之前的人力資本儲量構成,而通過團隊之間的互動學習形成專長性顯得相對薄弱,這導致知識隱藏行為與TMS 中的專長性沒有很強的關聯性。可進一步探討的是將知識隱藏區分為佯裝不知型、推諉隱藏型和合理隱藏類型,分別探討與團隊TMS 的3個子維度的關聯。
文章需特別注意指出的是存在數據方面的局限。研究按照最方便采集原則把正式運營時間不低于兩年的眾創團隊作為樣本,采用了自行匯報問卷的方式來收集橫截面數據,盡管通過控制樣本的一些個體特征和團隊特征屬性變量來控制其對結果的影響,但并未排除樣本自我選擇偏差的影響,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問題。另外,通過自我匯報法調查成員的知識隱藏行為時,不排除個體有意規避真實行為的可能性,適時采用縱向數據或他人匯報成員(譬如主管或同事) 也許會真實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