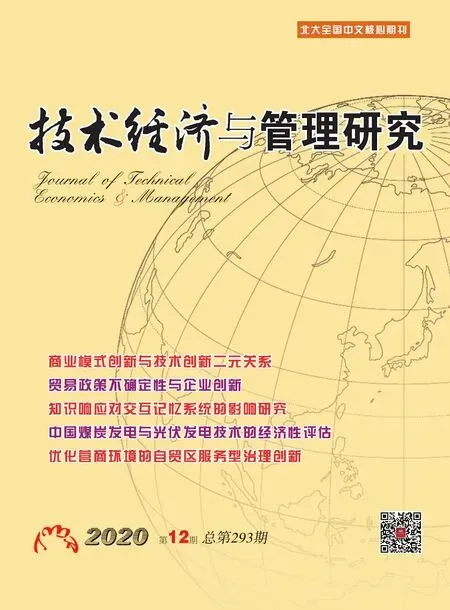財政分權、政府競爭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陳 明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100142)
一、問題提出
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當前及以后的經濟發展會更加注重質量的提升,而不是追求單一的數量方面的增長,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首次出現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更是彰顯了這一國家治理理念。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早期實現的高速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郭慶旺等,2005),為了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持續推進科技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學者們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大致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在宏觀層面整體進行考量的研究中:一是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以及對測算方法適用性的研究,二是對關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制約和影響因素的分析(繆小林等,2019)。微觀層面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主要圍繞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來展開。同樣,學者們對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法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討,有參數法、非參數法和半參數法等多種測算方法(Olley,1996;Levinsohn,2003),但僅在微觀領域探討各種因素可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構成的影響(李唐等,2018)。綜上來看,關于通過宏觀經濟的制度特征和管理框架對于微觀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李強(2017)基于制造業企業數據研究發現環境分權與地區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呈倒U 型關系。何美玲等(2019)通過研究發現金融分權顯著促進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二者之間同樣保持著倒U 型的關系。求根溯源的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關鍵是技術的進步和管理效率的提升,國家治理者在制定了更加宏觀的政策后,市場上的企業最終會作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微觀主體,我國宏觀制度的形成、政策的制定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的經營方式和策略選擇。因此,文章從宏觀角度入手去研究微觀問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我國自1994年進行分稅制改革后,建立了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體制框架,成功的實現了由行政性分權向經濟性分權的轉變(賈康,2010),財政的分權模式一直是央地政府之間國家治理的重要制度框架。行政性分權轉變為經濟性分權的制度約束,迫使地方政府轉換發展地方經濟的方式,打破舊有的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模式,在制度上對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進行了更加明確的安排,這種財政分權體制對我國長期以來經濟的飛速發展也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另一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一方面是地區發展之間的競爭,包括人才、資金、能源要素等的競爭,另一方面是由于“晉升錦標賽”的激勵機制(周黎安,2007) 等原因使地方政府官員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明顯的偏向性。因此,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必然會對企業的經營戰略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進一步的,關于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
較之先前的研究,文章存在的創新和貢獻在于:一是嘗試從微觀企業角度著手,探索在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的制度框架下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何種的表現;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滬深證券市場A 股上市企業較大樣本量,運用LP、OP、ACF、WRDG 等四種方法分別測算了企業的要全素生產率,并與宏觀層面的財政分權、政府競爭共同納入一個研究框架中進行匹配分析,試圖找到更為詳實深刻的研究結論。文章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進行文獻綜述并提出研究假設;第三部分介紹研究設計的框架;第四部分進行實證分析和穩健性檢驗;第五部分進一步分析討論;第六部分對全文進行總結。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說
在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的基本事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央在加強政治集權的同時,又在經濟上進行分權,“中國特色財政聯邦主義”將這種財政預算軟約束的分權方式認為是地方政府激勵的重要制度安排(Qian &Roland,1998),而地方政府激勵是我國實現經濟騰飛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從政府競爭的角度看,地方官員面臨的“晉升錦標賽”激勵(周黎安,2007) 以及地方政府競爭的評價標尺左右著地方政府的行為,這也被認為是中國模式獲得成功的關鍵。因此,長期以來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都被認為是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重要理論框架,地方政府的行為選擇正是在這種理論框架下進行的。
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分為支出分權和收入分權,自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關于財政收入的劃分清晰明朗,但是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表現出層層下移的趨勢,并且省級以下的財政體制改革尚不徹底,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逐年擴大。以政府之間的“GDP 錦標賽”和地方官員之間的“晉升錦標賽”為特征的地方政府競爭加劇了地區間的經濟競爭。在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的雙重壓力下,迫使地方政府的行為是以提高經濟增長、擴大財政收入規模為導向的,從而更多的介入到經濟建設上,在人才、資金、技術、能源等多領域展開競爭(賈俊雪,2015),而這種關于宏觀政策制定和微觀企業扶持的競爭政策本身就是一種偏向性的政策,由此可以說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框架下政府的行為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1.地方政府行為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效應
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政府較之于中央政府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優勢在于其能夠掌握更加完全的信息,地方政府較低的層級和較高的自主決策權使其能夠向社會提供更加高效的公共產品和服務(Tiebout,1956),財政資金支出的效率也能夠得到提升,因而所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當地發展的真實情況。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框架下地方政府行為可能通過以下機制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一是地方政府為了能夠在更加長期的競爭中占據優勢,會平衡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將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到科技創新、人才教育和技術引進等領域,根據企業的短板和劣勢給予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促進中高端產業的技術升級(賈妮莎,2016);二是財政分權影響高技術產業增長的重要途徑是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解決長期財政壓力的根本辦法就是培養地方財源,政府對積極創新的企業進行稅收優惠,使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空間投入到技術研發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中(尹朝靜,2017),利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三是政府競爭機制的存在會誘導地方政府保護主義的盛行,短期來看,這種市場分割有效降低了轄區內企業競爭的激烈程度,企業所受到的外部沖擊會更低,經營環境更加寬松,有利于有進取心的企業調整經營戰略,加大研發投入、技術引進并擴大投資規模,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就會相應提升(徐保昌,2016);四是在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下,不能很好適應地方政府競爭利益需求的企業在得不到政府特殊的政策支持的情況下,會將更大的市場份額讓渡給生產率高的企業。
2.地方政府行為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抑制效應
雖然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權激勵下對于財政政策的制定、財政資金的運用擁有更高的自主度和靈活性,但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的約束同樣具有兩面性,地方政府行為如果收到競爭的過度刺激而過于激進,很可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生負向影響。一方面地方保護主義下企業與政府容易走上合謀的道路,受到保護的企業更加容易獲得銀行資金以及政府補貼,不僅要素市場被扭曲,外部企業進入的門檻也被提高(蓋慶恩等,2015),在這種地方壟斷的情況下,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就會不斷下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隨之降低,同時轄區內缺乏進取精神的企業往往安于現狀,企業的自主研發、引進先進技術等行為受到阻礙,進而導致財政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促進效應轉變為抑制效應(李強,2017)。另一方面,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的大部分稅收收入來源于轄區內的企業,企業部門所創造的價值必然要有一部分通過稅收的分配效應流入到地方政府,政府在面對財政壓力和競爭壓力時會合乎邏輯的將壓力轉嫁到企業中,原因有二:一是更高的稅收負擔容易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過多的企業利潤流失也會進一步削弱企業研發的動力(Evans&Leighton,1990);二是企業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與支持是需要花費一定的尋租成本來維持這種關系,隨著更多的企業資源投入到尋租的過程中(羅黨論,2009),企業內部管理的創新和績效激勵等容易被忽視(Manso,2011),資源的浪費和企業效率的損失會直接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此外,在政府競爭的“GDP 錦標賽”約束下,地方政府會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能夠迅速帶來經濟增長效果的領域,相應的在教育、科研等領域的投入比重會降低(孫一菡等,2017),由此缺乏了人才和技術的支持,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去就會造成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財政分權水平和政府競爭程度的變動可能對微觀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顯著的影響,但綜合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來看,這種關系可能并非表現為簡單的線性特征,故文章提出假設,財政分權水平和政府競爭程度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具有顯著的U 型效應;同時,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地方政府所面臨的發展壓力側重點或有不同,因此這種U 型效應可能會表現出地域異質性;進一步來看,微觀市場上的企業構成更為復雜,具有不同的產權性質、行業特點、經營策略和發展階段的微觀企業都有可能對這種U 型效應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即這種U 型效應可能存在企業異質性。
三、研究設計
1.模型設計
文章構建了如下的模型(1)用以檢驗財政分權、政府競爭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其中,lnTFPij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注冊于i 省份的j 企業在t年度的全要素生產率,Fdit表示i 省份在t年度的財政分權水平,實證研究中用Fdeit和Fdrit替換進行回歸分析,Gcit用來描述i 省份在t年度的政府競爭水平,Xijt為控制變量,為時間、省份、行業的固定效應,εijt為誤差項,α0、α1、α2、α3、α4、β 為參數。
2.變量設定
(1) 被解釋變量
文章采用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所設定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對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參數法、非參數法和半參數法等多種測算方法,由于其能夠較好的避免產生內生性和選擇性偏誤等問題(魯曉東、連玉君,2012),OP 法、LP 法等半參數法被學者們廣泛采用。此外,還有ACF 法和WRDG 法等。Levinsohn 和Petrin(2003)對OP 法進行了改進,LP 法雖然沒有考慮企業退出可能帶來的內生性偏誤問題,但是可以減輕OP 法用投資作為代理變量引致的觀測值遺失較為嚴重的問題,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據可獲得的數據靈活選擇代理變量。鑒于此,文章參考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的做法分別通過OP 法、LP 法、ACF法、WRDG 法測算樣本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并將以LP 法的測算結果用于基本的實證分析,將以OP 法、ACF 法、WRDG法的測算的結果作為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
對于上述幾種測算方法中所涉及到的關鍵變量,文章綜合考慮了測量方法的適用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采用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收入來代替總產出增加值,中間投入采用主營業務成本加三費(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 再減去折舊攤銷和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來表示,資本投入變量采用固定資產凈值表示,勞動投入變量采用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表示,企業投資變量參考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的做法,用It=Kt-Kt-1+Dt 進行估算,其中K 表示固定資產總值,D 為折舊和攤銷,企業是否退出以考察年份企業是否退市為準。
(2) 解釋變量
模型中解釋變量包括政府競爭(Gc)和財政分權(Fd),文章關于政府競爭的表示參考學者們普遍采用的做法,即由外商投資總額與省級GDP 的比值進行表示。對于財政分權的定量研究,當前較為普遍的做法包括收入法和支出法兩種,即收入法用本級地方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表示,支出法用本級地方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表示,文章根據這一衡量方式,參考賈俊雪和應世為(2016)的研究用省級財政人均收入/(省級財政人均收入+中央財政人均收入)表示財政收入分權(Fdr),用省級財政人均支出/(省級財政人均支出+中央財政人均支出) 表示財政支出分權(Fde)。
(3) 控制變量
根據前文分析和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文章從宏觀經濟發展環境和微觀企業經營狀況兩個層面進行控制變量的選取,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Eco)、城鎮化率(Urb)、資本形成率(Capfr)、產業結構(Inds)、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資產收益率(Roa)、資本密集度(Cap)、企業年齡(Age)、固定資產比率(Fixed)、總資產周轉率(Totat)、勞均資本(Cappl)、平均工資率(Labq)。在進行計量模型分析時,還對省份(Province)、年份(Year)和行業(Industry)進行了控制,變量定義和釋義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變量定義與說明
3.樣本及數據來源
文章選取2007-2018年在滬深兩市A股市場上市公司數據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借鑒文獻的常見做法,對初始 樣 本 的28153個樣本觀測值進行如下標準篩選:剔除金融保險類和房地產上市公司;刪除ST、*ST 的上市公司;刪除控制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對全部財務變量按照5%分位數進行winsorize 處理,篩選后總共獲得23788個公司年度樣本數據。文章所使用的數據涉及兩大類,其中企業財務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其它宏觀層面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對樣本企業進行非平衡面板的多元回歸分析時采用Stata15 軟件進行。
四、實證分析
1.基本回歸結果
文章所選用的樣本數量較大,鑒于微觀企業之間的差異性顯著,在模型回歸分析中采用穩健標準誤的方式進行緩解。表2 數據為分別基于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基本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_LP)是根據LP 法測算得來。列(1)、(3)、(5)顯示在三種模型中解釋變量財政支出分權(Fde)的一次項的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為顯著的負值,二次項的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為顯著的正值,這表明財政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是顯著的且非線性的。伴隨著財政分權程度的增加,最初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處于下降的趨勢,當財政分權程度超過一定的閾值時,二者這種負相關關系得到轉換,財政分權程度的增加會帶動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表明財政支出分權(Fde)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_LP)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U”型效應。列(1)、(3)、(5)中解釋變量政府競爭(Gc)的一次項的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為顯著的正值,二次項的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為顯著的負值,表明政府競爭(Gc)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_LP)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效應,適度的政府競爭水平有利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列(2)、(3)、(4)報告的是將財政收入分權(Fdr)納入到三種模型中估計得到的結果,從回歸結果來看,雖然各個變量的估計系數有所變化,但是其方向和顯著性等特征沒有改變,即財政收入分權(Fde)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_LP)之間的正“U”型效應和政府競爭(Gc)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_LP)之間的倒“U”型效應非常顯著。列(1)、(3)、(5)中財政支出分權和政府競爭的交互項(Fde×Gc)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財政支出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受到政府競爭的約束,政府競爭能夠平抑財政支出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影響。列(2)、(4)、(6)中財政收入分權和政府競爭的交互項(Fdr×Gc)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財政收入分權與政府競爭之間的交互作用明顯,且政府競爭減弱了財政收入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效應。

表2 基本回歸結果
2.穩健性檢驗
在基本回歸結果的基礎上,根據LM 檢驗和Hausman 檢驗的結果,接下來的回歸分析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的面板數據估計方法,并采用穩健標準誤的方式來緩解異方差問題。
(1) 不同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方法的穩健性檢驗
變換不同測算方法對樣本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并將測算結果分別進行替換回歸分析:根據Olley 和Pakes(1996)提出的OP 法,其核心思想是把公司的投資水平作為生產率的代理變量,OP 方法對數據要求比較高,觀測值缺失較為嚴重,因此對于缺失值的處理,參照連玉君(2012)的做法采取用企業中間投入代替缺失的投資;Ackerberg 等(2015)針對OP 法和LP法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正方法(ACF 法),旨在克服OP 法、LP法在第一步估計可能產生的多重共線性問題;Wooldridge(2009)提出了基于GMM 的一步估計法,同樣對OP 法和LP 法的估計方法進行了改進,該方法(WRDG 法) 克服了ACF 法提出的在第一步估計中潛在的識別問題,在考慮序列相關和異方差的情況下,能夠得到穩健標準誤。文章也一并用OP 法、ACF 法、WRDG 法這三種方法測算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并將其作為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表3 匯報了穩健性檢驗的結果,所得結論與上文基本一致。

表3 不同測算方法的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2) 處理內生性問題
鑒于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關系和遺漏變量等問題,對于潛在的內生性問題處理主要采取以下兩種方法:一是前文基本回歸中被解釋變量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為當期數值,接下來用t+1 期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與t 期的解釋變量再次進行回歸,所得結論與上文一致;二是為了緩解由于反向因果、遺漏變量等問題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文章選擇通過系統GMM方法做進一步的回歸分析,所得結論與上文一致。
(3) 分位數回歸
為了增加前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進一步采取分位數回歸分析的方法,分別選擇10%、25%、50%、75%、90%五個代表性的分位數點,回歸結果顯示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等關鍵變量的估計系數大多都很顯著,且系數的正負值方向與基本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五、進一步研究
1.不同區域
我國各地區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平衡現象,經濟發展水平從沿海至內陸呈現出逐漸遞減的態勢,同時,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差異明顯且在不斷發生變化,東部地區第三產業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低端產業逐漸向中西部進行轉移。鑒于此,文章根據國家統計部門關于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劃分①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進一步研究財政分權、政府競爭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是否具有區域異質性問題。表4 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東部地區財政分權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保持顯著的正“U”型關系,政府競爭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財政分權與政府競爭的交互項也與基本回歸結果保持一致。然而,這一特征在中西部地區表現的并不是顯著,且部分關鍵變量在估計系數的正負值方向上也不一致,說明財政分權、政府競爭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

表4 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分組回歸結果
2.不同行業類型
魯桐和黨印(2014)等學者著眼于企業的生產模式和研發重點,運用聚類分析的方法將上市企業分別歸類于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文章參照此種行業歸類標準,進一步分析財政分權、政府競爭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在不同類型的行業上的表現。回歸結果見表5,總體上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分組回歸結果與基本回歸結果相同,財政分權、政府競爭和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U”型效應顯著,而這種“U”型效應沒有體現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間,可見其行業異質性明顯。
六、結論及建議
文章基于我國財政分權和政府競爭的制度框架下,研究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所受的影響。首先選取CSMAR 數據庫中2007—2018年滬深兩市A 股市場的企業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分別通過OP 法、LP 法、ACF 法、WRDG 法測算了28153個企業樣本的全要素生產率。接著分析探討了財政分權、政府競爭框架下地方政府行為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可能產生的促進和抑制效應,進而將財政支出分權、財政收入分權、政府競爭和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等變量引入模型通過實證分析獲取經驗證據。研究發現:財政分權、政府競爭與企業生產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具有顯著的“U”型效應特征,其中財政分權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顯著正“U”型關系,政府競爭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顯著倒“U”型關系;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之間存在交互作用,政府競爭能夠平抑財政支出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作用的邊際貢獻,減弱財政收入分權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作用的邊際貢獻。文章還通過實證檢驗、替代變量以及分樣本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的結果依然穩健。

表5 基于不同行業類型的分組回歸結果
基于文章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與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明確有利于其高效率的開展地方治理活動,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同時要進一步完善省級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將財政分權的正向經濟效益更大規模的釋放。
第二,良性的政府競爭有利于各地區之間的“比學趕超”,在競爭中求得進步,但必須掌握好政府競爭的評價標尺,“唯GDP 增長論”的觀念若長期存在則不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第三,地區發展水平的扭曲可能是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不高的影響因素,政府在競爭的同時,更應該開展經貿、人才、技術的往來交流,同時最大限度的降低地方保護主義,并防止企業與政府保持過高的關聯度,防止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
第四,財政分權下政府的競爭需是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的競爭模式,經濟發展以提質增效為重點的理念和標尺應該被地方政府一以貫之的踐行下去,有利于企業以至全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