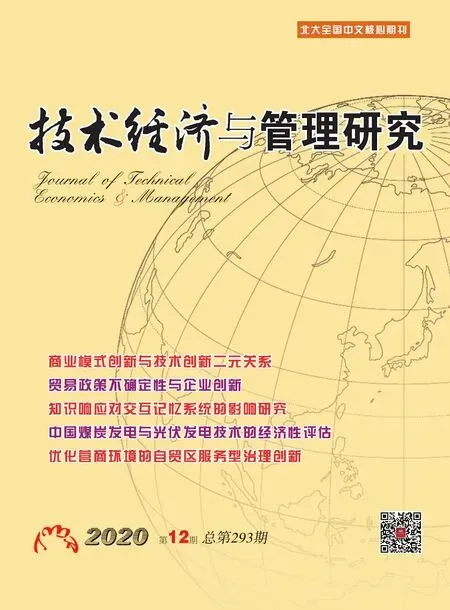基于因子分析法的A 市農村地區扶貧績效評估實證分析
郭興華
(南陽理工學院團委,河南 南陽473004)
現階段,我國自上而下高度重視扶貧工作,動員組織社會各界力量有序參與,精準發力,各項工作快速穩步推進,成效顯著。文章通過運用因子分析法進行評估,可以有效的找出對于貧困戶扶貧及脫貧效果影響程度高低的相關指標因子,并對一個地區前期扶貧工作開展情況進行反饋,對于各級政府組織以及相關扶貧主體當前和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安排提供評判標準,明晰在扶貧實施過程中,工作實施效果情況,從而助推下一步扶貧工作的開展。
一、文獻綜述
1.國外的研究概述
Skoufias 等(2001)采取的有針對性的方法對墨西哥健康教育和營養項目進行評價,評價要點是項目目標實施情況和相較于其他方案,該項目對減貧的效果的優劣。Sanchez-Lopez,Ramiro等(2012)在研究扶貧工作過程中,對其涉及的人權、性別平等、環境問題、社會價值等“跨學科問題”進行績效評價,通過MACBETH 多準則方法與傳統項目評價方法相結合,評價農村發展計劃建設項目,克服了項目評估操作困難的時間難以分離等問題。Notten&Geranda(2016)探析收入轉移對于收入貧困和物質貧困的效果時提出,不同的貧困個體的貧困指標存在不一致性,多維的貧困指標間的相互關系有助于項目評估的有效性。Buyukozkan&Giulcin 等(2017)運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考慮經濟可行性以及自然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基礎上,對能源扶貧項目的績效進行評價。采用多目標決策方法(MCDM)、層次分析法(AHP)和VIKOR 算法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
2.國內的研究概述
李菁等(2006)提出應從項目可持續性、促進社區發展和目標群體發展三個維度進行小額信貸的扶貧績效評價,并在三個維度設立了11個具體的指標,構建了多維的評價體系。許新強等(2009)提出扶貧資金績效評估應以結果為導向,評估的流程設計非常重要,基于貧困狀況的不同,在績效評估的層級和制度安排上要有體現,評價指標體系主要從基礎設施、社會公益、生產發展、政策制度和科技扶貧等方面設置。孫璐(2015)運用管理生態學思想,采用描述性評價方法,形成了更為有效的基期績效評價模型,將因子分析與有序Logit 回歸相結合,評價扶貧對象;采用AHP 層次分析法(AHP)、TOPSIS 評價模型和熵權法對項目的扶貧績效進行評價。邢慧斌(2015)提出在宏觀層面關注扶貧績效的同時,更多的應從微觀層面具體關注到扶貧的直接受益者,即貧困個體在旅游扶貧過程中的參與度和獲得感。李延(2016)對于如何克服扶貧績效評估的三大難點,以更好地體現公平性,解決識別精度不夠、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通過界定清楚政策彈性,考評扶貧的工作損失等來較好的體現出扶貧效率。丁輝俠等(2017)構建了包含基本保障、脫貧效果、幫扶滿意情況在內的三個一級指標,涉及到4個維度的16個三級指標,對脫貧成效進行了評估。
3.評述
綜上可知,無論是在宏觀層面,亦或微觀視角,扶貧績效評估的研究都是系統科學的,成果較為豐碩。但是,在評估資源投入的同時,如何體現被幫扶對象的認可度和滿意度是值得探討的,這正是文章進行分析探討的重點。
二、構建績效評估指標體系
1.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數學模型
設研究對象為P,而且P 可能存在具有相關關系的觀測變量為X=(X1,X2,X3,…,Xp),其均值向量為E(X)=0,Xp為原變量信息;設F=(F1,F2,F3,…,Xm)為研究對象為P 提取的新的因子變量信息,且m≤p,其均值向量E(F)=0。另外,Xi含有特殊因子εi(i=1,2,…,p);ε=(ε1,ε2,ε3,…,εp)代表的是從初始變量中提取的新因子變量所無法表達的剩余信息,也稱之為殘差信息。三者之間的線性函數關系表示如下:

2.構建扶貧績效評估指標體系
為了更好的反映精準測度貧困個體、實施相對應的扶貧路徑,體現扶貧活動的效果,文章構建能夠較好的體現績效評估的效率性和有效性構建指標體系,具體分為產出類指標、有效性指標、過程性指標。
(1) 產出類指標
文章選取了包括是否不愁吃、是否不愁穿、教育費用總支出、家庭總收入、日常生活的總支出、住房滿意度等指標,該部分指標能夠較好的反映貧困個體貧困狀況得到改善情況;該六項指標均為正向指標。
是否不愁吃主要是指貧困個體的在生活中是否能夠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飲食要求。是否不愁穿指貧困個體在生活中是否能夠滿足隨著天氣季節的變化所需的衣物。教育費用總支出包括貧困戶所有家庭成員為了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能所支付的費用。家庭的總收入包括種植業收入、果林經營性收入、其他農業收入、養殖業收入、其他家庭自營經營性收入、外出務工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性收入等。日常生活的總開支主要是指用于滿足家庭成員生存生活所需的食品、食物等所需的支出。住房滿意度是指貧困個體有效的居住面積、住房條件所構成的貧困個體的滿意度。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 扶貧績效評估指標匯總表
(2) 過程性指標
文章從貧困個體的視角對于村小組、村委會對于扶貧個體的測度和認定,以及扶貧資金的使用是否進行民主評議和公示公告。民主評議落實情況反映了對于貧困人口測度的標準、程序執行落實情況,貧困人口退出是否按照相關的的標準、程序辦理。
(3) 有效性指標
文章選取貧困個體對于扶貧工作責任人和幫扶路徑的滿意程度為指標。對幫扶工作是否滿意包含了幫扶責任人對家庭貧困狀況的了解程度、到貧困戶走訪調研的次數等具體工作內容的反饋。選取對幫扶是否滿意這一指標,通過該指標讓扶貧的主體——貧困個體對圍繞其進行的扶貧工作進行立體客觀的評價。
在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體現出讓貧困個體充分參與的理念;在理論上構建貧困個體及民眾表達權利的途徑,體現服務型政府的理念。
(4) 扶貧績效評估指標的匯總
結合前文分析,共選取了涉及扶貧的產出類指標、過程性指標和有效性指標三類11個指標,如表1 所示。
從表1 可以看出,11個指標除了醫療支出和是否承擔得起一般醫療費用外,均為正向指標。其中教育費用支出包括家庭子女上學的各種費用以及家庭其他成員為了提高就業能力參加的各種教育培訓所需的費用,該項費用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家庭的生計能力提高的可能性越高,對于其內生動力的增強有著正向顯著作用。
三、實證分析: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扶貧績效評估——以A市為例
1.數據來源與數據整理
(1) 數據來源
A 市是集革命老區、重點移民區和傳統農業區于一體的扶貧重點地區,包括兩個行政區,分別是Aa 區、Ab 區;還有10個縣分別為:Ac 縣、Ad 縣、Ae 縣、Af 縣、Al 縣、Aj 縣、Ag縣、Am 縣、Ah 縣、Ai 縣;兩個開發區分別為Ak 區和An 區。依照2016年6月30日市扶貧辦提供的數據,A 市有貧困人口44.68萬,16.37萬戶;扶貧及脫貧任務十分艱巨。文章績效評估實證分析所用的數據為2016年7月A 市入戶調研收集的的評估數據。
(2) 數據整理
依據上文選取的指標,對數據分類整理。
首先,依據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對選取的變量的原始數據數據進行處理,使正向指標和逆向指標二者之間具有可比性,從而保證分析研究的可行性與客觀性。
文章所選的逆向指標進行處理的公式是:

即對醫療支出和是否承擔得起一般醫療費用這兩項指標進行導數化處理。
其次,由于選取的指標表示單位和數量級存在較大差異,相互之間缺乏可比性,文章運用標準化處理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另外,文章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所運用的軟件為SPSS.24.0。
2.數據的檢驗
針對整理好的數據,運用KMO 測度和巴特利特球體檢驗來判斷樣本數據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
Kaiser(1974)關于KMO 的值的大小所反映的做KMO 測度的效果的論斷如表2 所示。

表2 KMO 取值做測度的效果說明表
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則是對相關系數矩陣的行列式進行測算,求出統計量。如果得出的統計量比較大,并且相應的概率值小于之前所設定的顯著性水平,這時就應該拒絕零假設。這時可以判定其相關系數并不是單位矩陣。同時,充分說明了原始變量相互間是具有相關性的,可以用因子分析法進行分析。反之則不然。
KMO 測度和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由表3 可知,針對上文選取的變量指標進行去檢驗,KMO 測度結果為0.614,該值處于0.60~0.69之間,根據Kaiser 的判定,能夠做因子分析。另外,巴特利特球體檢驗近似卡方觀測值為106.827,顯著性為0.000,近似為零,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顯著,可以做因子分析。

表3 KMO 和巴特利特檢驗結果
3.提取因子
文章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子提取,根據特征值大于1 的要求提取因子。選取變量因子分析的初始解如表4 所示。
通過表4 可以看出,十一項指標中共同度均大于0.8 的有六項,大于0.6 小于0.8 的有四項,是否不愁穿指標的提取度為0.574,說明原始變量方差中能被共同因子解釋的部分較大,原始變量的共同度比較高,原始變量的信息能夠較多的被保留。

表4 公因子方差
通過表5 可以看出,主成分1 的特征值為5.029,說明該因子是對扶貧績效評估影響最大的主成分;主成分2 的特征值是2.581,其是與主成分1 不相關的且對扶貧績效評估影響處于第2 重要的;主成分3 的特征值是1.244,其對扶貧績效評估的重要性位居第3,且和主成分1、主成分2 均不相關;以此類推。

表5 總方差解釋
其中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有3個,并且該3個因子的累積貢獻率達到了80.491%,說明所有原始變量的信息能夠被這3個因子較好的代表,所以提取的公因子數量為3個。
通過圖1 可以看出,前3個主成分特征值所形成的折線的斜率較大,而后面的主成分特征值所構成的折線較為平緩,斜率較低。充分說明對原始變量能夠很好的給予解釋的是解釋貢獻率較大的前3個因子,其余的8個因子解釋貢獻率較低;說明提取前3個因子是比較適合的。

圖1 碎石圖
4.因子的識別與命名
表6 中所表述的荷載系數表明了公共因子與原始變量之間的關系,但是從中很難明顯看出某一變量對各公共因子的相關性。基于此,運用SPSS.24.0 軟件中的凱撒正態化最大方差法進行旋轉,使系數在1 和0 之間進行兩極分化,以找到公共因子,并明晰每個公共因子的實際含義。旋轉得到的結果如下表7 所示。
從表7 可以看出,第1 主因子與變量X1、X2、X3、X6、X7、X8高度正相關,對這六項指標荷載量比較大。這六項指標主要反映了貧困個體在基本生活條件的保障,將第1 主因子命名為生活境況,用其來很好的反映貧困個體生存生活條件的改善程度。

表6 成分矩陣a
第2 主因子對變量X9、X10、X11正相關程度較高,它主要是從貧困個體對扶貧工作的滿意程度進行主觀評判,貧困個體的認定、扶貧工作的開展是否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將該三項指標的公因子命名為貧困個體對扶貧滿意度。

表7 旋轉后的成分矩陣a
第3 主因子對變量X4、X5的荷載較大,X4、X5分別指醫療疾病總支出和教育費用總支出。教育費用總支出能夠很好的反映出貧困家庭為了提高其擺脫貧困和走向富裕的能力而進行的投資。醫療疾病總支出能夠較好地反映出為了治愈有勞動能力的貧困個體進行的投資,同時為了使缺乏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擺脫疾病,以在未來減少自身家庭的損耗性支出。因此把第3 主因子命名為可持續發展能力。
3個公因子命名情況見表8。

表8 公因子命名一覽表
5.因子得分
文章運用凱撒正態化最大方差法得到旋轉后的因子成分得分系數矩陣,具體如表9 所示。

表9 成分得分系數矩陣
設F1、F2、F3依次代表上文提到的第1個公因子、第2個公因子和第3個公因子,依據成分得分系數矩陣表9 可以得出3個公因子的計算模型為:

為了更好的測算出每個縣區在各公因子上的扶貧績效,將經過標準化處理之后的原始數據代入上述公因子計算模型,計算出各縣區在每個公因子上的得分排名如表10 所示。

表10 各縣區公因子得分排名
(1) 單項公因子得分排名分析
第一,生活境況因子得分排名分析。從表10 可以看出,在該因子得分中,Ah 縣、Aa 區、An 區得分相對其他縣區來說比較高,分別為1.42856、1.40525、1.32293;其次是Ak 區,得分為1.01132,排名第三的An 區高出排名第4 的Ak 區0.31161;總體來說,該4個縣區通過前期的扶貧工作,貧困個體的生活境況較其他縣區來說比較好。另外,在該方面做得較好的還有Al 縣、Am 縣和Ad 縣,得分分別為0.37768、0.18184、0.05244。其他縣區得分均為負值。
第二,扶貧個體滿意度因子得分排名分析。從表10 可以看出,在該因子得分中,Af 縣排在第一位,得分為1.46128,高出排名第二的Ac 縣0.60685; Ab 區排名第三位,得分為0.7964。說明在所有縣區中間,無論是幫扶責任人履行職責情況,還是扶貧路徑的實施,該三個縣區的貧困人群對扶貧工作滿意度較高。其次,An 區、Ak區、Ad 縣得分也比較高,分別為0.69674、0.61133、0.60354。另外,排名比較靠后的三個縣是Ae 縣、Aj 縣、Am 縣,得分均為負值,分別為-0.91835、-1.61106、-2.1449。排名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說明該地區貧困人口對于本地區結合自身進行的扶貧工作開展情況的滿意程度的高低。
貧困個體對于扶貧工作滿意度的高低盡管是主觀評判,但是其涵蓋的綜合因素較多,諸如對自身貧困原因的認定、其他貧困人口的認定、幫扶的態度、幫扶的盡責情況、扶貧路徑的有效性、自身脫貧的效果等。所以該項因素一定要引起各部門的重視,通過該因子的評估,查找自身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并進行改進。
第三,可持續發展能力因子得分排名分析。從表10 可以看出,在該因子得分中,Ae 縣和Af 縣排名為第一和第二,得分較高,得分分別為:1.65618、1.45779;從長遠來看,該兩個縣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與脫貧動力較強,貧困人口的整體內生動力較強,在短期的未來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Am 縣、Ad縣、Ab 區得分相對較高,分別為:0.71463、0.62265、0.60546;該三個縣區的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相對來說比較強。其他縣區該因子得分較差,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地區貧困人口在扶貧過程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高較為緩慢,這就制約其短期內擺脫貧困的速度和效率。充分說明,各縣區之間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性。
(2) 公因子得分橫向比較
該部分的比較以公因子得分的正負作為衡量標準。從表10可以看出,在三個公因子得分之中,全部為正值的只有Ad 縣;說明該縣的扶貧工作在這幾項指標上是全面有效開展,并且均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得分為兩個正值的有:Ah 縣、Aa 區、An區、Ak 區、Am 縣、Ab 區,該順序沒有先后排名;說明該六個縣區在某兩個公因子上扶貧效果是較好的,但是都在某一個因子上存在較大的改進和提升空間,是需要今后改變和努力的工作方向。得分只有一個正值的是Al 縣、Ae 縣、Ai 縣、Ac 縣,說明該四縣均有兩個公因子的扶貧績效處于較差狀態。三個公因子得分全部為負值的有Ag 縣和Aj 縣,說明這兩個縣在研究設定的扶貧績效評估的各項指標上工作成效不明顯,扶貧工作整體績效較差。
(3) 各縣區扶貧績效評估綜合得分
為了進一步測算出該結果,對各縣區的綜合扶貧工作進行比較與評價,需要計算出各公因子的綜合得分F,計算方法為各公因子得分相應的權重進行加總,各公因子的權重為提取公因子時的方差百分比,運用這種方法設置權重是較為客觀的。同時,將3個公因子的累計貢獻率80.491%設定為1,進而測算出第1 公因子、第2 公因子、第3 公因子的權重分別為:0.4859、0.3230、0.1911。據此,得出各縣區扶貧績效評估綜合得分計算函數為:

通過測算,得出各縣區扶貧績效評估結果如表11 所示,通過該表可以看出各縣區的綜合排名情況,排在前四位的是An區、Aa 區、Ah 縣和Ak 區,得分分別為:0.806044、0.739666、0.707442、0.640854,其次是Af 縣和Ad 縣,得分均為正值,分別為:0.387464、0.339412;其他縣區得分均為負值。排在后兩位的是Aj 縣和Ac 縣,得分為-0.58808、-1.22979。
四、實證分析結論與建議
1.結論

表11 各縣區綜合得分及排名
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其進行績效評估是可行的,文章所構建的扶貧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是科學的,具有較強的適用性。針對研究評估的內容,得出了各縣區扶貧績效評估的結果,并對其進行了比較分析。該結果對于各縣區今后的扶貧工作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各縣區在扶貧工作開展過程中,必須重視對貧困個體生活境況的改善;在此基礎上,提高貧困家庭有勞動能力人群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要切實提高貧困人群對扶貧工作的滿意程度,三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2.建議
(1) 各縣區結合評估結果,進一步做到精準施策
根據績效評估的結果,各縣區要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對于本地區扶貧工作中的各維度進行反思與總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漏洞與不足,通過政策的完善、精準投入資金,強化人力物力配備,以改善貧困個體的生活境況為基礎,注重培養有勞動能力人群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探尋適合農村貧困群體的工作方式方法,掃除阻礙貧困個體成長、發展、脫貧、致富的障礙,實現本地區既定的脫貧目標。
排名靠前的縣區是值得其他縣區學習和借鑒的樣本。但是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視角,上述研究分析只能夠作為各縣區扶貧工作績效的重要參考。
(2) 充分考慮評估對象的差異性,做到精準評估
首先,明確評估對象和評估內容,基于評估對象時間、空間、貧困歷史狀況等客觀存在的差異性,因地而異的構建科學合理有效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其次,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評估方法的選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復醞釀,同時要充分吸納同行專家、學者意見建議。另外,在評估過程中,實事求是、尊重現實,科學把握區域間、地區間、縣域間的差異性。通過評估能夠查擺不足、發現問題、改進措施,進一步推動今后的工作有力、有效開展,最終做到精準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