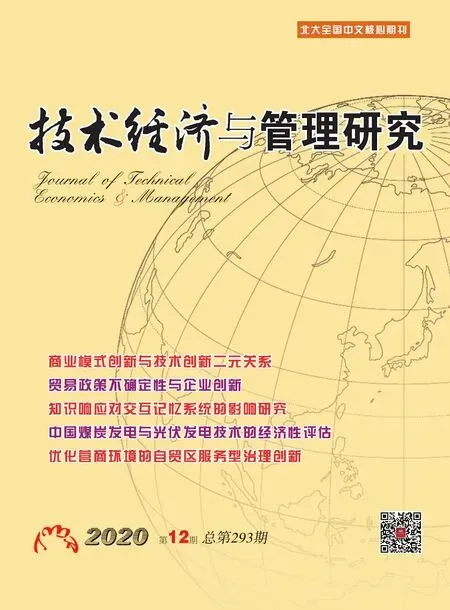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對就業的影響研究
廖戰海
(廣西財經學院,廣西 南寧530007)
一、引言
隨著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交通成本及監管成本日益降低,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特別是通過價值鏈分工的方式開展貿易也日漸繁榮。國際貿易實際上通過商品的流動替代要素的流動,引起要素供求的變化,從而對要素的價格產生影響,因此全球化會給勞動力市場帶來沖擊。外包作為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載體,實現了生產的分割,本國將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環節,比如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到國外,必然會對一國的就業以及收入分配產生深遠的影響。
最早關于外包與就業的文獻,大多關注的是發達國家外包對其就業的影響(Anderton 和Bernton,1999;Amiti 和Wei,2004)。之后的研究主要分兩大類:一是利用行業數據研究。首先從發包國的角度展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外包對就業起抑制作用(陳仲常、馬紅旗,2010)[1];另一種觀點認為外包拉動了就業增長,原因是規模效應抵消了替代效應(徐毅、張二震,2008;呂延方、王冬,2011)[2]。其次從承接國的角度,一般認為承接制造外包可以拉動就業,而且會有行業差異以及來源國的差異(王俊、黃先海,2011;李占國等,2014;馬晶梅等,2015)[3]。當然,也有學者指出服務外包對就業具有促進作用,而物質外包對就業則沒有顯著影響(肖芍芳、王俊杰,2012)。二是利用企業數據研究。Harrison 和McMillan(2011)[4]指出,離岸外包對母公司就業的影響顯著受到離岸外包動機以及外包目的地的影響。Pierce 和Schott(2016)[5]研究表明,由于消除了政策的不確定性,大量的美國企業將中間品生產外包給中國,是2000年以后美國制造業就業突然急劇下降的原因之一。Bandick(2016)[6]認為,離岸外包地點的選擇會對低技能就業產生顯著影響。Tamayo 和Huergo(2016)[7]利用2004-2011年西班牙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數據,估計出離岸服務外包和技能型就業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Andersson 等(2017)[8]利用1997-2002年瑞典企業數據,研究了外包如何影響企業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
國內利用企業數據考察外包對就業影響的研究并不多見。因此,文章利用中國企業數據,進一步論證了外包與就業的關系,具體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模型和假說,基于Melitz(2003),Hsieh 和Klenow(2009)與Hummels 等(2014)的研究,構建了外包對企業就業影響的理論模型;第三部分為計量模型構建和數據說明;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與分析;最后是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理論框架
文章在Melitz(2003)異質性企業理論的基本框架下,引入Hsieh 和Klenow(2009)模型中的嵌套生產函數,借鑒Hummels 等(2014)在生產函數中刻畫企業外包的方法,構建了外包對企業就業影響的理論模型。與之不同的是,文章不考慮低技能勞動力和高技能勞動力的劃分。
1.嵌套生產函數設定
借鑒Hsieh 和Klenow(2009),研究假定經濟體中具有三層嵌套的生產函數。
第一層生產函數假定為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示為:

其中Y 表示經濟體的總產出,YS表示部門S 的總產出,θS為部門S 在經濟體中的份額。由于式(1)為經典的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那么當假定產出市場是完全競爭時,總產出的價格給定為:

其中PS為部門S 產出的價格。那么,求解式(2)的利潤最大化問題,可得部門S 產出的需求函數:

第二層生產函數假定為CES 函數。于是,部門S 的產出可表示為:

其中YSi表示部門S 的差異化種類i 的投入數量,σ 為差異化種類之間的替代彈性。由于式(4)為CES 生產函數,因而部門S 的價格函數給定為:
其中PSi為差異化種類i 的價格。借鑒Melitz(2003)的做法,可以得到差異化種類i 的需求函數為:
第三層生產函數也假定為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與Hummels 等(2014)類似,生產差異化種類的企業利用勞動和外包產品進行生產。不同的是,此處不考慮低技能勞動力和高技能勞動力的劃分,以及資本投入。生產差異化種類i 企業的產出表示為:


其中ASi表示企業i 的生產率,OSi表示企業的外包量,LSi表示企業的勞動力人數。
2.比較靜態分析
假定企業生產需要投入固定成本f,企業外包也需要支付固定成本fo。那么企業i 的利潤表示為:

其中W 表示工資,γ 表示外包產品的價格。求解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問題,可得:

利用式(9)對外包量OSi求導,得到:

因此,文章得到假說:外包會增加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
由于文章是從進口中間品的角度來界定外包,因此根據現有中間品進口文獻,文章認為外包會通過外包產品質量、外包產品種類數目和外包產品技術溢出影響企業就業。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
1.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和假說,為了實證考察企業層面外包對就業的影響,文章設定以下回歸模型:

其中,下標i、t 分別表示企業和年份,employmentit表示企業i 在t年的就業人數,offshoringit表示企業i 在t年的外包程度,Xit表示其他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外資比重、年齡和負債比,εit代表誤差項。
文章的核心解釋變量是企業的外包額,因而控制變量的選取原則是控制變量會影響企業的就業,同時該控制變量又與企業的外包相關。這是因為如果控制變量與外包不相關,那么理論上可以證明,遺漏該控制變量不會影響回歸系數β1的估計值。規模越大的企業可能會雇傭更多的工人,同時也可能需要承擔外包的成本。外資比重越高的企業可能會使用更少的勞動力,同時也更有可能進行外包。成立越久的企業可能會擁有更多的工人,也越有可能進行外包。金融狀況越好的企業可能會雇傭更多的工人進行擴大生產,同時也更有能力支付外包的先期費用。
文章的被解釋變量就業人數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企業規模由企業的銷售額度量,其中企業的銷售額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外資比重定義為外國資本與企業資本之比,其中外國資本和企業資本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參照簡澤等(2014)與毛其淋(2015)的做法,企業年齡采用企業當年年份與建立年份的差進行衡量,其中企業建立年份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負債比定義為企業負債與企業資本之比,其中企業負債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2.外包的測度
目前,國內外研究中外包測算指標主要有四種:一是用中間品進口額與總進口額的比值(Imported Inputs in Total Imports)來衡量;二是利用企業中間品進口與企業總投入的比值來衡量(Imported Inputs in Total Inputs);三是運用企業進口的中間品與企業總產出的比值來衡量(Imported Inputs in Gross Output);四是利用垂直專業化指數來衡量(Vertical Specialization)。文章主要采用第一種方法來測度外包,即利用中國海關數據庫中企業中間品進口額來衡量企業外包。進一步,中間品進口額并不一定都屬于外包,為了減少誤差,文章借鑒Kurz 和Senses(2016)的做法,采用同一HS4 分位行業下的制造業中間品進口額來衡量企業外包。例如,企業所屬的HS4 分位行業為“2467”,那么在企業所進口的中間品中,只有同屬于該HS4 分位行業的中間品才被計算為外包。
3.外包的工具變量構造
根據Yu(2015)的研究,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會對企業的進口決策產生很大的影響,一般情況下,企業的就業人數是企業生產率的體現之一,同時企業的中間品進口受其進口決策的影響,意味著企業的就業人數可能間接影響企業的外包,這種反向因果關系產生了內生性,可能會使模型的估計結果出現不一致。文章借鑒Feng、Li 和Swenson(2016)的方法,使用企業層面的中間品進口關稅作為企業外包的工具變量,以解決文章的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指標構造如下:

其中,h 代表HS6 分位產品,Ωit代表企業i 在t年進口的產品集合,τht代表產品h 在t年進口關稅率,vαih,aver代表企業i在樣本期間產品h 的平均進口額。權重αih,aver=vαih,aver/∑h∈Ωitvαih,aver代表樣本期間產品h 的進口占企業i 中間品總進口的平均比重,為固定權重。固定權重可以避免貿易權重和中間品進口關稅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基本回歸分析
表1 給出了企業外包對就業影響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在每一列中逐漸加入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可以看到,企業外包的系數符號一直為正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同時數值大小也逐漸穩定并趨于一致。這意味著企業外包越多,其就業人數也越多,可能是因為當企業外包越多時,企業的生產成本下降,增加了企業效益,從而促使企業擴大規模招收了更多的工人。
為了排除中間品關稅是企業外包弱工具變量的可能性,在表1 中加入了其他檢驗統計量進行識別。因為沒有肯定的理由去相信誤差是同方差的,所以文章使用了異方差-穩健Kleibergen 和Paap(2006)檢驗統計量。Kleibergen-Paap LM 統計量表明可以拒絕內生回歸變量無法識別的零假設,然而,這說明工具變量可能只與內生回歸變量弱相關。Stock 和Yogo(2005)列出了同方差情況下,為了檢驗弱工具使用的Cragg-Donald(1993)的F 統計量臨界值。因為文中沒有假設異方差,所以報告了異方差-穩健Kleibergen 和Paap(2006)Wald rk F 統計量。盡管異方差情況下適當的臨界值在文獻中沒有列出(Mikusheva,2013),但通常的做法是與Stock-Yogo 臨界值進行比較。
考慮到弱工具變量的問題,文章還使用了Anderson-Rubin(1949)Wald 檢驗。可以看到,Kleibergen-Paap LM 統計量顯示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顯著相關,而且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統計量與Anderson-Rubin Wald F 統計量也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說明文章使用的工具變量可用。

表1 外包與企業就業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2.傾向得分匹配分析
傾向得分匹配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較同一時期下,有外包企業和沒有外包企業的就業人數差異。具體地,基于企業是否外包,就業人數差異計算公式為:

其中,Oit是一個虛擬變量,Oit=1則表示企業在t年有外包業務,否則為0。代表當一個企業有外包業務時在t年該企業的就業人數;則代表當一個企業沒有外包業務時在t年該企業的就業人數。
(1) 得到傾向得分
擁有特征Xit的企業i 進行外包的可能性是:

其中,Xit是影響企業是否進行外包可能性的一些變量。文章中的這些變量包括企業規模、外資比重、企業年齡、負債比、出口額、資本、生產率和加成率等。文章使用Probit 模型來估計企業是否進行外包的回歸,表2 給出了Probit 模型的回歸結果。

表2 企業是否進行外包的影響因素
(2) 匹配
文章用獲得的傾向得分確定每個企業進行外包可能性,之后使用分數找到每個外包企業對應的非外包企業。因為傾向得分是連續的,所以很難對每個外包企業找到有相同傾向得分的非外包企業。選擇非外包企業有以下標準,比如一對一匹配、最鄰近匹配、半徑匹配及核匹配。文章使用一對一匹配的標準來匹配每個外包企業與非外包企業,目的是為每一個外包企業都找到一個具有類似傾向得分的非外包企業。
(3) 平衡檢驗
文章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有兩個重要假設:公共支持假設與獨立假設。因此文章通過檢驗匹配結果來檢查是否滿足這兩個假設。公共支持假設意味著文章需要基于傾向得分,為每個外包企業找到一個非外包企業,所以文章刪除了所有不符合這個假設的觀測值。
獨立假設要求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考慮匹配變量時沒有顯著差異。這種情況下,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就業人數差異只是因為企業是否進行外包。因此文章檢測了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匹配變量的平均值和偏差,結果如表3 所示。可以看到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八個匹配變量的偏差在-2.0%到6.8%。Smith 和Todd(2005)認為偏差越小,匹配結果越好。如果偏差大于20%,匹配則是無效的。結果表明文章的匹配是有效的。文章也檢驗了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八個匹配變量的平均值是否相等。從t 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不少匹配變量都是不顯著的,這表明處理組企業和對照組企業中這些變量的平均值差異不顯著,從而從另一方面說明匹配的有效性。

表3 處理組與對照組的變量對比
(4) 傾向得分匹配的結果

表4 傾向得分匹配結果
3.外包承接國特征和企業異質性分析
(1) 外包承接國特征的影響
這一部分仍然基于中間品關稅這一工具變量,通過承接國制度、距離、人均GDP、人口等考察外包對企業就業在不同外包承接國特征下的影響。
第一,外包承接國制度的影響。
表5 中第(1)到第(4)列分別代表知識產權、商業自由化、腐敗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度四種制度衡量指標。具體地,外包與外包承接國知識產權制度的交乘項系數不顯著,與其他三種制度的交乘項系數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當承接國的商業自由化、腐敗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度等制度越好,在承接外包時的規模也會越大,因此相應地減少了更多的國內企業就業;而一般認為,承接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是企業進行外包決策的關鍵因素,因素影響尚不顯著,有待進一步驗證。

表5 考慮外包承接國制度時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第二,外包承接國收入的影響。
根據表6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企業外包與外包承接國人均GDP 的交乘項系數最開始顯著為正,隨著控制變量的引入,該系數穩定為負并且仍然顯著,說明同收入越高的國家進行外包,越容易導致國內企業就業下降。這可能是因為同高收入國家進行外包的一般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外包費用,即生產成本也相對更高,從而降低了國內企業對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導致就業下降。
第三,外包承接國距離的影響。
根據表7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企業外包與外包承接國和中國之間距離的交乘項系數最開始顯著為負,隨著控制變量的引入,該系數為不顯著,說明外包承接國的距離對進行外包的企業就業沒有顯著影響。
第四,外包承接國人口的影響。
根據表8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企業外包與外包承接國人口的交乘項系數最開始顯著為負,隨著控制變量的引入,該系數穩定為正并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同人口越多的國家進行外包,企業就業增加的越多。這可能是因為人口越多的國家以發展中國家居多,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往往是因為其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從而使企業節約成本、提高利潤,進而增加對相關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促進了企業就業。

表6 考慮外包承接國人均GDP 時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表7 考慮外包承接國距離時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表8 考慮外包承接國人口時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2.企業異質性的影響
文章仍然基于中間品關稅這一工具變量,通過企業規模、生產率、所有制、年齡、所在地區、貿易方式、所在行業等方面考察外包對就業的影響。
(1) 不同企業規模的回歸結果
文章通過企業銷售額衡量企業規模,表9 的第(1)到第(4)列分別表示處于第一分位、第二分位、第三分位和第四分位的企業。再根據表9 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除了處于第四分位的企業不顯著之外,其余均顯著為正,但系數變小。這表明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外包的就業效應逐漸減弱。這可能是因為企業規模很大時,跨國公司不僅僅采取外包的方式,更有可能采取FDI 的方式參與國際分工。

表9 不同企業規模下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2) 不同企業生產率的回歸結果
表10 的第(1)到第(4)列分別表示處于企業生產率為第一分位、第二分位、第三分位和第四分位的企業。根據表10 的回歸結果,除了處于第四分位的企業不顯著外,其余均顯著為正,但系數變小。這說明對于中低生產率企業,外包對就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于生產率非常高的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對于中低生產率企業,外包對企業的利潤增長具有質的影響,從而增加對勞動的需求。

表10 不同企業生產率下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3) 不同企業所有制的回歸結果

表11 不同企業所有制下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表11 的第(1)到第(3)列分別表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再根據表11 的回歸結果,只有當樣本為國有企業時,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樣本期內國有企業的外包規模較小,同時國有企業的樣本量也不多,需要進一步驗證。
(4) 不同企業年齡的回歸結果
表12 的第(1)到第(4)列分別表示企業年齡處于第一分位、第二分位、第三分位和第四分位的企業。根據表12 的回歸結果,在不同企業年齡分位下,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都為正并且顯著。說明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不取決于企業持續經營時間的長短。

表12 不同企業年齡下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5) 不同地區企業的回歸結果
表13 的第(1)到第(3)列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企業。根據表13 的回歸結果,對于東部和中部企業來說,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顯著為正;對于西部企業來說,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西部企業的整體發展水平較低,樣本期間基本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將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外包給國外企業的話,明顯減少了企業生產的產品數量,降低企業勞動力需求。

表13 不同地區企業下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6) 不同貿易方式企業的回歸結果
表14 的 第(1)到第(3)列分別表示純加工貿易企業,既有加工又有一般貿易企業與純一般貿易企業。根據表14 的回歸結果,對于純加工貿易企業和既有加工又有一般貿易企業來說,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顯著為正;對于純一般貿易企業來說,企業外包對就業的影響顯著為負。企業的加成率一定程度上反映生產率,黃先海等(2016)發現加工貿易企業加成率水平顯著低于一般貿易企業,因此加工貿易企業或混合型企業處于較低的生產鏈位置,外包對企業的利潤增長具有質的影響,從而增加對勞動的需求。

表14 不同貿易方式企業下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海關數據庫的匹配數據,從微觀角度研究了外包對企業就業的影響。考慮到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文章選取了中間品關稅作為工具變量,結果表明企業外包對就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次,使用了傾向得分匹配法進一步驗證了外包與企業就業之間的關系。最后,還從外包承接國特征與企業異質性考察了各方面的不同影響。
文章的政策含義是:第一,在全球化和價值鏈分工的背景下,中國以外包的形式參與到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不斷攀升,應該適時進行角色的轉變,從承接國轉向發包國。從研究結論可知,發包并未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反而促進了就業,因此政府應該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發包,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節約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第二,從承接國的特征看,如果外包給制度較好、收入相對較高的發達國家,則有可能會對國內就業造成一定沖擊,因此,應該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建設的契機,不斷深入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分工合作,大力發展外包和服務外包。第三,從企業異質性的考察來看,中小企業以及生產率較低的企業、民營和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型企業都有明顯的就業提升效應,政府應該大力扶持這些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