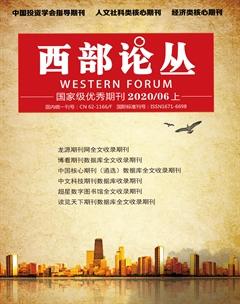文本抽象元理論初探
任敬鵬 王冶廷 葛欣雅
摘 要:文本的抽象元也可以叫做文本的意象,即通過文學文本中最小的意義發生單位的建構來對文本整體的意義發生做出一定闡釋的理論形式。換言之,文本的抽象元理論就是分析意象的結構來闡發意義發生的一條可能的路徑。本文首先將對文本的抽象元進行闡釋,從抽象元理論出發,探究文本元體系的運動機制,而后指出文本的本質——作為元組和組元的文本。
關鍵詞:文學理論;發生學;文學性
一般地,敘事元一般可以呈以下幾種運動方式:即自在運動、排列、組合、連綴,上述的四種運動模式一般認為涵蓋了作家創作過程中思維的運作模式。
首先,那些關乎日常經驗的“無限可分”的物象的自在運動是作家創作的首要對象,是作家生活中那些足以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事物在作家的思維中反映并最終以“敘事元”的形式得到表現的動態進程。論及動態進程,我們有證據指出敘事元的自在運動永遠是動態的,無論是其產生的過程抑或是其作用于敘事元的下一運動形式:排列與組合的過程。
其次是敘事元的排列與組合,時空體理論顯然要求敘事過程中兩方面——時間與空間要素的有機組合,一般地,我們將敘事元在“時間”方向上建構的趨勢稱為“排列”,通俗地來講,敘事元的排列就是文本的時間組織形式:該文學文本在哪一個時間內定向流動?如何對于較長的時間段內另一個較短的時間段的流動進行研究?文學文本時間組織的開頭和結尾在一個相對淺層的作用層上,構成了文本敘事元的“排列”。在定位于敘事元的時間排列進行建構時,更加重要的是作家能動的建構思路以及關于這些構成要件的組織與編排。
其次是“組合”——一般地,組合用以指稱文本意象運動之空間占據性方向上的運動方式。換言之,意象的組合,就是既存的空間在時間序列下的運動。如果說意象的排列是定位于直角坐標系中的橫軸的話,那么意象的組合則是定位于直角坐標系中的縱軸,是文本的歷時性建構。
文本的橫向—歷時性對象與縱向—共時性對象建構起了文本的表義空間,從而將文本的情節要素,或者稱功能性意象的對象置于一個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文本表義域中,這樣,文本的基本結構就相當明顯了,首先是作為情節流動之途徑的——時空體結構,它為文本的情節發生提供一個基本的發生范圍;其次就是情節本身了,它在作家的功能性意象的引導下,有條不紊,先后有序地在途徑中流動著。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提到,功能性意象也是關于情節引導性與決定性的對象,那么能否用以說明——功能性意象就是時空體呢?我們指出,這是不符合邏輯和詭辯的,無數的證據證明,時空體的建構決不能為文本的運行造成什么絕對實質的影響;反而作者的意向——建構情節的那些功能性要素(這里的功能性要素可以理解為作者意向的具象對象)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而將非功能性的時空體與功能性的作者意向相混淆,也實際上是詭辯的。
不過,在時間排列建構理論中,研究者常常會因為他們的對象而感到迷惑,所建構具有流動性特征的對象是什么?我們指出,首先是作為標示對象的,那些本身具有標示作用的詞語,諸如“從前、開始、現在、當時、后來”等;不過在很多現代主義的、先鋒主義的創作中,上述規則就顯得不是那么普適了;我們可以回憶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那些超時空要素的表達、那些剪輯式手法的廣泛運用促生的以集群性要素為支點進行描述的文本等,因而即使那些普適性的規律如何公正、如何精密,那些定位于文本本身的建構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其次是文本的形象體系中的表達形象的一類對象,在哈利澤夫那里,文本的形象體系是那些或積極、或消極地能與文本世界中各類要素發生關系的東西,包括文學文本中出場的那些無個性的“物”、“大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等。而作為具有空間性質的對象“物象”其最根本的特征是關于時間與空間方向上的,作家們也因而能夠通過那些定位于時間與空間的——立體建構的手段對文本的形象進行一定程度的,本質上的組織,在自然哲學上,正如叔本華指出的那樣:“……物質必須將雙方的屬性一并挑起;(因為)在雙方因為各自獨立而不能進一步統一的(那些東西)在物質中必定要被統一。(它們的方式是)將時間方面無實質的飄忽與空間方面的僵硬、不變的恒存統一起來……”;我們可以回想屠格涅夫那篇經典的作品《森林與草原》中那一大段描寫:“天邊漸漸泛紅;白樺林里,寒鴉蘇醒過來,撲棱著翅膀飛來飛去;麻雀圍著黑黑的草垛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天光放亮,小路漸漸顯出形跡,天空愈加亮起來,云朵泛出白光,田野出現綠衣。木屋里,松明吐著紅色的火苗,大門外傳來睡意惺忪的聲音。就在此時,朝霞燃燒起來;天空中出現許多金色的光帶,峽谷里霧氣繚繞;云雀開始展露清脆的歌喉,黎明前的風悄然刮起一輪深紅色的太陽冉冉升起。立時霞光萬道…… ”,那些無生命的東西(小路、天空、松明、朝霞、太陽)與有生命的東西(寒鴉麻雀、云雀),在被稱為“組合”的建構手法中,那些存在著的物質,以相當立體的方式最終在一個時空對象中得到了表達——一方面展現了運用對象本身的無限流動性,從而建構出了一副從天空破曉時向日出“流動”的那一段時間;另一方面則將那些物象與其空間占據性特征的對象有機地結合。
最后則是敘事元的連綴結構,如果說排列和組合分別代表著兩者在“時間”和“空間”方向上進行表達的話,那么意象的連綴一般用以指稱具有時間和空間雙重性質對象的相互關系與組合趨向,它同前兩者一樣,雖然同屬敘事元的運動模式,但實際上這三者與敘事元的自在運動不是一個層級的——其原因在于前者與后者具有本質上不同的定位。通俗地來說,意象的連綴實際上就是:在經過“排列”與“組合”之共同建構的手法之后具有外在形態的某種敘事組的建構.這里,我們不妨借助結構主義的基本方法來進行說明,我們首先將具有空間性質的對象賦以橫聚合軸上的任意一個值,同時再將具有時間指示性的語言對象賦以縱聚合軸上的任意一個值,通過兩者結合的模型我們最終可能通過該模型來對大多數敘事類文本中的大部分的,具有時空體性質的文本對象進行建構,上文說到,作家一般可以通過那些敘事元的連綴結構來形象地表達某種涵義,上文所舉的兩個例子就是這個樣子;應用到文本的建構上,那些敘事元的連綴結構將構成文藝學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參考文獻
[1] 米哈伊爾·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力岡譯 [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 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文集》 豐子愷譯 [M]南京 譯林出版社
[3] 亞瑟·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4] 嚙合點的理論,簡單來說就是關于情節與意象之同構流動的切合方式的理論。
[5] 埃普施泰因《形象與概念的交叉點(現代文化中的隨筆)》[M] 柏林
[6] 瓦連京·哈利澤夫《文學學導論》 周啟超譯 [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基金項目:本文是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大學生創新項目《邏輯學取向的結構主義文藝學文本分析在中小學閱讀教學中的應用》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任敬鵬(1999-),男,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18本科生
王冶廷(1999-),女,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18級本科生
葛欣雅(1999-),女,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18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