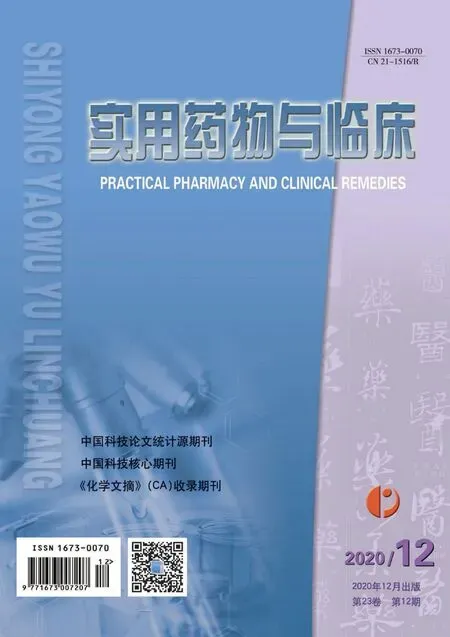橋接蛋白PALB2在乳腺癌發生機制中的研究現狀
孫沙沙, 馬金柱, 布日古德
0 引言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2017年我國乳腺癌發病占女性惡性腫瘤的17.07%,居第一位[1-3]。現有研究提示,絕大部分腫瘤在分子水平上都會有基因異常變化,包括某些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及相關凋亡蛋白的異常,導致細胞的增殖分化異常,最終累積而導致腫瘤的發生。PALB2被鑒定為一種BRCA2相互作用蛋白,被認為是通過同源重組進行DNA修復的細胞機制中的一個齒輪。PALB2與BRCA1相互作用,被BRCA1定位,并在BRCA1下游發揮作用,且從機制上來說,PALB2通過介導BRCA2和RAD51重組酶向DNA損傷位點的募集而為HR所必需。現對PALB2結構、生物學功能及其與乳腺癌的相關性作一綜述,以期對乳腺癌的基因研究提供一定幫助。
1 PALB2的結構及其在HR中的生物學功能
PALB2基因位于16號染色體短臂(16p12.2),包含13個外顯子,編碼的PALB2蛋白包含1 186個氨基酸殘基,分子量為131 kDa[4],主要作為連接BRCA復合體(BRCA1-PALB2-BRCA2-RAD51)的橋接分子,并促進RAD51的功能,同時可與多個同源重組相關蛋白結合(BRCA1、BRCA2、RAD51、RAD51C、MRG15 等),在DNA損傷修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PALB2在HR中的作用已經被證明涉及到幾個蛋白質結構域,包括卷曲的螺旋結構域、WD40結構域和染色質結合基序(ChAM)。
卷曲螺旋結構域位于PALB2(殘基9-42)的N末端,負責其與BRCA1的相互作用。除了積極調節HR外,BRCA1-PALB2相互作用還需要防止單鏈退火(Single strand annealing,SSA),這是一種導致DSB修復的缺失途徑。Anantha等[5]使用U2OS/DR-GFP和U2OS/SA-GFP報告細胞,證明PALB2或BRCA2的耗竭導致HR活性受損,SSA顯著增加,而BRCA1的耗竭則導致HR和SSA活性的降低。這些結果證實BRCA1是DSB修復的關鍵,而PALB2則是引導DSB修復走向切除后的HR通路。在電離輻射后發現PALB2(S59、S157和S376)的三個N端S/Q位點發生磷酸化,磷酸化事件由共濟失調毛細血管擴張突變蛋白和Rad3相關激酶介導[6]。磷酸化缺陷的PALB2未能促進RAD51病灶的形成,導致HR受損和基因組不穩定。
WD40域位于PALB2 C端,形狀為WD40型β-螺旋槳,有7個葉片[7]。該結構域與BRCA2、DNA聚合酶η、RAD51、RAD51C和泛素連接酶RNF168相互作用[8]。即使WD40區域內的單核苷酸變化也會干擾PALB2-BRCA2相互作用并導致HR缺乏[9]。PALB2的WD40結構域對于與DNA聚合酶η的相互作用也很重要。最近,在PALB2的WD40結構域中發現了一個隱藏的核輸出序列,乳腺癌相關的PALB2截短突變W1038X暴露于此,導致PALB2易位到細胞質并導致HR[10]缺陷。
ChAM是一個位于PALB2中部的進化保守的結構域。ChAM缺失的PALB2在支持MMC誘導的RAD51病灶形成中起著折衷的作用,提示ChAM通過染色質聯合促進PALB2的功能。染色質結合被認為是PALB2生物學功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除了ChAM,MRG15是參與PALB2染色質結合的另一個PALB2相互作用,MRG15屬于高度保守的MRG蛋白家族[11],具有兩個功能域:一個是與PALB2和多個轉錄調節因子結合的MRG域;另一個是與賴氨酸36-三甲基化組蛋白H3結合的N-末端色域,由賴氨酸甲基轉移酶集域介導。MRG15結合區大致定位于PALB2的中間區域(殘基611-764),與兩個高度保守的區域(殘基611-629)和MBD-II(殘基724-737)完全匹配[12]。Bleuyard等[11]提出MRG15-PALB2復合物可能是活性基因中的一種基因組穩定劑,使PALB2在DNA損傷后立即可用,并保證對復制脅迫的快速反應,從而維持基因組的穩定性。除了MRG15-PALB2相互作用外,PALB2在復制應激期間也被磷酸化復制蛋白A募集。Murphy等[13]揭示了在復制應激期間RPA的磷酸化刺激PALB2的募集并增加PALB2染色質結合的穩定性,使PALB2可用于緩解復制應激并促進停滯的復制分叉的恢復。ChAM與核小體結合并參與染色質上PALB2-BRCA2-RAD51復合物的形成,在DSBs后迅速轉化為活性BRCA復合物。
除了BRCA復合物的形成,PALB2還直接與RAD51相互作用,增強其侵入鏈活性[14]。最近,Deveryshetty等[14]表明,PALB2的主要DNA結合域(DBD)位于其N-末端(N-DBD,殘基1-200)。N-DBD中只有4種氨基酸突變顯著干擾PALB2的HR活性。令人驚訝的是,作者發現PALB2的N-DBD增強了RAD51介導的鏈交換,并且在沒有RAD51的情況下也促進了類似的反應。利用鏈交換熒光分析,他們進一步證明PALB2 N-DBD促進了以DNA或RNA為底物的正向和反向鏈交換。
2 PALB2與BRCA1、BRCA2的相互關系
PALB2作為BRCA2細胞核內定位、轉移和穩定的協同因子,PALB2末端的WD40重復序列介導其與BRCA2相結合,再通過卷曲螺旋結構域直接與BRCA1相互作用,來修復DNA損傷。在DNA損傷修復過程中,PALB2綁定BRCA1和BRCA2,形成BRCA1-PALB2-BRCA2分子支架,促進intraS端DNA損傷檢測點和同源重組功能的發揮[15]。
許多研究證明了BRCA1在HR途徑中的直接作用,因為BRCA1缺陷細胞顯示出嚴重受損的HR介導的DSB修復[16]。繼DSB之后,BRCA1通過abraxas-RAP 80大復合體與DSB結合,從而誘導組蛋白在脫氧核糖核酸雙鏈體上的泛素化[16]。BRCA1-abraxas-RAP 80復合物的形成依賴于組蛋白H2AX的磷酸化,組蛋白H2AX是DNA損傷檢查點蛋白1和環指蛋白8的介體[17]。隨后,BRCA1通過與Mre11、Rad50、Nbs1的協同作用與CtIP形成復合物,以在HR的合成依賴性鏈退火途徑的早期步驟中促進5’末端切除[18-19]。雖然BRCA1-CTIp復合物已被證明對雞DT40細胞中的HR途徑至關重要,但另一項研究報告稱,這種相互作用對于切除介導的哺乳動物細胞中的DNA修復或腫瘤抑制不是必需的[20]。接下來,BRCA1與PALB2和BRCA2相互作用,招募RAD51,RAD 51是HR修復途徑中的一種重要介質。BRCA1-PALB2- BRCA2復合物的形成依賴于CHK2介導的BRCA1上S988的磷酸化作用[21]。BRCA1在HR中的功能不同于其在DNA損傷修復應答(DNA damage response,DDR)中的其他功能。表達BRCA1突變體S988A的細胞具有缺陷的HR修復途徑,盡管檢查點調節或對電離輻射的抗性保持完整[22]。此外,研究發現,T1394磷酸化殘基對BRCA1-PALB2的相互作用有影響,該位點的任何突變都會部分損害HR途徑的活性。
BRCA1-BACH1復合物也有助于HR途徑。該復合物不受心率限制,涉及許多DNA修復途徑,如細胞周期檢查點和DNA鏈間交聯修復[23]。BACH1是一種范可尼貧血(Fanconi貧血,FA-N)蛋白,通過磷酸絲氨酸與BRCA1的BRCT結構域相互作用[24]。BACH1或BRCT結構域中的突變可能破壞BRCA1和BACH1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HR途徑,延遲DNA修復,并最終增加乳腺癌的風險[25]。
BRCA2通過實現基于同源重組的無錯誤DNA雙鏈斷裂修復和S期DNA損傷檢查點控制,充當基因組完整性的“看護者”。而PALB2,一種BRCA2結合蛋白,與核病灶中的BRCA2共聚焦,促進其在關鍵核結構中的定位和穩定性(例如染色質和核基質),并使其發揮重組修復和檢查點功能。此外,在乳腺癌患者中發現的多個種系BRCA2錯義突變,似乎破壞了PALB2與BRCA2的結合并使BRCA2-HR/DSBR功能失效。因此,PALB2維持BRCA2關鍵細胞的生化特性,并確保其腫瘤抑制功能。
3 PALB2與乳腺癌
大量研究表明,PALB2的雙等位基因突變導致范可尼貧血,而PALB2的單等位基因突變使攜帶者易患多種癌癥,如乳腺癌、胰腺癌和卵巢癌[26]。
乳腺癌是最常見的癌癥,也是全世界女性癌癥死亡的主要原因[27]。大約10%~15%的乳腺癌病例是由家族和遺傳因素引起的,這突出了遺傳易感性在乳腺癌發展中的重要意義。以前的研究已經確定了廣泛的乳腺癌易感基因,包括BRCA1、BRCA2和TP53[28]。然而,家族性乳腺癌的易感基因(如乳腺癌的家族性外顯率為13%,僅占乳腺癌總患病率的13%)。最近對多基因面板測試的大規模分析證實了PALB2是一個高危的乳腺癌易感基因[29],并且PALB2突變對乳腺癌的優勢比(OR)與BRCA2突變的比值比相當[30]。因此,全面了解PALB2的生物學功能對于乳腺癌的治療和精確的醫學治療至關重要。
PALB2與乳腺癌密切相關,并與乳腺癌的易患性、臨床病理特征和預后有關。研究測定了家族性乳腺癌隊列中BRCA突變陰性的PALB2單等位基因截斷變異的頻率(10/923,1.1%),對照組(0/1 084,0%;P=0.000 4)。同時,具有單等位基因PALB2突變的個體患乳腺癌的風險增加了2.3倍(95%CI:1.4~3.9;P=0.002 5)。隨后,多個基于人群的PALB2截斷突變篩查報告顯示,PALB2截斷突變攜帶者患乳腺癌的風險增加了2~30倍[31-33]。
男性乳腺癌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占所有乳腺癌病例的1%以下。然而,20%的男性乳腺癌患者有乳腺癌家族史,突出了遺傳易感基因與男性乳腺癌之間的強相關性。迄今為止,在男性乳腺癌患者中已報道了許多PALB2的致病變異體[34-36]。2017年,Pritzlaff等[35]發現PALB2變異顯著增加了男性乳腺癌的風險(OR=6.6;P=0.01)。Rizzolo等[36]發現,在非BRCA1/2改變的男性乳腺癌患者中,PALB2是最常見的突變基因(1.2%),而有害的PALB2變異使男性乳腺癌的風險增加了9.63~17.30倍。最近,Yang等[33]通過分析來自21個國家的524個PALB2的致病變異體家族的數據,進一步顯示PALB2的致病變異體攜帶者的男性乳腺癌相對風險估計為7.34(95%CI:1.28~42.18;P=0.026)。
一些研究還發現,PALB2突變乳腺癌與侵襲性臨床病理特征有關。Heikkinen等[37]報道乳腺癌患者PALB2 c.1592delT突變更易出現三重陰性表型(54.5%,P<0.000 1)。此外,與其他家族性或散發性乳腺癌患者相比,PALB2突變的乳腺癌患者更易出現在晚期疾病階段(分別為P=0.002 7和P=0.001 7),Ki67水平更高(分別為P=0.000 4和P=0.049 0)。
在研究中,PALB2突變的女性乳腺癌患者10年生存率為48.0%(95%CI:36.5~63.2),顯著低于PALB2突變陰性的女性乳腺癌患者(74.7%;95%CI:73.5~75.8)。最近,中國一項基于人群的乳腺癌易感基因篩查進一步證實了PALB2在乳腺癌中的預后價值,PALB2突變的患者與非攜帶者相比,總體生存期更短(校正危險比:8.38;95%CI:2.19~32.11;P=0.002)[38]。
4 PALB2缺陷的治療
PALB2是與遺傳性乳腺癌相關的基因突變。與普通人群相比,PALB2突變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風險增加了5倍。目前,對此突變的婦女的外科治療缺乏研究。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PALB2突變攜帶者手術的研究。乳腺癌的高風險使得雙側預防性乳房切除術成為PALB2突變婦女的潛在選擇。在推薦預防性乳房切除術之前,根據家族史采取逐案調查的方法,在這組患者中是合理的[39]。
聚ADP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作為DNA損傷的傳感器和調節器,在單鏈DNA的修復中起著重要作用,突破了堿基切除修復途徑[40]。PARP抑制劑治療可阻止單鏈DNA斷裂的修復,并導致細胞內DSB的形成。BRCA1/2缺陷細胞不能通過HR途徑修復DSBs,導致細胞死亡[41]。Rodrigue等[42]利用siRNA介導的RNA干擾產生PALB2缺失的HeLa細胞,并在PARPi敏感性試驗前補充外源siRNA抗性的PALB2變異體。表達PALB2的細胞變異株p.T1030I或p.W1140G顯示出明顯高于表達野生型PALB2的olaparib敏感性。Boonen等[43]開發了一個基于cDNA的PALB2變異體功能分析系統。通過評估PALB2變異體挽救PALB2基因敲除小鼠胚胎干細胞PARPi敏感性的能力,他們鑒定出12個PALB2變異體(p.Y28C,p.L35P,p.W912G,p.G937R,p.I944N,p.L947S,p.L961P,p.L972Q,p.A1025R,p.T1030I,p.G1043D,p.L1172P)顯示對PARPi過敏。
兒科進行的BMN673的臨床前研究表明,PARPi對PALB2缺陷腫瘤具有綜合致死作用。這些數據表明,為了獲得最佳的臨床結果,應該評估PALB2的狀態,并將其納入遺傳咨詢和患者治療方案中。
5 結語
綜上所述,在HR過程中,PALB2在BRCA1和BRCA2之間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促進RAD51重組酶向DNA損傷位點的募集并將其組裝成核絲以啟動DSB修復。PALB2突變的患者與非攜帶者相比,患病率增加、三陰性乳腺癌病理幾率大,預后差、總體生存期更短。雖眾多研究者對PALB2的具體結構、多方面功能和復雜的調控網絡已經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為了提供個體化的臨床管理,需要進一步的長期、基于人群的PALB2突變研究和系統的功能驗證,以積極應對乳腺癌治療中所遇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