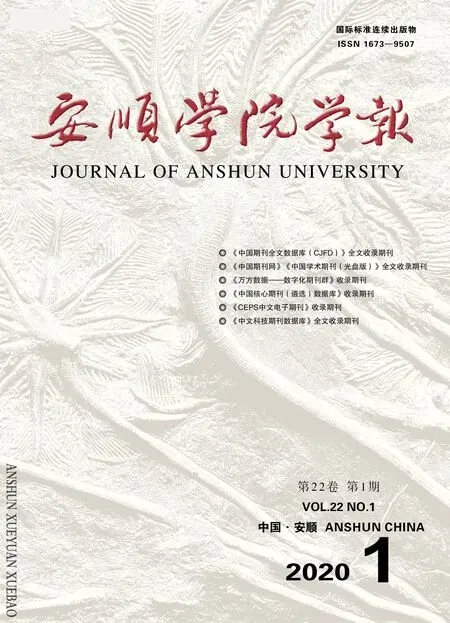明初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移民及其影響
(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貴州 貴陽550025)
關于明代貴州移民的相關研究,目前國內研究相對較少,查閱相關文獻,也就十余篇。研究涉及移民與家庭倫理、地域認同、地方開發、人文生態、民族融合等方面,然涉及黔東南地區的移民研究不多。諸如冉光芬認為,明代移民與貴州世居民族的交匯、融合,將儒家倫理觀念移植到了貴州,推動了貴州社會文明化的進程。[1]陳冉冉認為移民會館的形成是以共同信仰、地域認同、移民因素、鄉土觀念等為基礎的,連接著移民共同的文化信仰、共同的鄉誼鄉情。[2]李丹丹認為,移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滲透進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中,促使當地少數民族逐漸由“化外”轉為“化內”之民。[3]廖榮謙認為,移民將其所屬的強勢文化帶至貴州,與本土文化互相碰撞,相互融合,促進了貴州的人文生態的整體建構。[4]呂善長、張明認為明代漢族移民對貴州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風和民族關系均產生了深遠影響。[5]吳夏平從移民詩人的視角出發,認為移民詩人以“變夷”為己任,通過詩歌來宣揚儒家思想和人生哲理,是移民詩人作為異質文化介入黔本土文化的結果。[6]冉光芬、吳夏平以詹氏家族墓志為例,認為漢族移民之間的聯動,鞏固和加深了漢族家庭倫理觀念,但同時因其“優越”的自閉姿態,又阻礙了民族融合進程。[7]韓蕾蕾以顧氏移民宗族為例,認為顧氏宗族進入黔東南,促進了黔東南地區的開發,促進了漢苗民族文化的融合等。[8]綜上,明初黔東南地區作為漢族移民的主要聚集區,漢族移民為黔東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研究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移民,可以為黔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民族工作提供有益的歷史經驗,為黔東南區域經濟開發,民族融合,社會變遷及文化多樣性的形成找到突破口。
一、明初黔東南地區漢族遷入的原因
歷史上影響人口遷移的原因很多,有自主性的、被動性的、有政治、軍事、商業、災難、生態移民等諸多類型。不過就明初而言,移居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群體有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三方面的原因,三者之間互為表里,相互依賴,互為補充,構成明初黔東南地區完整的移民系統。
1.政治原因
明初中央王朝為積極經營西南各省,征討云南并鞏固西南邊疆安全,所以就以政治移民的形式,實行大規模、有組織的移民。而黔東南地區就是洪武初年移民的重點區域。政治層面的移民形式有衛所移民、民籍移民、充軍、仕宦及流放等五種。其中衛所移民,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和國家意志,是明中央政府強制性的移民政策的體現。而民籍移民,由于中央政府優惠政策的支持,凡是響應中央政府移民政策的民眾,在異鄉定居下來的均可免征各種捐稅,給予不征稅的待遇。民籍移民就是靠著這種政治性的政策,才源源不斷遷移到黔東南地區。明政府在黔東南地區大力推行“移民實邊”“開中”,設置衛所,推行軍屯,民屯、商屯等政策舉措,均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及鼓勵下推進的。同時,在明朝政府“調北征南”的戰略行動中,大批中原漢人隨軍移居西南邊陲,貴州黔東南地區首當其沖就成為明中央政府“移民實邊”的重要過渡地帶。
2.經濟原因
明洪武初年,因連年戰亂,致使國家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蕭條,社會各項事業急需百廢待興,政府為恢復社會生產,合理利用國土空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得不在全國范圍內對人口資源進行整合,“移民就寬鄉”就自然而然成為中央政府進行人口資源整合的首選。當時黔東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地廣人稀,久欠開發,正好趕上中央人口資源的整合,而黔東南地區開發的巨大吸力,成為明初中原漢人移居黔東南的客觀條件,給黔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發展生產力的契機。
由于洪武年間的衛所制度的設立及有效的移民政策的實施,使得中原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區,為了生計,響應國家政策,遷入黔東南地區,這種基于經濟因素引起的人口遷移,是黔東南地區空間人口拉力與中原地區人滿為患的人口推力的集中體現,它是直接或間接導致中原人口向黔東南邊陲地區遷移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想要借機發財的工商業者,冒險來這里發財,憑借政府之力,積極開展商屯,到這里與政府進行商業貿易,這些商人一方面改變了因大量軍戶移民而導致生活物資緊缺的現狀;另一方面,也解決黔東南地區少數民族食鹽的問題。綜上,無論是商屯募集者,還是自發流入者,皆因經濟原因而遷居黔東南地區。
3.社會原因
元末明初,由于常年戰亂,社會動蕩,民生凋敝,廣大農民群眾生活困難,導致大部分人民背井離鄉,從戰區跑到臨時安全區,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地方,遷入到經濟條件相對較差,但社會穩定程度與政治局面相對穩定的地方躲避戰亂。雖明初西南各省均遭受過戰爭的破壞,但戰亂波及云、貴地區的時間較短,影響范圍較小。而黔東南地區是湖廣進入黔中的門戶,剛好具備這種條件,戰亂影響小,居住環境相對穩定,自然資源豐富,加之明朝政府對“移民寬鄉”政策十分重視。在綜合諸多方面因素的考慮下,一些地區及生活較為困難的人民群眾,響應明政府政策的號召,自然而然就移居黔東南地區。同時明政府還規定:凡移居邊疆地區的人口,可減免幾年賦稅,他們為減免稅收,少交或不交。凡此種種,明初移民總離不開衛所移民的影響,因大批量的衛所移民移居黔東南地區,為黔東南地區的民籍移民、仕宦移民、流放政治犯移民等提供了社會保障和物資保障,大批衛所移民進入黔東南及整個貴州地區,為整個西南地區的自由移民導開先路。
二、明初黔東南地區漢族移民的主要類型
明初的人口流動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政府有組織的人口遷移;二是局部人口相對過剩造成的人口遷移;三是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遷移[9]。而明初貴州的漢族移民類型,有衛所移民、民籍移民、商屯移民、仕宦謫遷官員移民四種。
1.衛所移民
明朝初年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移民人數最多,且影響最深遠的當屬衛所移民。明王朝為統一中國,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派大軍征討云南,而黔東南地區作為中原進軍云南的第一道門戶,其戰略地位凸顯,為了保障明政府對云南的軍事行動,朱元璋決定在戰略地位凸顯的黔東南及以西地區設立衛所,并實行屯田制度,解決駐扎軍隊的糧食問題,以期實現自給自足。
說到明初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移民,不得不提及明朝初年的衛所移民,因為這是一支以漢民族為主體組成的、政府有組織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10]。明朝政府為了平定云南,消除云南的不穩定因素,于是自明朝大軍進入貴州起,就在控制貴州的范圍內,特別是從湖南經過貴州東部、中部、西部直達云南的驛道上遍設衛所,并派有軍隊駐守[11]。由此黔東南地區(洪武時期隸屬湖廣都司)衛所就隨之建立。
洪武十四年(1381年)藍玉、沐英等率軍進入貴州時,明朝政府就先后在今貴州境內廣設衛所,其中處于今黔東南境內的洪武時期所設的衛所就有11個。分別是黃平千戶所、清平衛、興隆衛(今黃平縣)、五開衛、平溪衛、清浪衛、鎮遠衛、偏橋衛、銅鼓衛及天柱所、汶溪所。因“邊六衛”及天柱(隸屬湖廣靖州衛、汶溪千戶所皆位于湘黔驛道上,隸屬湖廣都司,故貴州地方志多不載其編制軍額。但康熙年間編寫的《湖廣通志》卷之八《兵防》卻有明確記載,明初今黔東南境內各衛所軍隊的具體數量。每個衛所軍額分別如下,五開衛32261名、清溪衛6244名、鎮遠衛5600名、銅鼓衛18036名、偏橋衛5600名、平溪衛5614名、天柱所1112名、汶溪所1108名,合計75575名[12]。
2.民籍移民
民籍移民包括民屯以及后來因逃荒、流亡等因素而遷入黔東南。《明史·食貨志》說:“其制,移民就寬鄉,或招募或罪徒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13]黔東南各的民屯情況,目前沒有正史考證,所以較難把握。故只得從一些家族譜書中獲知,有“調北填南”此等說法、以及從漢族移民當時修建的民居風格來判斷,漢族通常居住一列三間吞口式平房,而苗侗民族大多居住干欄式房屋。民屯既組織“狹鄉”之民遷往“寬鄉”進行屯種。明王朝建立后,為鞏固王朝統治,急需盡快恢復各地區生產,于是明中央政府鑒于當時的社會情況,不得不把農民和土地重新結合起來,讓耕者有其田,以緩解社會矛盾,實行“移民就寬鄉”的政策,采取各種措施促使“狹鄉”人口向“寬鄉”流動。《明史·食貨志》謂:“移民就寬鄉,或招募或罪徒者為民屯。”[14]明朝初年黔東南地區的民屯主要有兩種不同的來源:一是由府、州、縣招徠的農戶及社會上的游民;二是因犯罪而發配到黔東南的罪人。[15]因為沒有衛所移民那樣有嚴密的組織,僅是零散的遷入,所以沒有確鑿的統計數據,但是這當中大部分均是漢族人口。
同時,明初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移民中的匠戶及一些自由移民,均將其納入民籍移民。匠戶在移民的過程中有一部分隨軍而來,在衛所中服役,另外一部分則在官府充役,有的則以手藝謀生。[16]由于今黔東南地區在明初擴建軍營,修筑湘黔驛道,架橋鋪路,鍛造軍械,制造農具及各種生活用具用品,急需各行業的工匠,致使各行各業的工匠進入黔東南地區。至于一些組織松散的、或根本沒有組織的移民,他們因受到居住地的自然災害而逃慌到黔東南地區,這些組織松散的遷入人口,大多從鄰省遷移到黔東南,并長期居住在這里從事商業貿易、手工業和農業生產活動。
3.商屯移民
《明史·食貨志》載:“明初,募鹽商于各邊開中,謂之商屯”[17]。 洪武年間,黔東南地區民籍人口的遷入與商屯有著密切的聯系。明朝政府為了鼓勵商屯,實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經濟措施,鼓勵商人積極投入“移民寬鄉”的社會經濟建設中來,而黔東南地區不產鹽,移民人口眾多,所需生活食用鹽極度缺乏,給軍隊和當地百姓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基于明朝政府就出臺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商人納米中鹽。于是鹽商們在黔東南招民屯田,以米糧來換取鹽引,而后從川、粵、滇、江淮等地購買食鹽進入貴州[18],進入黔東南地區,很大一部分中原漢人就通過此條“商屯”途徑進入黔東南地區。《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中這樣記載:“從洪武六年(1373年)在播州等處,‘募商人于本州納米中鹽’以來,先后在層臺……銅鼓、清浪、偏橋、鎮遠、五開等衛附近“開中”,商屯大興,商人牟利紛紛招種,許多內地農民來此屯田,此時漢族人口移入者居多。”[19]
4.仕宦謫遷官員移民
洪武年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雖不限南北,但是“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20]。 因此當時在貴州黔東南地區任職的官員,他們在職時間有長有短,可視為入籍黔東南地區的特殊移民。仕宦、流寓及謫遷的人員,他們一般都有一定的任職期限,任職期一滿,有的官員可能會轉遷到其他地方繼續上任,有的則返回原住地。但也有一部分謫遷流寓的官員,他們因種種原因而定居黔東南,永久地在黔東南安居樂業,繁衍子孫后代,而成為 “后原住民”,不過此種移民類型數量是有限的,故在此不做更多論證。
三、明初黔東南地區漢族移民的主要特征
1.以衛所移民為主,自由移民為輔
明初政府組織大規模的軍事移民,在貴州黔東南地區建立十幾個衛所,每個衛所均有一定數額的限定。大規模有組織的衛所移民,是黔東南地區漢族移民的主要形式,衛所移民占據比重大,而影響相應的也是其他類型的移民所不可比擬的。至于商屯移民、民籍移民及仕宦任職官吏移民等移民類型,他們的數量往往要比衛所移民少得多,此三種移民數量總和還不及衛所移民的十分之一 ,這些類型的移民所占的比重少,不成規模。
2.移民具有單一性,以漢族移民為主
隨軍而來的移民,除部分少量的回族外,大多是漢民族組成的軍隊。又因回族軍民的遷居地點多為云南曲靖,昭通及烏撒衛(今貴州威寧縣中水地區)等地,貴州其他地區,特別是黔東南地區再沒有回族移居的相關史料記載,因此黔東南地區的移民多為漢族移民,所以明初的黔東南地區移民成分具有單一民族性。至于移民當中除士兵外,還有一些匠戶以及隨軍的醫護人員,大多均來自中原地區,更加進一步確定其民族性。
3.移民數量龐大,軍戶居多
按照明代的衛所制度,除特殊情況,每衛定額五千六百人。為使軍士安心戍邊服役,明政府有明確的規定:“一人在軍,合家前往”,無妻室者皆予婚配[21]。這樣5600人就變成了5600戶,若以3口之家計算,每衛應當有16800人。然而當時黔東南地區所屬湖廣都司的六衛二所,合計有75575名軍戶。而黃平千戶所、清平衛、興隆衛隸屬貴州都司,按明初常規編制,則合計有12320名軍戶。那么明初黔東南地區的軍戶就約有87895戶。若按此法計算,當時黔東南地區漢族移民人口數當有263685人,若以4口之家、5口之家計算,明初黔東南地區的軍戶移民數量更龐大。當然這只是大概推算,除去一些沒結婚的或者家口少的軍戶、商人及官吏人口不上算,在明初黔東南地區的漢族移民當有二十余萬之眾,這是沒有爭議的。這樣一支龐大的建設隊伍,形成一股巨大的開發力量,對黔東南地區的社會發展不可謂影響不大。
4.共同經濟生活下的共同心理素質
由于漢族移民皆來自中原地區,他們擁有共同的經濟特征,即傳統的封建經濟,文化上受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經濟上受封建地主制經濟,男耕女織,精耕細作影響,所以在這些漢族移民身上就相應地表現出共同的心理素質,而在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則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眾所共同擁有的心理,即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民族富強。這為明朝政府進一步強化黔東南地區少數民族民眾的國家意識和民族團結意識奠定心理基礎。
四、明初黔東南地區漢族移民的主要活動
1.農業活動
明初黔東南地區的人地矛盾比較突出,往往是人偏少而田土偏多,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存在嚴重的不足,致使土地開墾的范圍有限,田土畝數偏低,可以耕種的土地面積少,因此在明朝的地方志中常有“黔不患無田而患人”的記載。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采取“移民寬鄉”的政策,用“移民實邊”的辦法,把地狹人稠地區的居民,移往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區,黔東南地區也就成為明朝政府“調北填南”的重點區域。[22]
據《貴州通史·明代的貴州》記載,在朱元璋時期湖廣都司所屬的六衛一所估計有屯田30萬畝,大部都分布在驛道沿線的壩子周圍,田略多于土。在水利資源豐富的地段,開墾為水田,人們常常種植水稻及養殖一些魚蝦之類,而在水源稀缺的地方,坡度較大的山地,一般開墾為旱地,亦稱土,種植小米、紅稗、大麥、小麥、燕麥和豆類等。洪武時期貴州黔東南地區還屬于湖廣都司的管轄范圍。由此可以看出,黔東南地區的稻作農業還是相當普遍的,而在漢族移民移居黔東南之前,黔東南地區山區地區,還普遍實行“刀耕火種”的粗放型農業耕種方式,直至洪武大移民,這種粗放型的農業耕種方式才逐漸得以改變。
明初的黔東南地區,由于漢民族的移居,帶來了中原先進耕種方式,致使這一地區,中洼之處,平曠之區“犁而為田”的現象逐漸普遍。到永樂以后的歷史著作中,經常有腰帶田(梯田)、冷水田、望天田和塘田等記載。麻哈,清平一帶的農民,在當時他們可以利用水勢高度引水向低處灌溉田土,也懂得按土壤性質、肥瘦來栽種不同的品種,諸如上田種晚稻,中田種早稻,下田種旱粘。[23]若是遇上風調雨順的年時,每畝上田可收米二石五斗,中田收米兩石,下田收米一石左右。[24]永樂后,黔東南地區在地勢較為平坦的鎮遠、清平一帶,漢民族居住相對集中的地方,冶煉技術的提高,鐵制農具的大量出現,各處的府、州、縣的鐵質農具皆已得到普遍使用,牛耕技術在黔東南地區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廣,農耕技術受到當地民眾的認可。[25]鎮遠已成為黔東南糧食市場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政府為了農業生計,大力鼓勵民間興修水利,以保障農業的生產發展。同時這些移民還給當地帶來內地“選種”的優良傳統極大地提高了糧食產量,緩解該地區的糧食危機,也為手工業及商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明初黔東南地區的農業發展,不僅體現在耕地面積得到極大增長外,還體現在耕種方式上牛耕技術的普及以及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更加規范。明洪武年間,先后在黔東南地區設立的“邊六衛”及天柱、汶溪(天柱境內)兩個千戶所,設屯堡屯田,把壩田,絕田收歸國有,令軍士、驛夫屯田自給,每軍屯田一般65畝左右。據《貴州通史·明代的貴州》一書記載,“邊六衛”的屯田數,不確切,因為屬于湖廣都司,貴州地方志未見記錄,但屯田數應與“下六衛”的數量相當,下六衛屯田約239955畝。明永樂十一年,置鎮遠、思州、新化、黎平府,隸貴州,農民向長官司交賦納糧,向朝廷貢物,各府、縣與朝廷戶部對口設置戶房管理土地[26]。至此,黔東南地區的土地納入政府的管理系統,這對黔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生產力發展有很大的提高,規范的土地管理進一步完善了黔東南農業生產制度。
按《明會典》記載明初軍屯衛所“耕種器具、牛只皆給于官”,“凡屯種去處,合用犁、鏵、耙齒等器著有司經給鐵、炭鑄造發用。”[27]“凡屯種合用牛只,設或不敷,即便多文即索 ”。[28]可見當時屯田的軍民已經普遍使用牛耕和各種鐵質農具,這對黔東南地區某些還處于“刀耕火種”和鋤耕的粗放耕作方式,應當是有著推動作用的。同時開墾如此眾多的田土,他們使用內地的牛耕技術進行生產,其意義就在于黔東南地區引進了內地巨大的新生產力。
綜上,明初漢族移民對黔東南地區農業的開拓,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耕地面積顯著擴大,農耕產生技術得到顯著提高,農田水利有較大的發展,成為黔東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2.商業活動
明初,在政府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下,軍屯、民屯、商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規模、不同程度地把中原地區的地主式封建生產關系移植到黔東南民族地區,為黔東南民族地區地主經濟的建立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由于貴州不產鹽,政府為解決貴州的食鹽問題,依靠商屯,招募內地鹽商到黔東南地區就地“開中”,它是明一代黔東南最重要的商業活動。《明史.食貨志》云:“明初,募鹽商于各邊開中‘謂之商屯’”,又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29]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開(黎平)設鹽運司,商人從湘鄉,澧州運鹽到黎平兌換大米。[32]為了順利的運送糧食和食鹽,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黎平至湖廣靖州古道被定為官方驛道,而洪武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389—1390年),朝廷設置衛所屯兵,鎮遠、偏橋、清浪等地置衛筑城。此后民間商船往來頻繁,港口逐步發展,以鎮遠為盛。“滇黔宦游,江楚賈客,多泊舟于此”[33]。
在黔東南地區,移民的商業活動中,茶葉的貿易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宋元時期,茶葉的貿易主要由政府控制,實行專買專賣。明洪武時期,“政府依舊沿用宋元時期茶葉流通的制度,對茶行業進行專買專賣,在交通要道遍設關卡,對茶葉進行統購統銷,嚴禁私人買賣”[34]。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政府在播州設置茶倉,對本地的茶葉實施政府主導買賣,以充實軍力,同時滿足當地少數民族對內地商品的需求。隨后又在石盯、鎮遠、江口等地設置茶倉和關卡,加強對茶葉買賣經營的控制,但明政府對茶葉分散的地區管理較為松散,導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汀茶”(由政府經營)和 “商茶”同時存在。[35]而這些茶商,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原遷移來的漢移民。據《黔東南州志 農業志》載:明代,鎮遠羊場“天印雀舌茶”,從江西山“滾浪茶”,黃平“浪調茶”,凱里“香爐山云霧茶”等均馳名京都,均被列為朝貢方物之一。《明史》中《西南群蠻》記載,貴州清平、偏橋、鎮遠衛場鎮,苗族農民“牽牛逐豕”前來販賣,“市如云集,朝至幕歸。”[36]這些現象都有力證明當時黔東南地區商業貿易的繁榮與發展。
3.手工業活動
《貴州省志·民族志》記載:“黔東南地區在唐宋時期,在金屬工具制造領域,當地苗族同胞自己就能生產多種鐵質工具,如鋒利的環刀、劍、斧和箭鏃。明清時期,他們制造的甲胄、標牌、牛尾槍(火炮)偏架弩等兵器都很有名。”[37]
按明朝政府的戶籍制度,工匠家庭將一律編入戶籍,世代為匠。“工之子恒為工”,世代充役,稱為“匠戶”。明代的匠戶分類很多,有泥水匠、木匠、石匠、鐵匠、銅匠、金銀匠 、織匠、染匠、廚師及其他百業工匠等。這些擁有手藝的漢族移民移居到黔東南地區,為黔東南地區手工業的興起打開了新的局面,漢族移民的手工技術與當地少數民族傳統技術相結合,使得黔東南地區手工業得到長足的發展。
由于匠戶都是世代相傳的,一般很難脫去匠籍,所以其技藝具有家族傳承性,越到后代其手工工藝技術就越高超,經歷父輩幾代人的精心雕琢,工藝技術越發的成熟、精湛。這些具有手工工藝的匠籍移民遷居黔東南地區,自然而然就把中原的先進手工技術帶入黔東南地區,在配上黔東南豐富的自然資源,當精湛的手工工藝技術與豐富的自然資源相結合時,漢民族的手工業在黔東南這塊地方生根發芽,無論是家具行業,還是冶煉行業等都有較快的發展。從明初匠戶的分屬來看,這些手工業皆與現實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是人們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這些手工行業在科學技術不太普及的時代,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完全替代它的產品,這就為黔東南地區民間手工行業的發展奠定了必然的歷史條件。
明初黔東南地區主要手工業活動有刻制金銀首飾、紡織、打鐵、鍛造等工藝。特別是紡織工藝方面,在五溪地區生產的溪布,包括白布和斑布,在當時就很有名。[38]黔東南地區的民族紡織工藝,由于受漢民族先進手工操作技術的影響,紡織機得到迅速的改進,紡織技術得到進一步完善,由此前的只能紡織一根紗的手搖紡車,改進為同時能紡四根紗的腳踏紡車,不管是工作效率還是紡紗產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39]
這些漢族移民,他們的生產、生活用具,如生產的犁耙、踩撬、各類刀具;紡織用的紡車,機梭;生活用的鍋、碗、勺、剪刀、針、錐、升、斗;樂器中的鐃、鈸、鑼、鼓;裝飾品的銀飾等幾乎都是自制。貴州建省后,布匹、刀、剪,鏵口、鋤耙、鐵鋼、鐮刀等都是黔東南地區市場上廣泛交易的重要商品。在造船方面,清水江、沅江流域的苗族,在宋代時只能制造獨木舟,到了明清之際已能制造載重千斤以上的大船了,而且數量不少。[40]明代的造船技術在當時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由于中原的漢民族移居黔東南地區,帶來中原的造船技術,才使得清水江及沅江流域的各少數民族同胞很快掌握更加先進的造船技術。
4.文化教育活動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自古以來歷朝歷代都格外重視,它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立國之本,是一個民族繁榮昌盛的根本。明初黔東南地區教育落后,民眾的智力開發主要是靠傳統教育和家庭教育,通過生產實踐與社會活動,傳承民族文化,傳授生產技術。當漢族移民到來時,貴州儒學教育在黔東南地區勃然興起,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諭中書省臣:“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儒師,授生徒,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教。”[41]對于貴州乃至整個西南,明中原王朝采取“懷柔”政策,把“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定為“安邊”的基本國策,強調“廣教化,變土俗,使之同于中國”,通過儒學的教化作用,使少數民族接受封建禮教,認同傳統經典,啟迪民智。而漢族移民自然而然就擔當了“廣教化,變土俗”這一重要角色。洪武十三年(1397年)在銅鼓衛設立衛學;宣德九年(1434年),設立興隆衛學等,成為黔東南地區官學的重要方面。
洪熙元年(1425年),鎮遠知府顏澤上奏:“本府儒學,自永樂十三年開設于偏橋等處四長官司,夷人之中選取生員入學讀書,頗有成效……”[42]。顏澤上奏得到中央認可,宣宗特下詔諭:“邊郡開學教夷人,若使自營口腹,彼豈樂于學?凡貴州各府新設學校,未與癝膳者,皆與之。”[43]同時命有司撥款修建廟堂齋舍,支持各地辦學。在朝廷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黔東南地區的儒學很快得到發展。據(萬歷)《貴州通志》中記載:鎮遠府“風氣漸開,人文丕顯,游宦者安之”,施秉縣“耕讀紡織,多從樸素”。[44]足見漢族移民到來后,黔東南地區的尚學之風興起,極大地改變黔東南地區的教育條件,扎實了黔東南地區的辦學基礎。
五、明初黔東南地區漢族移民活動的影響
1.提高黔東南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推動新生產關系的建立
明初,大量的軍事移民,給黔東南地區輸入先進的生產方式,提高了黔東南地區的生產力。早在宋朝,政府就在布告中誡諭貴州少數民族居民“個諭爾子孫,棄爾弓弩,毀爾牌甲,賣劍買牛,賣刀買犢”[45],向貴州少數民族宣傳牛耕的重要性。到了明初,由于受漢族移民耕種方式的影響,牛耕在黔東南地區很快得到廣泛的推廣。同時,為解決軍屯耕牛不足的問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延安候唐勝宗因云南諸屯屯牛問題,“請以沅州及思州宣慰司、鎮遠、平越等衛官牛六千七百余頭分給屯田諸軍”[46]。“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六月四日,平溪、清浪等12衛屯田士兵缺乏牛耕,朝廷從沅州、思州、鎮遠等處調劑6770余頭分發各衛”[47]。不管出于何種原因和動機,這些措施都在客觀上扶持,恢復了黔東南地區的農業生產,極大提高了黔東南的生產力水平。漢族移民的到來,在黔東南地區建立起一批“中原式”的開發基地,在交通沿線及衛所駐地周圍,形成一批城堡、集鎮和漢族村落,不斷向外傳播中原的農耕生產技術,進一步推動黔東南地區商業貿易的發展和新生產關系的建立。
2.促進黔東南地區商業市鎮的興起、發展和繁榮
漢族人口移居黔東南,他們不僅帶來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和先進的手工操作技術。同時還帶來了大量的人口,致使大量的移民人口機械進入黔東南地區,巨大的人口數量,首先得解決吃、喝、住、行等基本的生活問題,這必然會促使黔東南地區局部市鎮的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移民人口需要進行有效的商品交易活動,彼此之間互通有無;或是用貨幣進行購買他們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由于數量龐大,自然而然的就在人口相對集中、地勢較為平坦、寬闊,交通較為便利的地方,逐漸形成商業市鎮。而貿易活動的不斷發展,輻射周邊,后經政府宏觀調控順其自然地就形成了名義上商業城鎮。
自明朝初年衛所設立以來,十幾萬的漢族移民人口,以軍事移民的方式進入黔東南地區,他們不但起到明政府希望的“移民實邊”的作用,而且促使這一地區人口機械增長,充實了黔東南地區的人口,巨額數量的移民對生活用品及家具需求,不得不在集市上自行調換交易,這對黔東南地區商業市鎮的興起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到了明永樂年間,黔東南境內清平、偏橋、鎮遠、興隆、五開、思州等地已設有場鎮,鄉民“擔負薪炭、米豆、竹木,牽逐牛豕”入場互市。同時,鎮遠還是當時較大的馬市之一,永樂二年(1404年),鎮守黔東南地區的鎮遠候顧成于鎮遠馬市購馬2000匹,添置衛所官員軍馬。永樂十二年(1414年),平越、鎮遠、清平、偏橋四衛的集市較為繁榮,衛城內的漢族軍民與四圍鄉村的苗族人民,屆時皆從各地來趕場,眾多人群聚居在集市上進行商業貿易活動“市如云集,朝至幕歸。”[48]據《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 工商管理》記載,“至明永樂年間,黔東南境內清平、偏橋、鎮遠、興隆、五開、思州等已設有場鎮”[49]。鄉民們在場鎮上能自由進行物物交換和少量的貨幣交換。可以說永樂年間黔東南地區場鎮的興起與繁榮,是漢族移民的又一功勞。若沒有洪武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及交通等方面的前期積淀,黔東南地區在永樂年間是不可能突然興起諸多商業市鎮的。
3.打破民族分布格局,推動文化傳播及民族融合
漢民族在黔東南地區的遷移定居,原先都是以屯堡的形式與少數民族相互隔離,各自生活。后來由于生產生活的需要,逐漸有了經濟交流,時間久了,心理上的隔閡趨于淡化,于是漢族移民就逐漸走出屯堡,積極與當地民眾進行文化交流及經濟生產。后來,一些外來的漢族人口甚至與當地少數民族之間有婚姻,雙方之間自動達成姻親關系,各民族間的聯姻,使得黔東南地區民族關系變得融洽起來,各民族居住的格局在經濟發展的地區也就逐漸被打破了,相互之間,形成一個個雜居的小鎮,各個市鎮中既有少數民族居住,同時也有漢民族的居住,漢少長期相處相安無事。這樣市場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在各自彼此了解之中,加速了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傳播及民族信任,不論是少數民族主動學習漢民族,還是漢民族被少數民族潛移默化的結果,他們雙方之間都發生了文化的轉化,對各自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吸收,推動了黔東南地區的民族融合。
4.改善了黔東南地區落后的交通狀況及社會面貌
明初,黔東南地區由于湘黔驛道的修建及完成,極大地改善了黔東南地區對外的交通條件,使中原文化與先進的生產技術得以傳入,加速了黔東南地區的開發進程。由政府設軍把守、整修護養,增設站、鋪、因而暢通無阻,改變了當地交通狀況,加大了對黔東南地區的開發力度,使得黔東南在農業、手工業、礦業、交通業、文化、教育方面等都有顯著進步。從此“草昧”漸開,稍與內地比同,黔東南地區出現了新的社會面貌,成為黔東南地區及整個貴州開發史上的極為重要的里程碑,間接促成永樂十一年(1413年)在貴州建省,成為全國僅有的十三個行政區劃。在黔東南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開發的過程中,明朝初年“移民實邊”的政策措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洪武年間,相繼建立了的衛所,客觀上收到了“移民就寬鄉”的政策效果,這一舉措對黔東南地區來說,增加黔東南地區的勞動人手,加快該地區經濟社會的開發。移民寬鄉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明朝政府鞏固西南邊陲的穩定。
綜上所述,明初中原漢族移民進入黔東南地區,與當地少數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加強了黔東南民族地區與省內各個區域經濟文化的交往,打破了黔東南地區經濟社會原有的封閉格局,這對加強黔東南與各區域之間的內部聯系、加速黔東南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結 語
縱觀貴州歷史,自漢族移民進入黔東南地區以來,盡管因爭奪生存空間與其他民族有過矛盾糾紛、有過流血沖突,甚至發生過極端對抗,但從長遠來看,黔東南地區民族關系友好相處、平等互惠是主流。當地少數民族吸納了中原漢族的先進文化,同時部分漢民族以聯姻的形式與周邊各少數民族交往交流,逐漸形成了漢少相融的局面。漢族移民帶來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大大提升了黔東南地區生產力水平。并在漢移民影響下,儒家的“大一統”觀念、國家觀、民族觀、文化觀在黔東南地區生根發芽,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等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在往后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一并成為黔東南地區各民族的主流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