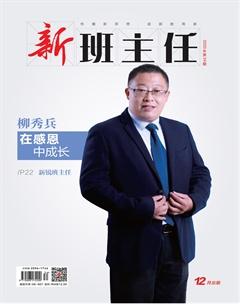班級“峰會”的“前世今生”
陳堅義

“加油,用力拉!”聽著我歇斯底里的吶喊聲,我們班的孩子變得異常勇猛,他們一個個漲紅著臉,死死拽著繩子往后拉。但結果也如我所料,三局比賽我們都輸掉了。
早在賽前,我就給自己打過“預防針”、重在參與。所以,在孩子們應聲倒地的那一刻,我馬上走到他們中間,把昨天早就想好的安慰的話說給他們聽。原以為這件事就這樣告一段落了,可沒想到,伴隨著一個孩子的哭聲,故事又沸騰了。
哭聲此起彼伏,一個比一個響,此時,我內心的想法是:完蛋了,這下不僅輸了比賽,還丟了面子,得趕緊把孩子們送回教室。但轉念一想,孩子們是因為沒能為班級爭取到榮譽才哭的,回到教室,這種狀態肯定一會兒就冷卻了,那這次拔河的經歷對他們來說就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沒有任何教育作用。何不借此機會,將悲痛轉化為力量。于是,我把他們叫到旁邊的草地上,圍坐在一起,開始了一次失敗經驗分享大會。
環顧一圈,我問哭聲最大的那個女孩子,“你為什么要哭?”
“我……我怪我自己沒有力氣。”女生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聽她說話的同時,我還觀察到旁邊的小汪不僅淚水在眼眶里打轉,還不停地用小拳頭捶著草地,小臉漲紅。
我走過去,聽到他嘴里嘀咕著:“媽媽為什么把我生得這么小,這么沒力氣。如果我的力氣大點,我們班就不會輸了。”說著說著,他的眼淚一下子就掉了下來。
我站在原地,讓他們盡情地發泄。等到哽咽的聲音漸漸變小,我才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們,你們知道自己的力氣為什么不夠大嗎?”
孩子們面面相覷。
突然,我們班的一個孩子很小聲地說了一句:“我們個子小,是因為飯吃得少,沒有力氣。”一語激起千層浪。旁邊馬上就有孩子補充:“我們平時太挑食了。”“我們平時回家也沒有好好鍛煉。”孩子們七嘴八舌地說開了。
我順勢問:“那我們要怎么做才能打敗超過我們的2班呢?”話音剛落,就有學生搶著說:“陳老師,我以后要吃兩碗飯。”越來越多的孩子從悲傷和自責的情緒走出來,開始想解決問題的方法。我突發奇想:何不把“失敗大會”改為班級“峰會”?于是,每周五固定的班級“峰會”便應運而生了。
“峰會”前
孩子們自薦或推薦產生候選人,然后通過競選演講,由全班投票選出心目中最公正的5名同學組成議會小組,負責記錄大家的觀點和整理材料。剩下的孩子根據各自的特長、性格等劃分成5個“首腦國”。班內設有2個“峰會”信箱,分為“重要+緊急”和“重要+不緊急”,專門收集班級需要解決的問題。議會小組根據事件的緊急程度將事件排序,每周三公布本周最急需解決的3個問題。每個“首腦國”各自討論,并商定提案。
“峰會”中
準備就緒后,班級“峰會”正式拉開序幕。“峰會”主持人由我擔任,隨著音樂的響起,每個“首腦國”的成員依次起身說出自己陣營的口號。落座后,孩子們一個個正襟危坐,準備大顯身手。在一次討論放學路隊扣分的問題時,我見識到了孩子們的高光時刻。
“A國”:“我們應該懲罰那些在路隊中表現不好,害得班級扣分的人,讓他抄100遍課文。”
“B國”:“100遍課文太多了,寫不完的,讓他跑10圈。”
“C國”:“有時候說話只是不小心,懲罰太重了,有人提醒就好了”
“D國”:“路隊長只有1個,還在最前面,提醒不到所有人,我認為可以增設2名路隊長,前中后各1名隊長維持秩序和提醒同學。”
“E國”:“我覺得,如果2周都沒有扣分,可以增加班級派對時間,有獎勵大家就會有動力。”
……
大家七嘴八舌,卻秩序井然。一個個有效的解決方案在討論中誕生。討論的最后要評出本場每個“國家”的“金點子值”,老師代表5票,議會小組每人3票,每個“國家”成員1票。每月“金點子值”最高的“國家”可以獲得一次外賣點餐的機會,孩子們的熱情和智慧被充分激發了。
“峰會”后
“峰會”結束后,我們有退場音樂,有主持人閉幕詞,還有“各國”的再見禮儀。定版的方案以紅頭文件的形式貼在班級的公告欄,蓋上班級印章,公示一周。
九次班級“峰會”后,我發現孩子們更愿意在集體中討論班級問題,也更愿意接受集體討論之后的結果。在討論中,學生你一言我一語,看似是低年級孩童的稚嫩想法,背后折射出的是為班級努力的強大意愿和驚人的執行力。
一個良好的班集體應該是一個相互影響的生命場。班級“峰會”從無到有,我們都在慢慢成長。
(作者單位:溫州大學附屬南白象實驗小學)
責任編輯 ?何欣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