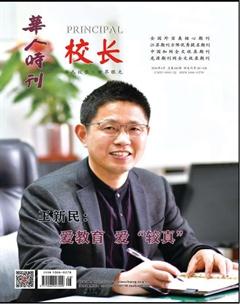放下你的教鞭
張正耀
小學四年級時,教了我三年的 Z老師突然對我意見很大,原因是我貼了他的大字報。
年幼無知的我,被 W老師洗腦了,他要我做“反潮流的小闖將”,于是我成了批判 Z老師的“急先鋒”。這也是學校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大字報,無異一枚重磅炸彈狠狠投擲向 Z老師。幾十年后,我似乎還能看到 W老師那得意而又陰險的笑臉,還能感受到 Z老師因被最信任學生“出賣”的那份氣惱與憤怒的情緒。
懲戒很快降臨到我的頭上:五年級畢業時,十三個學生中十一個都錄取到了初中,只有成績在片里遙遙領先的我卻無緣升學。W老師調走了,是 Z老師做的畢業生材料,他給我寫的“升學推薦表”中有這樣的話:“該生思想不健康,從小就有資產階級成名成家的思想。”后來我才知道,這樣說我的原因是,一次作文課上,我說了我的理想:“將來要上大學。”而當時這種思想是要受到嚴重批判的,雖然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大學”。
我的這份經歷,雖然帶有時代的痕跡,但也證明了這樣的道理:“懲戒之目標,甚于無目標之懲戒。”
Z老師出于一己并不光明正大的情緒,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懲戒一個對江湖險惡幾乎懵懂無知、無法自我辯解、也毫無反抗能力的小學生,無情剝奪了一個學生繼續學習的機會,這是典型的“泄私憤”。
有人說,老師懲戒學生的初衷是教育學生,是“為學生好”,也就是說“出發點是好的”,這實際上是一種說辭。難道教育學生“學好”,就只有或必須通過體罰、語罰、心罰等粗暴形式才能表現出來,才會達到目的嗎?既然是“為學生好”,那就要考慮學生的感受,尊重學生的人格,遵循教育的規律,任何時候,簡單粗暴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哪怕有時會有較為直接的效果。當老師意氣用事地揮舞懲戒的大棒時,其實就主動放棄了與學生和解的機會,而選擇了最為無能甚至最為錯誤的方式,一旦失去了引導和幫助學生的最佳時機,也就宣布了教育的失敗,老師的形象就會轟然倒塌。
教育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懲戒權及其行為一直存在,只不過不同的學校和老師做法有別而已。誠然,懲戒與表揚一樣,既是必要的教育形式,也是教育的內容,但絕不是教育的目的,更不是教育的全部。有的老師盲目相信懲戒的作用,不講原則與策略,懲戒效果適得其反,還破壞了和諧的師生關系;有的老師清醒認識懲戒的正負效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嚴厲中不乏溫情;有的老師講究技巧,注重“造勢”,充滿智慧,把懲戒權關進了籠子,懲戒前約法三章,懲戒時規范有度,懲戒后及時疏導。一味強調懲戒權,片面夸大懲戒權的功能,把教育目標的達成只寄希望于懲戒權的落實,好像只要有了懲戒權,教育的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那是一廂情愿,復雜問題簡單化。是退回過去、重走老路,是缺少教育自信、沒有教育底氣,是教育乏術、低能甚至無能的表現。
任何一個孩子都需要積極的教育眼光,需要真誠的微笑和鼓勵,那是他們成長的動力和源泉。古阿拉伯人歐麥爾·伊本·赫塔卜曾經說:“唯溫和而不軟弱、堅強而不嚴峻者能治人。” 此話雖然是講給政治家聽的,但何嘗不是對老師的忠告呢?老師應該把不帶怨恨的敬重、不帶親狎的愛戴,種在學生的心里。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擁有學生。
老師,請放下你的教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