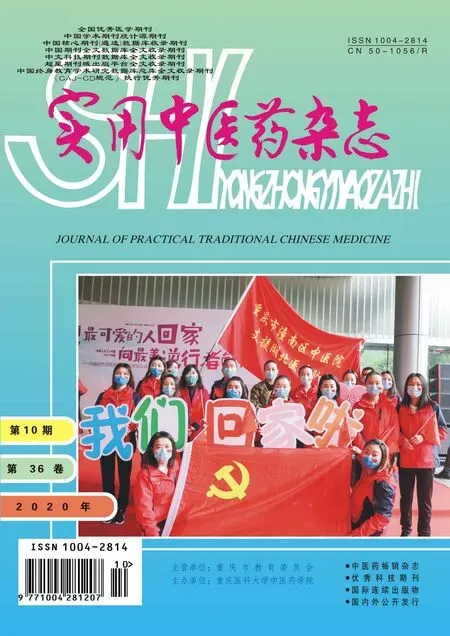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西醫發病機理研究概述
孔玉琴,唐志宇,張 密,沈夢玥,曹文富
(1.重慶醫科大學2018級碩士研究生,重慶 400016;2.重慶醫科大學附屬永川中醫院,重慶 402160;3.重慶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重慶 40001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簡稱慢阻肺(COPD),以持續存在的呼吸道癥狀和氣流受限以及不完全可逆為特點[1]。COPD 病程長、病情復雜,主要累及呼吸系統,同時可伴全身炎癥反應,后期可合并心肺功能進行性減退[2]。目前COPD的發病機理尚未完全明確,為進一步提高臨床治療COPD 的療效,發揮中西醫相互補充的優勢,深化COPD發病機理的研究勢在必行。
1 中醫發病機制研究
中國古籍中并未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明確記載。中醫根據其發病特征及臨床特點將其歸屬于“肺脹”范疇[3],同時中醫對肺脹的病機研究也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
《靈樞·脹論》中首次提出了肺脹之名,其間言“肺脹者,虛滿而喘咳”,指出了肺脹以咳嗽、喘促、脹滿為主要癥狀,與西醫學上COPD的臨床表現較為一致。中醫古籍中對肺脹的病因病機認識主要分為3個時期:春秋戰國至唐朝、宋金元以及明清時期。
春秋戰國至唐朝時期。在春秋戰國至唐朝時期,中醫對肺脹病因病機的認識日趨完善,其中《靈樞·脹論》中論及肺脹發生的病因有寒熱之別[4]。漢代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對后世影響深遠[5],其中有關論述肺脹病因病機、臨床表現、脈象等的相關內容較豐富詳盡。文中提及使用越婢加半夏湯證治療肺脹病的情況,多為肺氣上逆夾飲邪而出現咳而喘滿,目如脫狀,脈浮大等癥時,這已歸納出肺脹主要癥狀為喘促。從脈象浮大及越婢加半夏湯的方藥組成方面分析,主要為外受寒邪、內氣郁塞,氣機壅滯而致肺脹。書中還提及若咳氣上逆、水飲上泛而表現為煩躁喘滿、脈浮者,多用小青龍加石膏湯,從另一方面也提示肺脹病機還可因外邪內飲相搏、挾有熱邪導致肺失肅降。分析可知仲景認為肺脹的發生與內外合邪關系密切,可有飲重熱輕、熱重飲輕之別。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及唐代王熹《外臺秘要》二者認為肺脹的病機主要為肺本虛而感受六淫,正邪相搏,集聚肺內;或是肺氣有余,外邪侵襲,肺失宣降所致[6-7]。揭示肺脹發病機理與正虛或感邪有關。這一時期對肺脹病因病機的認識主要概況為以下幾點:①肺脹的發生與本虛相關;②肺脹發生的病因有寒熱之別;③肺脹的發生與內外合邪關系密切;④肺脹有虛和實,其主要病機是肺臟本虛或感受六淫,正邪紛爭,集聚肺內,導致肺失宣發、肅降。
宋金元時期。宋金元時期是歷史上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繁榮的階段,當時醫學發展成就顯著,對于肺脹的病因病機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8]。其中較為突出的有《太平圣惠方》、《儒門事親》、《丹溪心法》等。《太平圣惠方》中認為肺脹發生主要與肺氣不足,加之風冷寒邪侵襲有關,可致肺失宣降,正邪相爭,肺氣郁滯,痰飲實邪壅塞胸中,并進而表現為咳嗽、喘促等肺脹癥狀[9]。肺脹患者在急性加重期多會出現喘促而不得睡臥的情況,在《太平圣惠方》中提出了氣機升降失常,肺氣上逆是導致肺脹患者出現上述癥狀的主要原因。隨著醫學的逐漸發展,醫者對肺脹理論的認識也逐漸深入。例如《圣濟總錄》在引據《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經典醫籍的基礎上,結合當時各家學說對疾病理論作了進一步闡述。文中提到實邪阻滯手太陰肺經,致經絡不暢,氣機受阻,肺失宣降,可表現為脹滿、喘、咳等癥。元代朱丹溪編著的《丹溪心法》在前人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肺脹的病機為痰瘀阻滯致肺氣失宣。都為肺脹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治療方法[10]。不論是劉完素的《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還是張從正的《儒門事親·病機》皆認為郁火滯肺是導致肺脹的主要原因之一。表明此時期有關肺脹的理論在逐步完善。總結這個時期對肺脹病因病機的認識主要為以下幾點:①肺氣不足,加被微風,氣聚于內,壅塞不通,表現為肺脹;②氣逆是導致喘息不得臥的主要原因;③肺脹發生機理多為實邪阻滯肺經脈絡;④肺脹的病機可為痰挾瘀血,阻礙氣機;⑤郁火滯肺是肺脹的病機之一。
明清時期。明清時期雖然是歷史上經濟、文化由鼎盛到衰落的轉變時期,但在此期間也涌現了大量珍貴的醫學著作,對肺脹發生機理闡述的相關著作也明顯增多,主要著作有《本草綱目》、《癥因脈治》、《脈癥治方》等[11]。明代吳昆《黃帝內經素問吳注·四氣調神大論》篇中提到肺脹發生與人類違背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密切相關:秋燥傷肺,津虧肺燥,氣陰兩傷而致肺氣不足以息。明代李時珍所編著的《本草綱目》中認為肺脹與氣機升降失常相關。《普濟方·咳嗽門》篇提到肺氣不足,加之外邪侵襲,肺衛失宣,邪聚于肺,而為肺脹。秦景明所寫的《癥因脈治》也認為肺脹之因歸咎于自身正氣不足,復感外邪,肺氣郁閉,不得宣發[12]。上述二者都認為肺脹本因為肺氣不足,或是肺氣郁結,復感外邪所致,為內外因合而致之。吳正倫《脈癥治方·濕門·喘嗽》認為火熱傷肺,肺氣郁遏而致脹滿。《張氏醫通·肺痞》提及肺脹多以實證居多。《證治匯補·咳嗽》提出肺脹病機為虛實兼雜,當分虛實辨證施治。《類證治裁》中認為喘由外感者首治其肺,由內傷者從腎治之。清代李用粹《證治匯補·胸隔門·咳嗽》篇對肺脹發病機理歸納較為完備[13],認為其病因病機虛實參雜,診治也應參虛實。如痰瘀礙氣、風寒襲肺、腎虛水枯等導致肺氣不能收斂、發越,可出現一系列的肺失宣降、腎不納氣的癥狀。這一時期對肺脹病因病機的認識主要為:①肺脹發生可因人類違背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秋燥傷肺,津虧肺燥,氣陰兩傷所致;②肺脹的發生多與氣機升降失常相關;③肺氣不足、或是肺氣郁結,復感外邪所致,為內外因合而致肺脹;④肺脹病因病機虛實參雜,診治應參虛實。如痰瘀礙氣、風寒襲肺、腎虛水枯等導致肺氣不能收斂、發越失常。
現代醫家在總結古籍文獻的基礎上,結合臨床實踐經驗,認為肺脹可分為緩解期和急性加重期。急性加重期主要為本虛標實,以實為主;緩解期主要以虛為主,兼實邪內阻[14]。本虛主要是肺脾腎虧虛,發展后期以肺腎心三臟為主,發病之誘因為外邪侵襲、饑飽勞逸等;標實主要為痰瘀等病理產物,并貫穿病程始終。
馬玉玲[7]通過收集近30余年有關慢阻肺的有關文獻,最終納入65篇文章,發現在慢性阻塞性肺病緩解期治療中,中藥使用多以補虛藥為主,另一方面也說明本虛為慢阻肺緩解期的主要特點。萬文蓉等[15]認為外感風寒是肺脹發病的主要誘因。此外,嗜食肥甘厚味、勞逸失調、情志不遂等均可誘發本病,這些誘因每多互相關聯,但仍以氣候變化時外感六淫為主[16]。張仕玉、孫子凱等[17-18]認為慢阻肺反復發作,多因其肺脾腎虧虛,導致氣血、津液運行障礙,聚而為痰、久而瘀結,終至肺氣壅塞而為肺脹。劉小虹等[19]納入126例COPD住院患者,通過分析臨床資料得出,慢阻肺的臨床辨證分型主要為痰熱蘊肺、痰濁阻肺、陽虛水泛和氣陰兩虛四型。其中陽虛水泛證是通常為慢阻肺的終末期,該病程經歷了肺氣虛、肺脾腎氣虛、肺脾腎心陽虛等病程,與“慢支炎-肺氣腫-慢阻肺-肺心病”這一鏈條具有高度一致性。
肺氣不足是肺脹發生的前提和基礎[20],六淫是其主要外因,痰瘀內阻既是肺脹發生、發展的病理產物,也是導致其遷延難愈的主要內在原因[21]。慢阻肺的發生發展主要為平素肺脾腎虧虛,外邪引動內飲,一般為寒邪,導致痰瘀內阻,肺氣失宣,腎不納氣,出現喘累、氣促加重。肺脹患者平素易感冒,在氣候變化、季節交替時易加重。綜其原因多為平素肺氣虛弱,肺為水之上源,肺氣不足,則津液疏布障礙,水飲阻肺,肺氣郁滯,則可出現一系列的肺失宣降的表現。若處南方地區,其氣候陰冷潮濕,濕邪氤氳,加之南方人嗜食肥甘厚味,濕熱焦灼于內,綿延難去。素體虧虛,濕熱之邪更凝結不除,而困阻脾胃、中焦,而致痰飲內聚。五臟六腑功能失調,久病多虛,多瘀。痰飲、濕熱內阻,成為惡性循環。若發展至肺脹后期時,終致肺脾腎虧虛,心陽虧耗,腎水不暖,水飲凌心,出現咳嗽、喘累加重,心悸、雙下肢水腫等癥狀。
2 西醫發病機制研究
目前西醫對COPD的病因及發病機制仍未完全清楚,國際公認的慢阻肺發病的三大關鍵機制為炎癥機制、蛋白酶—抗蛋白酶機制、氧化應激機制,而吸煙、環境污染、粉塵以及化學物質接觸等是導致COPD最主要的危險因素[22]。當前對COPD病因及發病機制的深入揭示,是COPD防治研究的基礎。
炎癥機制。在COPD急性加重期及終末期,炎癥因子在肺部活化、集聚是導致癥狀加重的內在因素。COPD患者體內的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巨噬細胞等聚集會引起肺組織結構破壞、肺部實質慢性炎性改變,如白介素-1(IL-1)、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等炎癥因子過度釋放,并以此為惡性循環導致疾病進行性加重。其中TNF-α是由巨噬細胞和單核細胞分泌的一種重要的細胞因子,可促進中性粒細胞吞噬,而中性粒細胞通過釋放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使細胞增殖和分化,聚集形成慢性粘液高分泌狀態,會導致肺部進一步損傷。當TNF-α大量釋放時,將成為炎癥反應的始動因子及最重要的內源性介質,可導致IL-6、IL-10、IL-8等炎癥因子的合成及釋放,引起級聯反應,導致炎癥細胞的進一步放大,使人體出現病理損傷。白細胞介素在炎癥反應中也起重要作用,如IL-1,IL-6,IL-8等炎癥因子,可以介導炎癥反應、調節免疫、機體代謝等,其中以IL-1β為主。有研究證實,白細胞介素-1β(IL-1β)和白細胞介素-17A(IL-17A)是流感引起的慢性肺部炎癥加重中的中性粒細胞炎癥的關鍵介質,IL-1β誘導嗜中性粒細胞的增多,在肺功能障礙及病毒感染階段起到了驅動作用[23]。促炎細胞因子TNF-α被認為能夠誘導PMN(多形核白細胞)中IL-1β的基因表達[24],而抑制IL-1β可以降低TNF-α和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的含量[25]。以上分析可以看出TNF-α是參與慢阻肺炎癥反應的關鍵炎癥因子[26],白細胞介素在炎癥反應的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機制。目前研究認為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是引起COPD的經典機制。其中細胞外基質(Extral cellear memberma,ECM)是由細胞分泌到細胞外間質的構成肺泡壁的重要大分子物質。正常狀態下可調節組織的發生和細胞的生理活動。但當蛋白酶增多或抗蛋白酶不足均可破壞ECM,導致肺組織消融,肺泡間隔破壞,肺泡腔擴大,而致肺氣腫[27]。蛋白酶主要分為外源性和內源性蛋白酶,多數為內源性蛋白酶。目前研究發現以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 (neutrophil elastase,NE)和巨噬細胞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與COPD的發病密切相關[28]。抗蛋白酶主要以a1-抗胰蛋白酶(a 1-AT)為代表,其活性強,可抑制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酶、胰蛋白酶、凝血酶等多種絲氨酸內切肽酶。抗蛋白酶可通過對抗蛋白酶的水解、催化作用,抑制感染和炎癥的發展,從而延緩慢阻肺的發生[29]。有研究表明先天性a1-抗胰蛋白酶缺乏的患者,與肺氣腫的患病率呈正相關[30]。當NE活性過度時,易誘發肺組織損傷、免疫功能下降,而a1-AT是NE的天然抑制劑,若a1抗膜蛋白酶分泌減少時,蛋白酶-抗蛋白酶機制失衡,則易誘發肺氣腫[31]。
氧化應激機制。氧化-抗氧化失衡是目前公認的導致COPD的三大發病機制之一,其已日益受到研究者重視。在正常情況下,氧化-抗氧化反應可保持動態平衡,不會引起機體損傷,但當二者失衡時會產生氧化應激反應,廣泛參與機體的病理損傷過程,引起脂質,蛋白質和脫氧核糖核酸等一系列的損傷[32]。其原因是當體內有大量活性氧自由基產生并遠超出機體抗氧化防御體系所能清除的能力時,會導致氧化應激的發生,引起細胞死亡和組織損傷,從而誘導COPD疾病的發生和加重。機體的肺部組織一直處于高氧狀態下,加之其擁有較大的呼吸膜面積及豐富的血供,極易受到內源性氧化劑的損害[33]。氧化-抗氧化失衡引起機體的氧化應激促進COPD發生,而且也是導致COPD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4]。在COPD的急性發作中,氧化應激所激發超氧離子及細胞因子在COPD的發病機理中起著重要作用。COPD患者氣道氧化應激水平增加,氧化應激促進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與其受體的結合,導致肺泡細胞調亡和肺氣腫的形成。大量的氧化劑可以影響粘液分泌和黏膜纖毛清除能力,加重COPD的損傷。Santos’等[35-36]研究認為,氧化應激反應參與肺脹發生、發展的整個過程。在氧化和抗氧化反應中,丙二醛(MDA)是脂質過氧化代表產物之一,它可反映氧化應激的嚴重程度,且間接反應機體細胞受自由基攻擊的嚴重程度。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是機體內重要的抗氧化劑,其氧化活性代表了體內抗氧化能力的高低[37]。實驗研究證明[38-39],無論在COPD急性發作還是緩解期,血清MDA濃度均升高,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均降低。治療后血清MDA濃度下降,而SOD活性顯著增高,提示COPD存在氧化-抗氧化失衡,氧化應激會對氣道和肺組織造成直接損傷。
3 小 結
中醫認為,肺脹發病機理主要誘因為外感六淫邪氣、飲食起居不當、情志失調等;主要病理產物為痰飲、瘀血。本虛為肺脹發病的內在因素,即肺脾腎三臟虛弱,隨著病情進展導致五臟俱損,后期以肺腎心三臟虛損為主。
西醫認為,COPD 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清楚,有炎癥機制、蛋白酶-抗蛋白酶機制、氧化應激機制及其他發病機制。慢阻肺相關的文章雖已不少,但就其發病機制論述仍不完整,尚須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