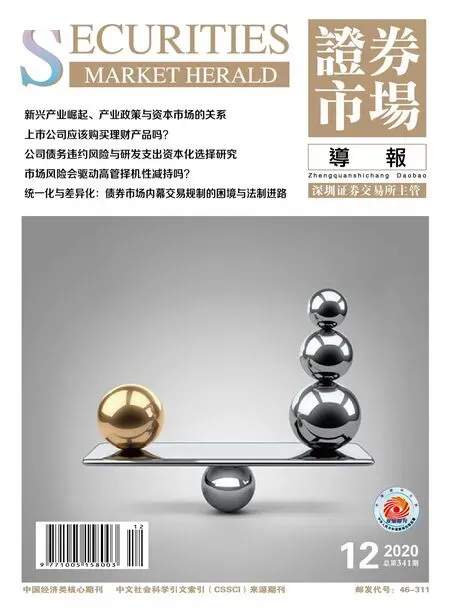基金經理性別、信息依賴與風險承擔水平
郭白瀅 龍翠紅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上海 200041)
一、引言
隨著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市場跨越式發展,基金已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以及個人投資的重要選項。在基金的管理與運作過程中,基金經理個人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很多情況下,“選基金就是選基金經理”,基金經理的個體特征與其投資風格以及業績表現之間的關系成為投資者非常關心的問題。在基金經理諸多個體特征當中,性別是一個基本而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性別與基金經理投資風格以及業績表現緊密相關,而且與其他個體特征變量還具有顯著的交互相應(Agnew et al.,2003;Barber and Odean,2001;Niessen-Ruenzi and Ruenzi,2013)[1][3][19]。
已有的社會學與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由于對風險的度量、感知以及偏好的不同,女性相對男性更為謹慎和保守(Byrnes et al.,1999;Fang and Wang,2015;Malmendier et al.,2011)[7][12][18]。在投資領域,現有研究也普遍支持這種觀點,認為女性基金經理在決策過程中更加厭惡風險,男性基金經理更加自信并且持有組合的風險也更高(Agnew et al.,2003;Barber and Odean,2001;Niessen-Ruenzi and Ruenzi,2013)[1][3][19]。這可能導致女性基金經理所持資產組合的風險承擔水平低于男性同行。但是,在風險偏好(原因)與組合風險承擔水平(結果)之間的中介變量值得進一步研究,尤其是決策方式方面的特征。本文期望檢驗基金經理的風險承擔水平是否具有性別差異,并且從信息依賴的角度對這種性別差異給出一個行為方面的解釋。
首先,本文對于基金經理組合的風險承擔水平進行測度,并檢驗其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根據Kempf et al. (2009)[16],基金投資組合與市場中其他基金組合(以下簡稱市場組合)越接近,則其承擔的風險也就越小。因此,可以用二者的接近(偏離)程度來反映組合的風險承擔水平。本文基于基金持股數據建立了基金持股網絡模型,設定規則如下:選定基金持股比例前10位的股票,如果兩只基金持有同一只股票,則他們之間具有一個“連接”。這樣,在網絡中代表該基金節點的度(即它與其他節點之間“連接”的數量)就表征了其持股組合與市場組合的接近程度。檢驗發現,女性基金經理持股組合與市場組合的接近程度明顯高于男性同行,即她們的風險承擔水平更低。但是,如果進一步擴大選股范圍,則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將逐漸消失。
其次,本文檢驗了基金經理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信息依賴這種決策方式特征可以作為風險偏好與組合風險承擔水平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量。基金經理在決策過程中使用的信息包括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私有信息是指在基金經理之間小范圍傳播的信息,通常以社會關系網絡為媒介;公共信息是指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和分析師的評級與預測,市場的所有投資者都可以獲得。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都是基金經理決策的依據,但它們在獲取渠道、傳播范圍以及不確定性等方面存在明顯差別。相比公共信息,私有信息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對其的倚重將給基金經理的決策帶來更大風險,因此,保守的基金經理傾向于更多依賴公共信息。同時,依賴私有信息使得基金經理的持倉組合偏離市場組合,而依賴公共信息的效果正好相反。本文參考了Pareek(2012)[22]提供的方法建立了基金信息網絡,即基金經理之間交流私有信息的社會關系網絡,通過檢驗基金與其信息網絡成員持倉水平變化之間的關系以證實他們之間私有信息傳播影響的存在性、程度以及性別差異。研究發現,相比男性基金經理,女性基金經理在決策過程對于私有信息的倚重更小,而對公共信息的倚重更大。這可以作為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性別差異的一個解釋。
最后,本文通過引入交互項進一步考察了市場行情與決策情形對于基金經理信息依賴性別差異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牛市時基金經理對于兩類信息的依賴都存在性別差異,女性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的依賴更小,而對公共信息的依賴更大;在熊市時只有對于公共信息的依賴存在性別差異,而這時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的依賴都普遍下降。此外,在調倉、建倉和平倉不同的決策情形下,女性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的依賴都低于男性。在調倉時公共信息對于女性基金經理的影響更大。而在建倉和平倉情形下,公共信息對于基金經理決策的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平倉時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最大,而調倉時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最小。
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第一,現有關于信息對于投資者決策行為影響的研究尚不能有效分離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各自的影響,本文將社會關系網絡引入投資者行為的研究中,為此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嘗試;第二,不同于現有文獻對于投資風格性別差異的解釋止于社會心理與風險態度,本文從信息傳播與決策過程的角度對于這種差異給出了進一步的行為解釋;第三,本文采用網絡結構特征變量表征不同基金持股組合之間的關系,為機構投資者持倉組合的相似性以及管理者決策保守性的測度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
二、文獻回顧
與本文研究主題最為相近的文獻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基金經理風險偏好與業績表現的性別差異,其二是信息網絡對于基金經理決策行為和資產價格的 影響。
(一)基金經理風險偏好與業績表現的性別差異
關于基金經理風險偏好的性別差異,Agnew et al. (2003)[1]和Barber and Odean(2001)[3]研究發現,相比男性同行,女性基金經理對于風險更加厭惡,而且她們過度自信的程度更低;女性基金經理持倉組合的風險相對更低,她們對于風險控制比男性更好。Niessen-Ruenzi and Ruenzi(2013)[19]研究指出,女性基金經理一般不會采取極端的投資風格,且其投資風格的持續性強于男性,規模大和聲譽好的公司更傾向于雇傭女性。史金艷等(2016)[32]研究發現,女性基金經理管理基金的風險承擔水平顯著低于男性,并且學歷越高、任期越短,女性基金經理降低風險承擔水平的作用越明顯。高鶴等(2014)[27]利用配對樣本方法研究發現,與男性基金經理相比,女性基金經理持有投資組合的市場風險水平更低,她們更適合為風險厭惡程度較高的投資者服務。
對于基金經理業績表現性別差異的實證研究很多,但結果存在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女性基金經理與男性同行在業績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例如,Bliss and Potter(2001)[4]、Dwyer et al.(2002)[11]以及Hu et al.(2012)[15]都研究表明,女性經理管理基金的風險調整收益顯著高于男性。雷衛與何杰(2018)[28]研究發現,在市場下降期女性基金經理的業績強于男性,而在震蕩期和上升期基金經理性別對基金業績的影響不顯著。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女性基金經理與男性同行在業績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例如,Kostovetsky(2009)[17]基于美國共同基金的研究發現,從調整后的收益來看女性基金經理和男性基金經理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晏艷陽和鄧開(2015)[34]研究表明,牛市中基金業績的性別差異不明顯,而熊市中女性基金經理的表現更好,這可能與女性基金經理風險厭惡程度較高、從而能夠很好控制風險有關。
(二)信息網絡對于基金經理決策行為和資產價格的影響
現有文獻構建機構投資者信息網絡主要有以下兩種方法:一種是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直接確定機構投資者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交流,以此為基礎構建他們之間的信息網絡(Arnswald,2001;Shiller and Pround,1989)[2][24];另一種是通過檢驗具有某種共同屬性(例如社會關系、地理位置以及資產配置等)機構投資者行為的一致性來驗證他們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交流(Butler and Gurun,2012;Pareek,2012;Pool et al.,2015)[6][22][23]。目前第二種方法的使用范圍更廣。
關于信息網絡對于基金經理決策行為的影響,Pool et al.(2015)[23]研究提出,具有社交關系的基金經理擁有相似的資產配置和交易風格;Pareek(2012)[22]基于重倉持股關系建立了基金經理信息網絡,發現在控制了投資風格和地理因素后,同一信息網絡中基金的交易行為表現出顯著的一致性。Colla and Mele(2007)[9]對于循環網絡的研究發現,在網絡中關系較為“緊密”的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而在網絡中關系較為“疏遠”的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存在負相關性。肖欣榮等(2012)[33]為Pareek(2012)[22]的發現提供了中國市場的證據,而且發現信息網絡對于基金的影響在熊市和震蕩市時顯著,而在牛市時不顯著。Ozsoylev et al.(2014)[21]研究發現,處于網絡中心地位的投資者能夠獲得比其他投資者更高的回報率,并且他們對于信息的反應速度也要比非核心網絡成員更加迅速。
關于信息網絡對于資產價格的影響,H a n a n d Yang(2013)[13]建立了一個理性預期均衡模型,說明了在市場信息總量固定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網絡中投資者的交流改善了市場效率,降低了資金成本,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但在均衡狀態下,其將減少信息的獲取,從而對市場效率與資金成本具有負面影響。Ozsoylev(2011)[20]提出了一個理性預期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投資者通過信息網絡進行社會學習),發現網絡中心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劉京軍和蘇楚林(2016)[29]研究顯示,基金網絡結構對基金的資金流量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可以給基金帶來顯著的業績增長,基金網絡促進了基金經理行為一致性的提升。陳新春等(2017)[26]研究表明,基金之間信息分享網絡的密度不僅會增加股票的總體和特質風險,而且會顯著加大股票極端下跌和極端上漲的概率,尤其對極端下跌影響 更大。
現有文獻主要基于基金凈值增長率標準差、貝塔系數以及風險調整意愿等指標衡量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本文采用了新方法進行測度,即直接測度基金組合與市場組合的接近程度,因為組合與市場組合越接近,其所承擔的風險就越小。此外,現有研究主要通過比較投資組合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來驗證女性基金經理與男性基金經理風險偏好的不同,但在前者(結果)與后者(原因)之間存在著決策方式這個中間變量。本文引入了基金經理行為差異,建立了從性別差異到行為差異、再到結果差異的完整影響路徑。具體來說,本文基于基金信息網絡研究了基金經理在決策過程中對于能夠帶來不同決策風險的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的依賴。本文豐富了基金經理個體特征與其投資風格之間關系的研究,所采用的社會關系網絡分析方法可以作為其他行為特征研究的借鑒。
三、研究設計
(一)基金持股網絡與基金信息網絡
假設在第t期市場中滿足條件的基金構成集合N={1,2,3,…,n}。基金i∈N持倉市值占凈值比例排名前m位的股票構成集合Si。如果對于基金i,j∈N,股票a∈Si∩Sj,即兩只基金同時持有股票a,則兩只基金之間存在一條邊eij∈E。如果兩只基金共同持有的股票超過一只,它們之間就存在多條邊。這樣,節點集合N與邊集合E就構成了一個無向有環網絡G(N,E),本文將其稱為第t期的基金持股網絡。
投資者在決策時通常都會通過社會關系獲取私有信息(Cohen et al.,2008)[8]。社會關系網絡是基金經理之間私有信息傳播的主要媒介與有效范圍,包括校友關系(Pool et al.,2015;申宇等,2016)[23][31]、地理相鄰關系(Hong et al.,2005)[14]以及資產配置相似關系(Pareek,2012;肖欣榮等,2012)[22][33]等。本文將基金經理之間以私有信息交流為目的的社會關系網絡定義為基金信息網絡。
然而,根據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基金信息網絡存在一定難度:其一,信息網絡是多種社會關系網絡相互作用和疊加的結果;其二,基金經理之間存在社會關系并不意味著他們之間會進行信息交流;其三,基金經理的社會關系難于確定。因此,本文用基金重倉持股網絡來代替信息網絡,理由如下:首先,如前所述,機構投資者重倉某項資產通常是因為擁有私有信息,因而重倉同一資產很可能是他們之間相互共享信息的結果(Bushee and Goodman,2007;Cohen et al.,2008)[5][8],且他們存在共享信息的激勵(Crawford et al.,2017; Stein,2008)[10][25];其次,在控制了公共信息影響之后,重倉持有同一只股票的機構投資者的交易行為具有很強的一致性,說明他們之間大概率存在信息交流(Pareek,2012;陳新春等,2017;肖欣榮等,2012)[22][26][33]。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構建基金i的重倉持股網絡Gi(Ni,Fi),其中集合Ni和Fi分別表示與基金i共同重倉持有相同股票的基金集合(節點集合)以及這些基金與基金i之間的連接集合(邊集合):假設基金i在第t期重倉持有的股票構成集合Li,如果對于基金j∈Ni,存在股票a∈Li∩Lj,即兩只基金都重倉持有該股票,則它們之間存在一條連接fij(兩只基金可能共同重倉持有多只股票,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只用一個連接表示)。滿足條件的基金以及連接分別構成了集合Ni和Fi,且構成了一個有向無環網絡Gi(Ni,Fi),即基金i的重倉持股網絡。遵循相關文獻,本文將重倉的標準設定為5%,即某一季度基金持有某只股票的市值占該基金凈值的5%以上。如前所述,本文用基金重倉持股網絡替代基金的信息網絡。
(二)基本模型與方法
1.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測度與性別差異檢驗
對于基金持股網絡來說,節點的度(degree)是由基金與市場組合的接近程度決定的。具體來說,如果基金的持股組合與市場組合越接近(即選擇了市場中越多基金共同持有的股票),則網絡中節點的度就越大,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就越低。目前,現有文獻主要采用凈值增長率標準差、貝塔系數以及風險調整意愿等指標從基金主動承擔風險的角度間接衡量基金風險承擔水平。本文引入基金持股網絡,并且用節點的度來反映基金風險承擔水平,從定義看這個指標相比傳統指標更加直觀。
在用基金持股網絡中節點的度來代表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基礎上,本文采用以下兩種方法來檢驗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1)置換檢驗
本文采用以下步驟進行置換檢驗:(1)將基金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在對照組中,基金管理團隊成員均為男性,用變量fgender=0表示;在觀察組中,基金管理團隊至少包含一名女性成員,用變量fgender=1表示;(2)執行1000次隨機置換計算,得到節點度組間均值之差的抽樣分布;(3)計算實際兩組均值之差的顯著性水平,得出結論。由于這是以置換為基礎的假設檢驗,因此不需要常規的樣本獨立性假設和隨機假設,比較適合網絡數據(劉軍,2018)[30]。
(2)回歸分析
本文構建方程(1)檢驗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與其性別之間的關系:

其中,degree是基金持股網絡中節點的度。fgender是基金管理團隊性別變量,取值設定如下:(1)用mgender來表示基金經理的性別,mgender=0代表男性,mgender=1代表女性;(2)基金管理團隊性別變量fgender為團隊中所有成員性別變量mgender的均值(包含了基金管理團隊只有一個基金經理的情況)。因此,團隊中女性成員數量越多,則fgender取值越大。controls為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2.私有信息與公共信息對于基金持倉決策的影響
根據Cohen et al.(2008)[8]和Hong et al.(2005)[14],信息互動對基金決策行為的影響表現為基金持倉決策的相關性。因此,本文通過檢驗基金與其信息網絡成員持倉決策的相關性,來證明和測度私有信息交流的存在性及影響程度。為此,構建方程(2):


表1 控制變量定義(一)

3.私有信息與公共信息對于基金持倉決策影響的性別差異
在方程(2)的基礎上,本文引入性別變量以檢驗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對于女性基金經理和男性基金經理持倉決策影響的差異,構建方程(3):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性統計
1.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選取2005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股票以及公募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樣本。考慮到指數型基金缺乏主動性,本文遵循同花順公募基金分類標準,去除了股票型基金和債券型基金中的指數型基金。基金重倉持股數據來自iFind數據庫,上市公司財務數據、股票交易數據以及基金基本信息數據等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基金經理信息來自和訊財經。本文基于樣本基金季報中的重倉持股數據構建基金信息網絡,并且據此計算基金持倉水平變化。這主要是考慮到雖然基金半年報包括了基金的持股明細數據,但我國基金具有較高的換手率,該頻率的數據不能及時反映基金持倉水平變化情況。本文還選取樣本基金半年報中的持股明細數據構建基金持股網絡,因為季報中只披露基金前十位重倉股,不能滿足對于基金經理更大規模組合風險承擔水平的比較。

表2 控制變量定義(二)
本文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如下常規處理:(1)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2)剔除數據缺失的公司;(3)通過不同數據源比對修訂有明顯錯誤和補全缺失的樣本數據;(4)剔除在基金構建組合時上市未滿一年以及研究期間內退市公司的股票;(5)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上下各0.5%的縮尾處理。
2.描述性統計
根據基金半年報數據,對于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女性基金經理占比的均值為0.159,最大值為0.236(2019年第四季度),最小值為0.080(2015年第二季度),期間一直保持增長趨勢。此外,完全由女性基金經理管理(包括女性基金經理單獨管理和基金管理團隊完全由女性構成)基金比例的均值為0.103,最小值為0.056(2006年第四季度),最大值為0.167(2018年第四季度),期間也一直保持增長趨勢。管理團隊包含至少一名女性成員的基金占比均值為0.113。由于完全由女性基金經理管理的基金與男性管理的基金在數量上差距較大,在分組比較時,將管理團隊包含至少一名女性成員的基金與其合并。根據2019年第四季度的數據,基金持股網絡度的均值為2392,標準差為1070,說明基金持股組合與市場組合相似度的個體差異較大。對于基金信息網絡,除去了信息網絡規模(即信息網絡中節點數量)小于5的樣本,這樣信息網絡規模的均值為77,標準差為41,說明基金在信息網絡成員數量上存在較大差異。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1.置換檢驗
本文通過置換檢驗的方法分析每個季度基金持股網絡中代表觀察組(基金管理團隊至少包含一名女性成員)和對照組(基金管理團隊全部由男性組成)基金節點的度的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以檢驗基金經理的風險承擔水平是否存在性別差異,結果如圖1所示。從中可以看到,2014年第四季度后除個別季度外,檢驗得到的p值均小于0.10,說明兩組均值的差異較為顯著。也就是說,女性基金經理的風險承擔水平顯著低于男性。在2014年第四季度前,兩組均值差異大部分情況下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觀察組樣本過少的緣故,如圖2所示。
2.回歸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9年數據對方程(1)進行估計,以檢驗基金經理性別與風險承擔水平之間的關系,結果如表4所示。從中可以看到,不同模型設定下的估計結果比較相近。在表4第1~3列中,fgender的系數顯著為正,這意味著隨著基金管理團隊中女性成員數量的增加,基金持股網絡中基金對應節點的度顯著上升,即基金持股組合的風險承擔水平下降。在第4列中,只保留管理團隊只有一個基金經理的樣本,用虛擬變量female代表基金經理的性別:female=0代表基金經理為男性,female=1代表基金經理為女性。可以看到,female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女性基金經理的風險承擔水平顯著小于男性同行。以上的結果說明,相比男性同行,女性基金經理的風險承擔水平顯著較低,與之前置換檢驗的結果一致。

圖1 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性別差異的置換檢驗

圖2 觀察組與對照組樣本量

表4 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

圖3 基金經理性別變量的顯著性
基于2005—2019年各年度的樣本數據,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對方程(1)重新進行估計,基金管理團隊性別變量fgender系數估計的p值如圖3所示。從中可以看到,fgender的系數在2014年第四季度后變得顯著,即女性基金經理的風險承擔水平顯著低于男性同行,與之前置換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
(三)基金經理持倉決策與信息依賴
本文對方程(2)進行估計,以檢驗基金經理持倉決策時對于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的依賴,結果如表5所示。從中可以看到,ΔHN與ΔHR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后者大于前者,說明私有信息與公共信息對于基金經理持倉決策都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且后者的影響相對更大。該結論與Pareek(2012)[22]、肖欣榮等(2012)[33]一致,基金經理對于公共信息的相對倚重使得股價具有較強的同步性。對比第1列的結果,第2列增加了股票估值變量(包括賬面市值比bm、總資產收益率roa以及換手率turnover等)和分析師預測變量(包括分析師評級rank與分析師關注analysts)。值得注意的是,ΔHN的系數在加入這些控制變量前后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說明代表市場中其他基金經理對于市場變化普遍反應的變量ΔHR已經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共信息的影響。第3、4列、第5、6列估計結果的對比同樣佐證了這個結論。

表5 基金經理持倉決策的信息依賴
(四)基金經理決策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對方程(3)進行估計,以檢驗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對于基金經理持倉決策的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結果如表6所示。從中可以看到,表的第3列中交互項fgender×ΔHN的系數顯著為負,而交互項fgender×ΔHR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比男性基金經理,女性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的依賴更小,而對于公共信息的依賴更大。在第4列中,只保留單個基金經理管理的基金樣本,得到的結果與之前一致。以上結果說明,基金經理決策信息依賴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這可能是由于女性基金經理相比男性同行風險厭惡程度更高,因此更加倚重不確定性相對較小的公共信息,而對于可能帶來較大風險的私有信息倚重較小。

表6 基金經理決策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

圖4 進一步擴大股票組合范圍的置換檢驗
五、進一步討論
(一)基金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擴大組合范圍
前文將基金持股范圍限定為持股市值占基金凈值比例前10位的股票,以此建立基金持股網絡模型,在此基礎之上檢驗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接下來,本文擴大選股范圍,以檢驗之前結果的穩健性,同時觀察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是否會受到組合規模的影響,結果如圖4所示。從中可以看到,如果以p=0.05為限,當股票組合規模N∈{20,30,40}時,2015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觀察組和對照組均值的差異仍然是顯著的,即女性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低于男性;當股票組合規模N∈{50,60},在很多季度二者之間的差異不再顯著,說明隨著選股范圍的擴大,這種差異可能變得不再明顯。以上結果說明,當選股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女性與男性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差異將減小或消失,這說明性別差異可能只體現在倉位占比居前的股票組合中。
(二)決策情形與基金經理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
本文將基金持倉決策的情景分為以下三種:調倉、建倉和平倉。調倉是指當期和前一期股票均屬于重倉股;建倉是指前一期股票不屬于重倉股,而當期成為重倉股;平倉是指前一期是重倉股,而當期不再是重倉股。前文分析均考慮調倉這一種情形,因為這種情況最為常見。由于這三種情景下的決策對于基金后續操作以及整體收益的影響方式和程度不同,基金所持態度和應用策略也具有明顯差異。因此,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的依賴程度可能存在差異,同樣也可能存在性別差異。

表7 決策情形與基金經理決策信息依賴性別差異
為了檢驗在不同決策情形下基金經理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本文在方程(3)的基礎上構建方程(4):

其中,interaction為其他交互項;scenario是決策情形虛擬變量:建倉時scenario=0,平倉時scenario=1,調倉時scenario=2。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和截尾回歸模型對方程(4)進行估計,結果如表7所示。采用截尾回歸模型是考慮到建倉和清倉基金樣本的特點(在這兩種情形下,基金倉位變化分別大于零和小于零)。從表7第1列、第3列以及第4列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決策情形下,fgender×ΔHN的系數都顯著為負,說明女性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的依賴程度都低于男性。而且從表7第2列可以看到,這種差異在平倉時最大,在調倉時最小,而建倉時居中。此外,在調倉時基金經理對于公共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顯著,而在另外兩種情形下,性別差異并不顯著。女性基金經理相比男性同行的風險厭惡程度更高,因此在進行持倉決策時對于不確定性較大的私有信息的倚重較少,而對不確定性較小的公共信息的倚重較大。這種傾向在基金經理調倉決策時表現得最為明顯。
(三)市場行情與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差異
市場行情往往影響了基金經理的投資心理與策略,因此本文進一步關注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性別差異與市場行情之間的關系。用基金持股網絡中節點度的標準差來代表風險承擔水平的個體差異,用fgender=0與fgender=1兩組樣本中節點度均值之差作為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性別差異,將以上兩種差異與上證綜指收益率進行對比,結果如圖5和圖6所示。從中可以看到,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個體差異與市場行情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即市場行情較好時,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個體差異較大,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188;而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與市場行情存在明顯的負相關性,即市場行情較好時,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較小,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144。以上結果的一個解釋是女性基金經理的風險厭惡程度變化對于市場行情更為敏感:市場行情較好時,女性基金經理的風險厭惡程度降低更多,此時基金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將減小;而市場行情較差時,女性基金經理風險厭惡程度提升更多,此時基金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將增大。同時,市場行情較好時,在機構投資者普遍看多的條件下個體的樂觀程度存在較大差異,表現為基金風險承擔水平差異較大;而市場行情較差時,在機構投資者普遍看空的條件下個體的謹慎態度比較一致,表現為基金風險承擔水平差異較小。

圖5 基金持股組合差異與市場行情

圖6 基金持股組合性別差異與市場行情
此外,本文將市場行情引入方程(3)中構建方程(5)和方程(6)以檢驗在不同市場行情下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對于基金經理決策影響的差異:

其中,interaction為其他交互項;state是市場行情變量,當市場處于上升期(牛市)時state=0,下降期(熊市)則state=1;ret_idx為上證綜指收益率。對于方程(5)和(6)估計的結果如表8所示。從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到,在牛市時基金經理對于兩類信息的依賴都存在性別差異,而在熊市時只有對于公共信息的依賴存在性別差異。從第3列可以看到,熊市相比牛市私有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下降,公共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上升。以上結果說明,在牛市時,女性基金經理由于更加謹慎而比男性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的倚重更小,而對公共信息的倚重更大;在熊市時,基金經理普遍比較謹慎,從而對于私有信息的倚重均有所下降,而女性基金經理更高的風險厭惡使其更加倚重公共信息。從第4列可以看到,ret_idx×fgender×ΔHN的系數為正,而ret_idx×fgender×ΔHR的系數為負,說明隨著市場行情的向好,基金經理對于私有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在增加,而對于公共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在減小。反則反之。以上結果說明,女性基金經理相比男性同行更為謹慎的態度表現為在市場行情較好時對于私有信息的倚重更小,而在市場行情較差時對于公共信息的倚重更多。此外,女性與男性基金經理對于公共信息倚重程度差異的減小,使得基金風險承擔水平的性別差異減小,與前文結論一致。

表8 基金經理風險承擔水平與市場行情
六、結論與啟示
基金經理的個體特征是其投資風格的決定因素。在基金經理諸多個人特征(如年齡、經驗、性別以及教育背景等)中,性別是一個基本而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對于女性基金經理在投資決策方面是否更加保守尚存在爭議,且這些研究通常從女性基金經理與男性基金經理投資結果(如風險承擔意愿、投資組合與投資業績等)的差異判斷性別因素的影響,沒有對投資行為這個中介變量進行分析。本文期望在檢驗女性基金經理是否相比男性同行更加保守的基礎上,進一步從信息的傳播與基金經理對于不同渠道獲得信息倚重程度的差異的角度分析他們投資行為的不同,為其保守性差異給出一個行為 解釋。
基于2005—2019年我國A股與公募證券投資基金市場數據,本文利用基金持倉網絡結構特征指標測度了基金經理持股組合的相似度,并且基于基金信息網絡分析了不同性別基金經理在投資過程中對于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的依賴程度的差異。研究發現:第一,相比男性同行,女性基金經理的持股組合與市場組合的接近度更高,因此她們具有更低的風險承擔水平;第二,女性基金經理在決策過程中對于私有信息的依賴程度更低,而對于公共信息的依賴程度更高,這可以作為其持倉組合具有較低風險承擔水平的一個解釋;第三,對于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依賴的性別差異受到決策情形(調倉、建倉和平倉)和市場行情(牛市和熊市)的影響。
本文將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與方法引入機構投資者的行為分析中,采用基金持股網絡的結構特征變量表征不同基金持股組合之間的關系,為機構投資者持倉組合的相似性以及管理者決策保守性的測度提供了一種新方法;同時,基于基金信息網絡(基金經理社會關系網絡的一種形式)分離了私有信息和公開信息對基金經理的影響。本文豐富了基金經理個人特征與投資風格之間關系的研究,所采用的社會關系網絡分析方法可以作為其他行為特征研究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