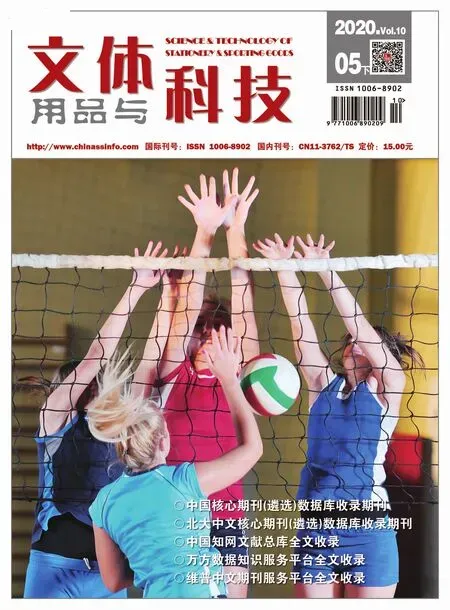電子競技與體育關系
(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 廣東 廣州 511400)
1、前言
在近幾年,電子競技發展飛速,在2013年3月,國家體育總局選出了一支電競隊伍代表國家參加 “第四屆亞洲室內和武道運動會”,這個決定引起了一些國內體育運動員的不滿,跳水運動員何超在網上發聲,認為電子競技不是體育;隨之,中國體操運動員何一冰也提出質疑,他質疑電子競技是否真的屬于體育范疇,這一網絡輿論爭斗引起了廣大網民的熱議,引發了體育與電子競技之間關系的爭議,有人認為兩者之間關系密切,并且屬于體育的范疇。有人則認為兩者毫無關系,并且排斥電子競技,認為電子競技的存在是弊大于利。本文意在通過論述體育概念的基礎上,對電子競技與體育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分析,希望可以對電子競技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2、體育的定義
2.1、國外體育定義
柏拉圖是最早定義“體育”的哲學家,他將體育定義為是一種簡單并且較為靈活的體育訓練,是為了備戰而進行的訓練。”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一個名詞——é ducation phy-sique,這個詞代表著身體教育,在1762年時,盧梭名著 《愛彌兒》中第一次使用了這詞;斯賓塞在1861年出版了《教育論》,其中包含了《怎樣的知識最有價值》《德育》《智育》《體育》等四個篇章,明確地把體育置于教育之中。1994年美國體育標準文件里指出,體育的標準是,“學生要保持身體活動,維持健康水平,需從知識和技能來實現。該標準提出學生要定期參加體育活動和學習體育知識、技能,通過身體活動,使骨骼肌產生能量消耗。2016年英國拉夫堡大學機構庫,HARRIS在定義體育概念時,他提出“體育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循序漸進的學習方式,在學校課程中設置了體育課程,并且分配好上課時間。體育課程包括“基礎學習”和“進階學習”。
2.2、國內體育定義
現代體育來源于西方,“體育”是從日本傳入中國,體育的概念源自于英語的翻譯:gymnastics譯為體操,physical education譯為身體教育,sports譯為體育教育、運動,physicalculture譯為運動文化,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譯為體育教育和運動。在1980年,熊斗寅提出了“體育”要有大概念的觀點。他認為:根據整體性原則,體育實踐和傳統用語,體育應該被稱為 “大體育”;這個詞能反映國際體育的潮流,它包含了體育教育、社會體育和競技體育。崔穎波通過研究,日本“體育”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是“身體教育”階段、第二個是“通過運動進行教育”階段,第三個是“運動教育”階段,與日本相比,我國正處于“運動教育”的階段,所以,用“運動教育”來解釋“體育”是最合理的。另外一派是真義體育,通過比較俄語、日語、英語等不同語種的體育概念后,韓丹認為這幾種語言中,對體育的解釋都有“身體的”,“教育”或“培訓”等詞語,翻譯成漢語那就是“身體教育”或“體育”,所以“身體教育”就是“體育”。王廣虎認為體育是以優化發展為基本指導思想、以主客體同一為基本活動特征、以身體活動為基本活動方式、以身體力行為基本活動要求的,對自身自然實施改造的人的活動。
3、電子競技概念
國家體育總局對電子競技作如下定義:電子競技是通過先進的軟件和硬件設備,以軟件和硬件作為運動器械,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智力、思維對抗運動。此外,國內的一些學者也對電子競技進行定義,馮宇超認為電子競技是通過電子游戲平臺,根據參與者的比賽成績,從中比較參與者游戲競技水平高低的一種競技項目。王俊認為電子競技是用網絡設備作為運動的器械,遵循體育比賽規則,將電子游戲和比賽進行有機的結合,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進行人與人之間對抗的體育運動。何慧嫻認為電子競技是人和人之間的競技,是一種提高人的反應能力、思維能力、合作能力和智力的一種運動。
4、電子競技與體育的關系
4.1、電子競技具備高強度運動特征
在2007年時,Aadahl等人指出,通過分析個人基礎代謝率(MET)的倍數,使用絕對強度來確定運動強度。由于MET可以用來確定勞累,所以通過玩電子游戲時,觀察MET變化,以此建立聯系。另外,在2010年時,Stroud等人表明也可以使用氧氣水平(VO2)確定運動強度,適度的體育鍛煉會產生40%-60%的VO2儲備或4-6 MET。在2013年時,在Bronner等人的一項研究中,男性和女性參與者在參加涉及舞蹈的電子游戲時MET提高了4-9。在一些傳統體育項目中,比賽中表現出的身體性非常明顯,如籃球、跳水、足球等等,這些運動項目的比賽對體力和身體技術要求非常高,而電子競技對體力和身體技巧的要求相對較小,盡管電子競技與傳統體育項目相比,電子競技在體能方面的要求相對較小,但是電子競技對身體機能依賴性仍然很強,它們只是身體部位訓練的不同而已,電子競技對參與者反應速度和手指靈活性的要求極高,只有比對手有更快的反應速度和更完美的手眼協調能力,才會有更大的獲勝機會;另一方面,電競競技比賽對選手的負荷強度、體力耐力、注意力、心理承壓能力的要求都非常高,因此,電子競技也和傳統體育項目一樣,在心理上和身體上都具備高強度運動特征。
4.2、電子競技促進身心健康的發展
電子競技在部分人眼中,就是“惡魔”,它會讓人迷失其中,并且有害健康,覺得它的存在是在浪費人的時間和消耗人的精力。其實,電子競技也有積極作用,在電子競技類游戲中,有很多競技游戲對傳統體育項目進行虛擬模擬,如各種球類游戲、賽車類游戲、射擊類游戲等等。這擺脫了天氣和場地的束縛,無論何時何地都可進入虛擬環境進行運動。還有一些關于政治、經濟、軍事的戰略游戲,這些游戲規定每局的游戲時間,一局定勝負,所以游戲者不容易上癮,參與該類型競技運動的人,并不都從事國家政治、金融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工作,但可以提升參與者的綜合能力,所以電子競技運動對參與者的身心有積極的影響。所以電子競技并不是片面的“惡魔”形象,電子競技也有“天使”的形象;另一方面,電子競技是通過手指、眼睛和大腦之間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進行的競技活動,對選手肢體和器官之間的協調能力有較高的要求,在大腦給肢體發出指令后,相關的肢體迅速地執行指令,作出特定的動作反饋大腦的指令。適當地進行電子競技活動,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能力,從而使得身體更加協調,更加靈活,并且在電子競技活動中,大腦充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大腦對虛擬的事物進行分析、思考,把虛擬化轉化為具體化和形象化,然后迅速地做出反應。例如:觀察、記憶、想象、分析、應變能力等,這系列的合理運用,會提高大腦思維的敏捷性,同時智力也得到合理的開發。所以電子競技可以提高人的思維能力、反應能力、協調能力。但是,并不意味電子競技類運動對人的健康沒有危害,進行長時間的電子競技,與過度的體育鍛煉一樣,同樣會危害參與者的身心健康。
4.3、電子競技具有教育意義
還有部分人認為電子競技只是消遣時間的一種方式,與體育沒什么關系,更談不上教育,其實電子競技具有教育的功能。2004年,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委托的“電子競技課題組”對電子競技的概念進行定義,明確地指出電子競技與其他益智活動一樣,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Bejjanki等人表明,在動作視頻游戲體驗之后,在各種任務上觀察到的增強表現,在文獻中通常被定義為“轉移效應”,其中,在一個任務上的訓練后,在面對新任務時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可是,最近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認為動作視頻游戲體驗向用戶傳達了快速和有效地學習執行新任務的能力,而不是對新任務產生立竿見影的好處。換句話說,游戲玩家已經“學會了學習”。在感知和運動領域觀察中,得到了與該替代框架一致的數據。如今,科技迅速發展,VR、AR和可穿戴技術日益成熟,各種傳統運動項目與電子競技融合在一起,從中學習各種運動的技術動作及戰術策略,從而提高學習者的運動能力及技戰術水平,所以電子競技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
5、小結
電子競技具備高強度的運動特征,它可以促進人的身心健康發展,并且具有教育功能,它屬于體育的范疇。在2003年,國家體育總局就正式批準,將電子競技列為第99個正式體育競賽項。并且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體育產業統計分類(2019)》,將電子競技正式歸類為職業體育競賽表演活動。其實電子競技“實已至,而名未歸”而已,隨著電競的迅速發展,曾被視為青少年的“慢性毒藥”,慢慢地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現在電子競技還處于萌發期,還沒完全得到廣泛人的認可,但是這只是時間的問題。在今年的12月16日,國際電子競技聯合會(Global Esports Federation,以下簡稱為GEF)在新加坡正式成立。GEF是在國際奧委會電競兩項“政策”出臺后,在全球范圍內成立的國際電子競技單項組織。國際電子競技聯合會的成立意味著電競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電競競技的發展在日后將會傳統體育項目一樣成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