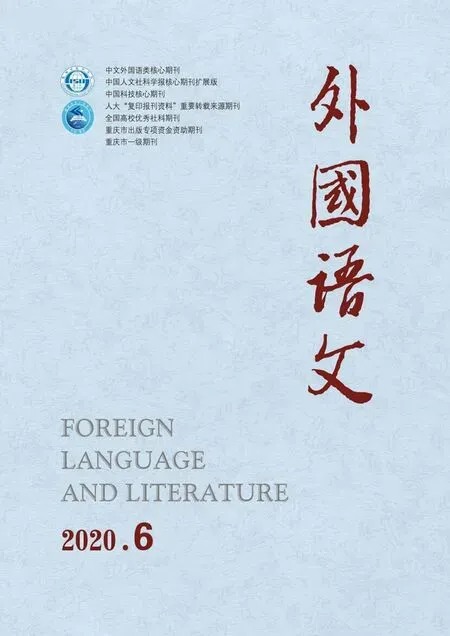行走者的生存之旅
——彼得·漢德克小說《短信長別》中的空間實踐
張赟 楊欣怡
(四川外國語大學 德語系,重慶 400031)
0 引言
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空間轉向”這一范式轉換,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對空間問題的本體論討論,聚焦人類活動與空間的互動關系,將人的精神意識、身體行為、社會活動及生存狀態等問題納入對空間理論的考察中。在空間轉向視閾下,人往往被視為現代社會空間的創造者和擁有高度空間感知力、想象力和行為力的主體,與日常生活空間有著無法斷裂的緊密聯系,在面向世界的生存、活動與體驗中,主體的空間實踐被不斷強調,成為探究人與空間關系的核心詞之一。其中,德國當代人類現象學家博爾諾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在其《人與空間》(MenschundRaum)一書中提出了“被經歷的空間”(erlebter Raum)這一概念,通過剖析人類隱匿于日常生活中基于不同空間表征的實踐行為和感知特征,將人與空間的互動關系揭示出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賽爾托(Michel de Certeau)的空間實踐理論則將日常生活作為思想論述的邏輯起點,通過對主體在空間中的實踐行為——散步與行走的分析與闡釋,對主體獲得“一種深度的審美生存” (張榮,2011:85)進行深刻論述,由此挖掘了主體與城市空間之間的緊密關系。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代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發表于1972年的小說《短信長別》(DerkurzeBriefzumlangenAbschied)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了作為奧地利作家的“我”在面臨現實生活的婚姻危機之時前往美國旅行并因此穿梭美國境內的故事。從文本的敘事層面來看,敘述者“我”的新大陸之行自東向西,由16個翔實的地理站點串聯起來。在與妻子尤迪特“貓捉鼠”般的暗自較量中,主人公沿著西進之旅的路線,在其途徑的站點時而漫步游蕩,時而駐足觀望,行走、觀察、反思與回憶構成其行為活動的主要特征。其中,不斷向前的游走行為成為小說主要的情節推動力,伴隨當下凸顯的城市感知和體驗,主人公在鏡像般的旅程中完成了對過往記憶的尋找以及生存狀態的反思,現實生活與內心世界的危機得以化解和治愈。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韓瑞祥教授在其擔任主編的《短信長別》譯本前言中提及,該小說采用客觀冷靜、具體寫實的風格,融傳統發展、偵探和多愁善感的旅行小說模式于一體(漢德克,2013:前言6)。筆者看來,小說演繹的“在路上”這一旅行模式則憑借有跡可循的地理空間指稱,使得文本在內容與結構層面極具畫面感,甚至具備公路電影的某些元素。本文將聚焦小說主人公的旅行行為,以其“行走于城市”這一空間實踐作為出發點,結合博爾諾夫和德·賽爾托的空間理論,探討主人公如何在一次次的行走中明晰自己的生存狀態以及如何走出現實生活的困境,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1 作為空間實踐的行走
自19世紀以來,伴隨大城市的興起,步行逐漸成為一種大眾活動(Hummel, 2007:12)。如今,行走早已構成現代人日常生活最為普遍的行為方式,賦予其置身世界、獲取感受的可能性。行走的方式多種多樣,或向前,或迂回,或短暫停留,甚至不以到達某個具體的站點為目標。與其他空間活動相比,行走以身體在場、緩慢、在路上等狀態作為本質特征,將主體從功能性、目的性的“操勞”中解放出來,通過行走者的步伐,在窺視、觀察和感受空間的過程中,獲取最真實的認知體驗,建立起外部世界于自我的意義和界限。德語成長小說里的年輕游歷者,浪子詩人波德萊爾及哲學家本雅明筆下的都市閑逛者,均代表和體現與自身、他者及世界進行交互的現代漫步者的形象。
德·賽爾托在其著作《實踐的藝術》(KunstdesHandelns)一書中,試圖將視角探向大眾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環節,探尋日常生活的意義并尋求對抗現代生活異化的策略,從而考察蘊含其中的邏輯關聯并建構出一套獨特的日常實踐理論。他在開篇曾寫道:“獻給一般人。獻給生活中的英雄,無處不在的人,行走于路上的大眾。在我敘事的開端,借著召喚這個引發我敘事開展與必要性之從未出現的人物,我探究一個欲望,這個欲望所無法企及的對象,恰好是這個從未出現的人物所代表的……”(Certeau, 1988: 9)。德·塞爾托以“行走街頭的無名英雄”構建起其日常空間實踐理論的核心主題。在第五章《走進城市》(GehenindieStadt)里,德·塞爾托將步行作為人類最為基本和具體的實踐行為納入人與現代城市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空間交往的討論范疇。他認為,作為身體最自然、最直接的空間位移方式,步行是主體游離于現代城市最基本的形式,而步行者以步行為主的運動機能則占據城市系統的核心。在城市中的行走者以實踐性的活動將身體寫入空間。他們無須理會那些充斥著抽象線條和標示符號的城市地圖,而是通過自己在城市道路中的駐足、穿梭、流動等實踐行為從缺乏實際動作和在場性的模糊線條中解放出來,以沒有終結、漫無目的行動創造屬于自己的城市文本,獲取由各種建筑、街道、場景、氣息交織在一起的空間意象和感受(Certeau, 1988: 188-197)。在德·塞爾托看來,“場所”(Ort)和“空間”(Raum)是兩個彼此聯系又相對的概念,“場所”是一種由各種元素按照一定關系比例劃分的秩序,代表著不具生命現象的客觀物質性存在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而“空間”不是一個客觀物質性的存在,它是由方向、速度、時間等流動因素組成的交織,是一種運動的結果,取決于人類實際的行動與作為,所以,它總是與人類的行動和歷史有關。人類在一個“場所”內涉入了主觀性的行動時,才驅動了“空間”的產生。用他的話來說,“空間是被實踐了的場所,由都市規劃所定義的幾何性街道在行走者(的腳步下)轉化為空間”(Certeau, 1988: 217)。
小說《短信長別》分為“短信”和“長別”兩個部分,每個部分的引言分別為德國作家莫里茨的自傳體小說《安東·萊瑟》中一段與旅行活動相關的話。第一部分引言如下:“……這天氣看起來確實適合旅行。天空貼著地面,周圍的景物黑蒙蒙,這樣一來,人們的視線似乎只有盯在腳下行走的路上。”(2)這段引文中,四周暗黑的環境與焦點所在的道路形成對比,“行走”一詞更是預示著主人公在美國停留的主要方式。而引文中提及的“腳下行走的路”與隨后《短信》開篇的出場地點杰斐遜街道相呼應:“杰弗遜街在普羅維登斯是條寧靜的街道。它繞著商業區通向城南,在這兒它叫挪威街,可以駛上通往紐約的輔路。杰弗遜街錯落變寬的地方,形成了圍著山毛櫸和槭樹的小廣場,其中韋蘭廣場旁有座英式樓房,這便是韋蘭酒店。”(3)此處雖為故事展開的環境交代,但敘述視角猶如一臺帶有長焦鏡頭的攝影機,由北向南、由遠及近,將視線先后定格于“街道”“廣場”“酒店”這些隨處可見的日常空間元素。“我”的美國之行開啟于杰斐遜街道,為后文不斷延伸的行進做了鋪墊,也暗示了主人公“我”的新大陸之旅首先是在一種與“街道”有關的“敘事性活動”(Brueggemann,1996:138)中展開,行走構成其最主要的空間實踐方式。通過行走,其身體和各種感官介入城市這一集“人的生存、文明與建筑的復雜載體” (張榮,2011:83),審視、感知和體驗美國現代城市圖景,也為其一步步地投射出過往經歷的回憶,賦予其更為開放的審美體驗與生存空間。
2 城市行走者與觀看者
縱觀《短信長別》全文,行走、閑蕩、觀看、尋找是主人公“我”在美國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行為特征和活動狀態,援引克里斯托夫·巴特曼(Christoph Bartmann)的話,這是一種在文本內“被講述的運動”(erz?hlte Bewegung)(Bartmann,1985:115)。當“我”抵達首站普羅維登斯安頓好后,便開始了自己的城市漫步。此時的主人公似乎被妻子突如其來的威脅信所困擾,他不斷的“從人行道走到馬路上,又從馬路走回人行道” (10),周圍的事物匆匆閃過,使“我”向自己發問:“我能夠改變的環境又在哪兒呢?我暫時把固有的環境拋到了身后,在眼下這個陌生的環境里,我不過是一個使用公共設施的人,一個在馬路上行走的人,一個乘坐汽車的人,一個住酒店和光顧酒吧的人。”(11)伴隨這一拷問,主人公啟動了對自己現有生存狀態的剖析,也揭示了其美國之旅的動機,即試圖通過遠離家鄉、踏入陌生環境的旅行來擺脫現實生存的困境,換而言之,其根本動機為:認識自我、找尋自我并改變自我。
可以看到,啟程伊始,“我”的行走并非愜意自如,而是充滿危機與不安,因為“我”一次次地“穿過幾條橫街”后,又“折回杰斐遜街” (11),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妻子尤迪特的形象和與她相處的種種矛盾,使得“我急切地避開人行道上每個向我迎面走來的人” (11),而“這種恐懼和這種盡快改變自己、最終擺脫恐懼的欲望使我厭煩透頂” (12)。某種意義上來看,主人公此時在街道中的行走趨于被動,他意欲躲避人際間的直面交往,來不及也不愿細細體察腳下和眼中的城市,而是被動地行走在街道上。
前文提到的博爾諾夫曾對街道這一日常空間的基本結構形式進行過闡釋,在他看來,世界是由交通關系、道路和街道網絡構成的,而人的日常生活、日常行動均在這一基本空間結構上得以展開和顯現。主體一旦離開家匯入街道這個均質、中立的空間,便被納入其與社會交流的基本關系體系:“我在家是個人的,在街上卻是匿名的。”(Bollnow,1963:101) 現代城市中的街道往往具備一種無限延伸、沒有中心的空間特征,人在街上的行為被規定以速度與目標,即不停向前以抵達目的地。個體在匆匆向前的人流中必須為保持自己的節奏與步伐而勞心,這也是人在街道中感到茫然無從的原因,其最終結果就是導致主體的自我異化和屈服于大眾。文本里的主人公就是這樣被動前行,他越是急切地想要改變自己,越是步伐匆匆,毫無目的地“四處張望,然后急不可耐地看看手表”(10)。可以說,主人公此時與城市尚是疏離的關系,行走的城市于主人公而言,潛伏著倉促與惶恐,時時將其拉入婚姻危機的噩夢中,步履匆匆的他難以獲得喘息之機,取而代之的是生存的壓迫感、無歸屬感。
依照妻子留下的蹤跡,旅途繼續延伸,紐約、費城、圣路易斯等美國大都市構成人物旅行的重要站點,也是其逗留行走的主要場所。與第一站普羅維登斯相比,紐約作為西方現代社會特別是都市空間典型代表之一,在主人公進入之初就以各種各樣的符號表征刺激和影響著他的視覺和心理感知,成為一個特有的感官之城和能指世界,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建構主體的生存機制和感知體系。當主人公乘坐美國最具代表性的“灰狗大巴”初入紐約時,“我”首先通過視覺印象感受到美國現代社會所富含的符號體系和消費氣息:“離紐約越近,廣告上的文字越來越多地被畫面取代了:冒著泡沫的巨大的啤酒杯、燈塔般大的番茄醬瓶子和原型一般大的噴氣飛機在云端。”(19)在紐約,由酒吧、商場、飯店、報亭、旅館、電影院、公園等各類空間形式所構筑的都市結構呈現為一種流動的、多變的、充滿異質性的空間圖像,嵌入人物的視覺感官:“現代大都市完全可能變成一個物的差異性的海洋,沒有任何重要的物品遺漏在人們的審美沖動之外。”(汪民安,2006:115)正如主人公事后與朋友克萊爾憶及初到美國的印象時,首先提及的便是映入眼簾的“加油站、黃色出租車、汽車影院、廣告牌、高速公路、灰狗大巴、鄉村公路上的汽車站牌、圣塔菲鐵路、沙漠等”(62)。現代社會使都市變成了一系列圖畫似的象征符號,帶來一場視覺革命,強烈地刺激著“我”的視覺神經。主人公在日常行走中不斷抓捕的細節,美國社會的物質性、符號性與自然性共存,甚至成為規范的、有秩序的“第二自然” (Brueggemann,1996:134),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常規之物存在于現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也嵌入到主人公的意識中。與旅行伊始的被動行走相比,主人公在紐約不由得“放慢了腳步” (27),“漫無目的卻充滿好奇地蕩來蕩去” (30),迎來了一番新的行走體驗。
“時代廣場”“百老匯大道”“第五大道”“中央公園”等紐約別具代表性的地標或建筑通過主人公漫不經心的游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前往時代廣場的路上,眩暈的方向感一度讓“我”窒息:“我沿44街向東走去,‘向西!’我轉身朝相反方向而去。我要去百老匯,可直到越過了美洲大道和50街我才發現,其實我并沒有轉身往回走了,所以我停下來,想來想去,開始有點暈。接著,我沿著麥迪遜大道走到了42街,在這兒我又拐了個彎慢慢走下去,的確走到了時代廣場旁的百老匯大道。”(23)這里,街道這一最廣泛的城市空間材料在主人公的步行活動下再次展示了其迷宮般的空間秩序。作為城市血管的街道,它的意義不可小覷。一方面,作為一種基本建筑模式,街道經由網絡化的縱橫匯聚、切割,連接了整個城市和城市人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它作為現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場所,集結和匯聚了各種現代社會的氣息乃至姿態,“承受了城市的噪音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消費,承受了歷史和未來,承受了匆忙的商人、漫步的詩人、無聊的閑逛者以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最后,它承受的是時代的氣質和生活的風格”(汪民安,2006:137)。在米夏爾·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看來,“街道是不同類別的人、那些來自不同階層、信仰、種族和年齡階段的人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交匯點”(Bachtin,1989:192)。對于主人公“我”來說,從旅途啟程的“杰斐遜”街開始,各類物質和人群積聚的街道成為“我”觀看和行走的主要地點。“我”置身其中,用腳步丈量街道,捕捉城市意象的含混與復雜,體驗它們的細微之處。隨著“我”在紐約街頭的漫步,啟程伊始的緊張和不安被逐步消解,“我”獲得了暫時的解放與愉悅,甚至好奇:“在時代廣場上,我看著裸體照;我從百老匯上空的霓虹燈字幕上讀著當天的新聞;對著報社大樓的鐘我對了對自己的手表。”(漢德克,2013:30)對他來說,漫步紐約的最大感受“不是一種想象,也不是一種聲音,而是一種時不時造成這兩種錯覺的節奏”(33)。主人公借“節奏”一詞道出了現代主體為己所困的精神牢籠。在講求節奏與效率、時間被精確計算和無限擠壓的現代都市里,常人很難按下生活的暫停鍵,放緩腳步,在細細體量世界中獲取最真切的內心體驗及探尋自我存在的意義。而此刻,身為旅行者的“我”,以沒有終結、漫無目的都市漫步創造了德·塞爾托所說的個體審美體驗和“城市文本”,因為“紐約面目祥和地在我內心展開,并沒有對我施加什么壓力”(34);“我”甚至把這個“擁擠不堪、隆隆聲不絕于耳的城市當成一個溫情的自然劇來感受。我剛才就近可以看到的一切,玻璃窗、停車牌、旗桿、霓虹燈字幕……此刻分散成了一種你可以在其中極目遠眺的景象,讓我有了融于其中和讀書的興致”(34)。
3 在行走中建立關聯
在紐約街頭,“我”偶有迷失方向,但仍有意識地緩慢前行,地鐵入口旁的電話亭、嬉笑談話的姑娘、井蓋里散出的地鐵熱氣、一旁的柏油馬路、嘶鳴的警笛……這些當下最為真實和日常的人群、聲音、圖像等不再一閃而過,而是被主人公主動捕捉,仔細體察,正如主人公所說,“現在我才開始在內心感受著這座我先前幾乎忽略了的城市”(33)。這種看似閑散的行為將主人公的感官調動起來,為其提供了無限的感知可能性,因為“一排排大樓和街道事后由留在我大腦里的顫動、停息、糾結和沖擊組合而成” (34)。主人公在紐約街頭的行走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愜意感,他“輕松地觀看著,處于一種天堂般的狀態,一種只是想觀看,觀看就意味著認知的狀態” (25)。
在“觀看”欲望的驅動下,“我”停停走走,卻不忘打量街上的人群和面孔。比如“兩個姑娘,一個對著話筒說話,另一個偶爾將身子彎過去,一邊用手把頭發別到耳后”(24);電影院外,“我前面走著一位高大的姑娘,似乎被她那擺來擺去的書包牽引著,也在人行道上不緊不慢地走來走去” (27);就連在咖啡店里停留片刻,“我”的目光也不忘四處周旋:“從掛著簾子的窄門向路上望去,能看見的空間很小,以至于其間的景象越發清晰。里面的人行動似乎很緩慢,像在演戲。他們好像不是從門前走過,而是在門前信步。女人們的胸部從來都沒有現在這般好看和充滿魅力……”(28)這里,主人公漫步街頭頗顯無羈的形象類似波德萊爾筆下的“浪蕩子”,而對本雅明來說,在一個城市里的溜達閑逛就是發現其空間位置的意義,并無可避免地與街道上過往的人群接觸碰撞,大都市的人際關系則首先鮮明地表現在“眼看的活動絕對明顯地超過耳聽”(本雅明,2005:34)。《短信長別》的主人公就是這么一位在閑逛中用“眼看的活動”來體驗現代都市的人物形象。與19世紀大城市興起初期的閑蕩者有所區別,主人公“我”的游蕩行為不以發掘大眾背后遺漏的細節和事物(文人、詩人、拾荒者)或鬼祟地從事隱秘勾當(小偷、妓女)為目的,他看似無所事事的游蕩,實則身后充斥著強烈的精神需要和渴望:釋放自己、建立關聯。這種需求通過他對人群有意識地主動打探——“觀看就意味著認知的狀態” (25)和從他所打探的主要對象——女性體現出來,換而言之,主人公當下的行走空間和觀看行為成為投射他失敗的兩性關系和生存困境的鏡像。
在隨后抵達的費城,“我”對于擺脫危機、建立關聯的愿望更加強烈,因為我甚至和一個“大兵一同走過廣場,兩人都不知去哪兒,互相陪伴著” (40),在與大兵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好久以來,我第一次又能夠近距離而且不緊張地打量別人”(41)。回到酒店后,“我”平靜地對自己說道:“我再也不愿孤單一人” (43)。這些行為無不表現出主人公在行進的過程中,由城市的行走者、觀看者逐步演變為渴求建立與他者和世界的關聯的追尋者。他意識到,唯有走向人群、靠攏人群才能從根本上擺脫危機,彌補和修復與外部世界失去的關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主人公在美國都市是一位“幸運”的游蕩者形象。無論行走的心境如何,他在每個站點都努力走向大街,與形形色色的各類人群相遇碰撞:黑人電梯員、酒吧女郎、退伍士兵、街頭樂隊、妓女、游行隊伍、印第安人乞丐、醉漢、吸毒者、失業人員,等等。透過主人公的步伐和視角,一個立體的、蘊含歷史與文化語境的美國都市空間躍然紙上。貧富差距、越戰影響、種族階級等問題(Batt,1975:222;Mixner,1977:145)雖然不是漢德克所要表現的根本要素,但無可否認,通過主人公的游走行為,都市街道中每一個個體都伸展出異質性面孔,把他們原本“匿名、既沒有背景,也沒有歷史” (汪民安,2006:146)的身份在都市空間的大環境下透露并勾連起來。雖然這種僅限于眼觀的短暫接觸仍然滲透著現代性轉瞬即逝的特質,但主人公逐漸主動的游蕩行為正慢慢引發催化反應。
他主動寫信聯系三年前有過一夜之情的美國女朋友克萊爾,與克萊爾及其女兒匯合并一同到達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的大城市圣路易斯。美國歷史上,這座城市是“進入西部的大門,是先鋒精神的象征” (Brueggemann,1996:127)。于主人公而言,該城則是其關聯他人(克萊爾母女及其畫家朋友)、向他人披露自身經歷和回憶的“傾訴地”以及反客為主、向妻子尤迪特主動“出擊”的戰場。主人公游走于圣路易斯,“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向我敞開胸襟,無論我看什么,都會有一種新的感受”(112)。而隨后在圖森這一站,當“我”閑逛至一家教堂,“懷著一片虔誠觀察著這一切”時(130),再次肯定了自己的內心渴望:“我突然有能夠與什么產生關聯的愿望。真讓人受不了,總是獨來獨往,形影相伴。想必存在著一種與他人的關系,它不只是個人的,偶然的或者一次性的,在這種關系中,你不用依靠不斷要挾或者欺騙來的愛情來相互維系,而是通過一種必然的、非個人的關聯。” (131)這段感悟源于行走,卻超越行走本身,道出了主人公美國之行的全部意義:行走于不斷延伸的旅行空間,以“在路上”的發現者姿態摒棄大眾意義上的“孤獨的行者”,用緩慢沉靜的節奏去發現和感受世界的每個細微之處,吸取最本真的感受,建構新的生存空間,獲得自我與他人、與世界的聯系。最終,主人公與妻子抵達大導演約翰·福特位于洛杉磯的私人花園,在這個“從露臺向山谷望去,是一片片橙子樹和柏樹” (149)的伊甸園內,他平靜地傾聽福特“教育式的講話” (Bartmann,1985:120),與妻子達成和解,最終從被困擾和壓抑的意識中脫離出來,獲得“童話般”(Karasek, 1973:87)的結局,完成了自己在美國境內的變形之旅。
4 結語
不可否認,從創作風格上來看,《短信長別》受20世紀70年代德語文學“新主體性”趨勢的影響,具有發現自我、尋找自我的寫作主旨。而自《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DieAngstdesTormannsbeimElfmeter)起,漢德克中期創作生涯中的文學人物大都以迷茫、搖擺、不定的狀態游刃于外部世界,漫游和感受構成最為鮮明的行為特征,伴隨人物的生存活動始終。《短信長別》一文中,主人公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城市游走者形象,通過“行走”這一具體的空間實踐,主人公捕捉當下世界的真實感受,并在觀察、回憶、反思中重構新的自我生存空間,演繹了一場現代主體透過腳步的丈量和經驗的表達走出困境的生存之旅。不難發現,無論是博爾諾夫強調的人與空間的互動,還是德·賽爾托的日常空間實踐理論,都業已在《短信長別》中有所體現。同時,小說也向我們指明,漫步與行走作為現代人最普遍的空間實踐,代表了主體與世界最直接的交互關系,也提供了一種現代生存的美學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