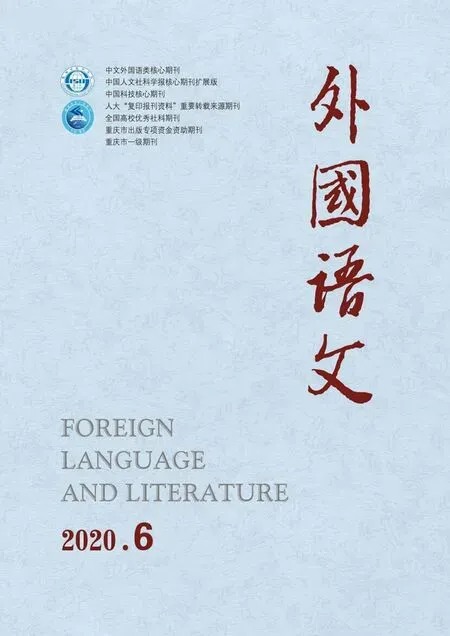《哈利·波特》系列的雙重敘事運動
姜淑芹
(四川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重慶 400031)
0 引言
自1997年以來,《哈利·波特》系列已風靡全球20多年。《哈利·波特》系列始終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但到2000年第四部出版時,因其空前暢銷,開始遭到主流批評界的強烈抵制。學者們冷靜下來認真閱讀作品后,才發現這是一部內涵極其豐富的作品,很快便形成了兩種研究走向,“一是以神話原型批評為導向的主題學研究,致力于挖掘作品中豐富的文學原型;二是以社會文化批評為導向,評析作品中涉及的性別、種族、權力、多元文化等主題” (姜淑芹,2008b:86)。早期研究偏向于傳統性,近年來的研究話題越來越多元化,與消費主義、權利話語機制、酷兒理論、認知批評等理論相結合(Panoussi,2019:42),稱其為“極具史詩意味的后現代主義作品”(崔筱,2015:97)。但是,這些關于后現代主義特點的話題研究往往只是關注作品的某側面,忽視了《哈利·波特》系列在整體敘事方式上的自我解構性。在善惡爭斗的宏大英雄敘事背后,還有一股貫穿整個系列的微小個人敘事暗流,形成一邊建構一邊解構的雙重敘事運動。本文挖掘作品中隱性的敘事暗流,解析其與故事的顯性敘事互為補充、相互顛覆的審美張力。
1 雙重聚焦主體與感知者
聚焦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敘事學概念,它“以感知行為為標志,并以不同的行為主體作為識別特征”(陳芳,2017:4)。聚焦概念的出現強調獨立于敘述之外的感知行為,即在對敘事文本的情境、事件、人物等進行描述時,總有一個看待所有這一切的視角,或觀察點,通過這一觀察點將所看到的一切呈現出來,并借由同一個或不同的敘述者之口將它們“說”出來。在敘事文本中,聚焦所涉及的是誰在作為視覺、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譚君強,2008:82-83)。《哈利·波特》系列整體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但聚焦的主體和客體,即感知者和聚焦對象卻具有雙重性,既有從魔法世界的感知視角看待哈利·波特的敘述也有從哈利·波特的感知視角看待魔法世界和自己的敘述。這種雙重性使文本產生了多義現象,因為“感知往往能體現出特定的情感、立場和認知程度”(申丹,2018a: 85)。最突出的便是哈利·波特的人物形象問題。哈利·波特無疑是魔法世界的英雄,但同時他“身上又帶有現代反英雄的特性”(姜淑芹,2009:82)。這種矛盾的身份特征正是由于感知者認識的不同而產生。哈利·波特的英雄身份是被魔法世界的宏觀視角塑造出來的,即一種外聚焦的視角,代表了整個魔法世界群體對哈利·波特的肯定與期待。故事一開頭便通過魔法世界的兩大權威人物麥格教授和鄧布利多校長的視角為讀者營造了關于哈利身份的神秘氣息:“他會成名的——一個傳奇人物——如果將來有一天把今天定為哈利·波特日,我一點兒也不會覺得奇怪——會有許多寫哈利的書——我們世界里的每一個孩子都會知道他的名字!”(Rowling, 1997:13)隨后在哈利身上便發生了一系列神秘的事情,包括悄悄消失的玻璃,貓頭鷹傳書等事件,直到哈利·波特的神秘身世被揭開,哈利進了霍格沃茨魔法學校,故事情節按照傳統英雄歷險的模式展開。不管是對角巷的人,還是哈利·波特的老師和同學,這些從外部視角感知到的哈利·波特都在不斷地印證他的英雄身份。
如果我們把感知的視角切換到哈利個人的內聚焦,看到的便是他的弱小與普通。在麻瓜姨媽家里,哈利一直被欺凌。雖然對角巷的人見到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都畢恭畢敬,哈利自己卻一直處于懵懵懂懂的狀態,更多的是為自己對魔法世界的無知而感到羞愧膽怯。進入霍格沃茨魔法學校之后,雖然感到開心,但各種功課對他來說仍然壓力巨大。就連最能表現他英雄氣概的歷險部分,因為羅琳在情節上設置了敘事逆轉(1)在《哈利·波特》系列每一集作品的高潮部分,讀者都會發現不是助者變成了對手,就是對手變成了助者,營造出出其不意的敘事逆轉效果,詳見姜淑芹,《論〈哈利·波特〉的敘事結構》,《外國文學研究》第32卷第3期,2010年6月。,等到最后與伏地魔的化身面對面時,哈利感到的不是驕傲,而是驚愕與懊惱。例如在第一部中,當他看到面前的敵人不是他一直以為的斯內普教授,而是奇洛教授時,哈利驚愕得喘不過氣來,他“無法相信這一切,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288),隨后哈利便一直處于被動地位,最后暈了過去,醒來之后就已經糊里糊涂地取得了勝利,躺在病床上收獲了大量“朋友和崇拜者送給你[他]的禮物”(231)。《哈利·波特》的每一部都遵循這種模式,哈利和他的朋友們每次都因為不遵守規則而落入伏地魔的圈套,雖然在斗爭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勇氣與機智,但每次都是要靠師長的幫助脫險,直到最后一部哈利才真正成熟起來。整個系列描繪的是一名普通少年不斷犯錯逐漸成長的過程。但這種從哈利個人感知角度的描寫隱藏在魔法世界對哈利·波特偉大形象的宏觀聚焦框架之下,讀者很容易被魔法世界的新奇和故事的史詩性吸引,忽略了微小的個人視角。
隨著故事情節的復雜化,兩種感知視角都開始更多地聚焦于解構哈利·波特的英雄性。在第四部結尾,哈利親眼看到了伏地魔的歸來,因此在第五部的一開頭便表現得焦躁不安。他的教父小天狼星給他寫信要他“安分守己……不做任何魯莽的事情”(Rowling,2003:9),好朋友羅恩和赫敏也勸他不要著急,但他“內心的怨憤不斷地堆積,他真想大聲怒吼出來。如果不是他,甚至誰都不會知道伏地魔回來了!”(10)回到魔法世界后,哈利多次對兩個好友和教父發火,小天狼星提醒他要“保持禮貌”,不要“發脾氣”(123),但他甚至還多次感到想要攻擊鄧布利多校長,最后還因為沖動地闖進了魔法部而永遠失去了他的教父。從哈利的朋友、師長的感知視角對他的描述是煩躁魯莽,一個典型的叛逆期青少年形象。
代表魔法社會的魔法部對哈利的壓制更是將善惡爭斗的英雄歷險變成了個人反抗權威的無奈與失落。從哈利年齡不夠卻意外入選三強爭霸賽開始,他便被看成了一個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而不惜撒謊的人,連他最好的朋友羅恩都說:“你可以把實話告訴我的,如果你不愿意讓別人知道,很好,但是我不明白你為什么要撒謊呢?”(Rowling,2000:287)等到他迫不及待地想警示大家伏地魔已經歸來的時候,以魔法部為代表的官僚機構不愿意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選擇隱瞞真相,不惜一切力量把哈利·波特塑造為一個沽名釣譽的小人。魔法部長福吉利用手中的資源,在媒體上抹黑哈利的名聲,“使外面的巫師都認為他只是一個蠢笨的男孩,是個笑料,盡說一些荒唐的無稽之談,就為了使自己出人頭地”(Rowling, 2003:74)。高級調查官烏姆里奇教授更是因為哈利說了真話而罰他每天在自己手上刻“我不可以說謊”的字樣。哈利·波特無力改變現狀,他“迷失在謊言、半真半假的事實以及各種各樣謎一般的信息中,哈利·波特不知道該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該怎么讓自己被人相信”(Flaherty,2004:93)。此時的哈利·波特“身上的英雄光環完全褪去,呈現為一個典型的從虛幻中驚醒的反英雄形象”(姜淑芹,2008b:84)。
作為一部成長小說,故事的最終結局自然是正義得到了伸張,哈利·波特仍然是魔法世界的英雄。但整個系列結尾的英雄與開頭的英雄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善惡爭斗的傳統英雄敘事框架經過微小個人敘事的內部解構已經演變成了現代普通人的心路歷程。難怪哈迷讀者認為小時候看《哈利·波特》驚詫于其非凡的想象,夢想著自己也擁有強大的魔法斬妖魔除鬼怪,長大了才看到哈利·波特的辛酸與努力(Natov,2001:311)。雙重聚焦的敘事手法使哈利·波特的人物形象變得立體化,更加貼近現代人的生命體驗。每個現實生活中的人都曾經歷過壓抑、反抗與無奈,夢想著有一天成為無往不勝的英雄,又慢慢地認識到自己的平凡與奮斗的價值,可以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神性與人性交織的哈利·波特。
2 表層文本與潛藏文本
從敘事進程的角度來講,哈利人物形象的發展過程其實是表層文本與潛藏文本的互動過程。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塑造一個傳統英雄,潛藏的視角卻塑造了一個掙扎的現代普通人形象。 傳統的英雄敘事重在強調命定論,“哈利·波特系列的文本中充斥著與生俱來的英雄氣質、由內至外的領袖風采,確保一切回歸秩序的自我犧牲等結構符碼”(Mendelsohn,2002:160),但與這個顯性的表層文本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隱性的潛藏文本,它在不斷強調個人選擇的力量。“命運與自由選擇之間的沖突貫穿整個系列七部小說,但研究界卻始終沒有關注到這個雙重性”(Pond,2010:181),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關于自由選擇的敘述隱藏在宏大的英雄敘事框架之下,并且作者采用了碎片化的方式分散提供信息,只有反復細讀文本才能發現。其實,早在2004年和2007年就已有資深哈迷關注到了這個問題(2)詳見Dworsky, Lauren.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in Harry Potter.” Mugglenet. 20 Dec. 2004. 9 Oct 2007
有能力戰勝黑魔王的人走近了……生在曾三次抵抗過他的人家,生于七月結束的時候……黑魔王會把他標為自己的勁敵,但他將擁有黑魔王不知道的力量……他們中間必有一個死在另一個手上,因為兩個人不能都活著,只有一個生存下來……有能力戰勝黑魔王的那個人將在七月結束時誕生。(Rowling, 2003:841)
預言是英雄故事常用的元素。傳統的預言是神的旨意,沒有任何人力可以改變,所有的神話故事及民間傳說都是如此,例如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老國王選擇殺死自己的兒子也無法擺脫厄運。哈利的歷險都是因為伏地魔想要抵抗命運的安排,但他注定每次都失敗。在《哈利·波特》系列中,這個預言貫徹始終,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讀者哈利的神秘性,但圍繞預言的敘述卻隱藏著許多不確定性的因素。
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特別是糧食作物生產經營的“直接物化成本+地租+人工成本”三大投入要素價格,全部呈現陡峭的直線飆升狀態,農業生產經營全面走入高成本時代。這就要求發展具有更高賠償金額和賠付標準、更廣闊的農業生產成本覆蓋面的農業大災保險來為農業生產活動保駕護航。
這個預言的內容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選擇,因為這個預言適用于兩個男孩,一個是納威,一個是哈利,他們倆都生于七月底,父母都在鳳凰社,兩家的父母都曾經三次從伏地魔手里死里逃生,也就是說那個有能力戰勝黑魔王的人也有可能是納威。但“黑魔王會把他標為自己的勁敵”,也就是說哈利的命中注定實際上是伏地魔選擇的結果,他選擇了哈利作為自己的勁敵,由此便改變了哈利的一生。
被黑魔王選定后,哈利的人生似乎就被預言左右了,從小便頂著“救世主”的光環,承擔著拯救整個魔法世界的重任。實際上并非如此,哈利最終成為拯救魔法世界的英雄也是他自由選擇的結果。最初進入霍格沃茨魔法學校時,分院帽就很猶豫,并且認為哈利更適合去斯萊特林學院,因為它“會幫助你走向輝煌,這毫無疑問”(Rowling, 1997:121)。但哈利最終去了格蘭芬多。這個時候的哈利對斯特萊林并無多少了解,他的選擇只是基于對馬爾福的厭惡。在對角巷購物的時候,他表現出的傲慢以及對非古老巫師家庭出身孩子的輕蔑讓哈利感到不適。后來在火車上馬爾福對好友羅恩的嘲弄更加激起了哈利的憤恨之心,并且從羅恩那里了解到一點馬爾福一家與黑魔王的關系。面對分院帽的時候,哈利完全沒有考慮自己的未來是否輝煌,而是遵從了自己當下的內心。哈利選擇的是純潔正義的一方,正如鄧布利多指出的,哈利必須殺死伏地魔,但“不是因為預言!而是因為你自己,你不這樣做就不會安心!”(Rowling, 2005:511)伏地魔選定了哈利作為自己的敵人,所以他一定要追殺哈利。但預言中并沒有說哈利必須做什么,他也完全可以不理會那個預言,但出于正義的本性,即使伏地魔不來追殺他,他也一定會站在反抗伏地魔的一方。伏地魔與哈利的命運都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結果,而非命運的安排。
作出預言的特里勞妮教授在故事中被塑造成一個老騙子的形象,她那些所謂的預言都是無稽之談。鄧布利多校長認為她沒有絲毫天賦,并且認為占卜課也沒有必要開,“因為我們行為的因果關系總是如此復雜、如此多變,所以預測未來是非常困難的”(Rowling, 1999b:426)。神奇動物馬人費倫澤更是對特里勞妮教授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她的時間幾乎都浪費在自吹自擂的廢話上了,這種廢話被人類稱作算命”(Rowling, 2003:603)。費倫澤指出人類向來不怎么擅長預測未來,就連馬人也都是經過漫長的歲月才擁有了這種能力,但是“有時連馬人都會看走眼,所以過于相信這一類事物是很愚蠢的”(604)。在《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中,當哈利感到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對抗伏地魔時,鄧布利多向他強調,“永遠不要忘記,預言的意義只是伏地魔造成的……伏地魔把你當成對他最危險的敵人,而這樣一來,他就使你成了對他最危險的敵人”(Rowling, 2005:509)。這句話聽起來比較繞,鄧布利多進一步解釋道,特里勞妮教授的預言誤導了伏地魔,并且他只聽了一半就采取了行動,而如果伏地魔沒有聽說過那個預言,就不會去殺哈利,哈利的母親也不會犧牲自己保護兒子,伏地魔也就不會因為犧牲魔咒的力量而制造出自己最可怕的對手。也就是說,預言本身并沒有意義,這一切都是伏地魔選擇的結果。如此一來,預言的權威性就完全被顛覆了。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正是后現代社會的真實寫照。
申丹教授稱這種與情節發展齊頭并進、貫穿文本始終的敘事暗流為隱性進程(3)申丹教授早期對隱性進程的研究限定的范圍比較狹窄,基本都局限于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篇幅短小,語言精練,申丹教授舉例的隱性進程很不容易為人所察覺,都是通過細致的文體學與敘事分析才發掘出作品的隱含進程。申丹教授2019年與2020年新發表的論文中探索的范圍有所擴大。《哈利·波特》系列的這些敘事進程雖然在文本層面有明確的表述,但也不同于傳統的隱匿情節、第二故事等,而是更接近于申丹教授提出的隱性進程概念。,并認為這種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兩種敘事運動交互作用、互為補充,聯手表達出經典作品豐富復雜的主題意義和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申丹,2018b:84)。哈利·波特被塑造成英雄,而實際上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男孩,選擇對抗邪惡。他的對手伏地魔也曾經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男孩,而他選擇把自己塑造成偉大的黑魔王。他們之間的爭斗從表層敘事來看“用各種象征符號勾畫出一幅社會意識形態畫面……反映出各種各樣的社會不平等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傳統、儀式、規則等”(Heilman et al.,2003:242)。簡而言之,哈利·波特與伏地魔的斗爭代表著傳統的善惡之爭,象征著顛覆偏見、追求多元平等世界的努力,是宏大敘事,那么是什么使兩個男孩做出了如此影響深遠的選擇呢?這些宏大的善與惡的根源是什么呢?《哈利·波特》系列通過微觀敘事的潛藏文本回答了這一問題。
3 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
正邪沖突是托爾金以來的高奇幻小說的基本主題,但90年代之前的奇幻小說對于兩派之間爭斗的原因通常模糊處理,往往是黑暗勢力無端地就崛起。這種模糊性是奇幻小說被指虛空逃避的重要原因,因為抽象的正邪對立十分空洞,主人公的所有冒險活動就淪為模式化的行為,即評論界所詬病的類型文學的套路,缺少具體的深刻的現實關懷。《哈利·波特》系列在傳統奇幻小說的大模式之下,不僅融入具體的社會問題,并且使黑暗勢力與正義勢力爭斗的基本點也具體化,一個追求單一專制的極權統治,一個追求多元和諧的平等生存。不僅如此,這種對立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不僅哈利·波特的命運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黑魔王的命運也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更進一步的是,作者還挖掘了造成這些選擇的原因——是否擁有父母的愛。關于哈利的力量來自母親的犧牲的敘述貫徹整個系列,同時也潛藏著關于伏地魔缺少母愛的敘述。關于原生家庭是否給予了孩子愛的力量這樣的微觀敘事與宏大敘事形成了映照。
作為成長故事系列,它也是哈利逐漸體會父母的愛的力量的過程。哈利能夠成為大難不死的男孩是因為母親施了一個古老的魔咒,犧牲自己保全孩子,這個魔咒保證了哈利在成年之前不會受伏地魔的傷害。哈利最初并沒有完全明白母親為他做的犧牲的力量有多么大,甚至會有些厭煩鄧布利多總是強調他的力量源于他有愛。等到最終了解了伏地魔的身世后,他才體會到母親的犧牲護符力量有多么強大。
伏地魔的恐怖則源于母愛的缺失,他本名湯姆·馬沃羅·里德爾,他的母親梅洛普·岡特是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四大創始人之一斯萊特林家族的后人。她的父親和弟弟因為她出身巫師家庭卻沒有魔法技能(啞炮)而殘酷地虐待她,可是實際上她的魔力只是因為父親的高壓和恐怖行為而無法正常發揮。她癡癡地暗戀著村里的一個麻瓜湯姆·里德爾。在父親被抓去阿茲卡班服刑后,梅洛普使用魔法讓湯姆·里德爾與她一起私奔了。但真相敗露后,湯姆無情地拋棄了已經懷有身孕的她。梅洛普深受情傷,完全沒有活下去的意志,生下兒子后一個小時便死去了,臨死時只希望孩子長得像爸爸,并給孩子取了父親的名字。梅洛普沒有給予小湯姆一點點母愛的力量,她陷在自己的悲劇里不能自拔,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那個不愛她的男人身上,但如孤兒院院長所說:“從來沒有什么湯姆、馬沃羅或者里德爾家的人來找他,也不見他有任何親戚,所以他就留在了孤兒院里。” (Rowling, 2005:266)作為一個生活在麻瓜孤兒院的小巫師,童年伏地魔的一些奇異力量讓其他的孩子感到害怕。可湯姆的成長歷程中沒有一點愛的力量,他意識到自己的某些特異功能后,選擇了利用它們恐嚇、懲罰、控制別人,從中獲得滿足與存在感。
愛的缺失使湯姆成長為一個冷漠、自私、孤傲的孩子。長大后經過多方查訪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他的心中充滿了仇恨,冷酷地殺死了自己的父親、祖父母與舅舅。湯姆切斷了一切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將自己的名字重組為伏地魔,開始了孤家寡人獨霸天下的征程。因為憎恨麻瓜父親,他也憎恨自己身上的麻瓜血液,所以堅決不會再采用父親的姓氏,這也是為什么他要帶領食死徒們維護魔法世界的純正血統。在第二部中,他親口向哈利解釋了自己是如何將自己原來的名字“湯姆·馬沃羅·里德爾”(Tom Marvolo Riddle)重組為“我是伏地魔”(I am Lord Voldemort)的。二者字母完全一樣,只是排列不同。
難道你認為,我要一輩子使用我那個骯臟的麻瓜父親的名字?要知道,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著薩拉查·斯萊特林本人的血,是通過他后代的女兒傳給我的!難道我還會保留那個令人惡心的普通麻瓜的名字?他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就拋棄了我,就因為他發現自己的妻子是個女巫!不,哈利。我給我自己想出了一個新的名字,我知道有朝一日,當我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魔法師時,各地的巫師都不敢輕易說出這個名字!(Rowling, 1999a: 314)
伏地魔的選擇本質上是一種畸形的報復。他的悲劇根源于那可怕的無處不在的偏見,麻瓜對巫師的偏見。因為父親的偏見與拋棄行為,使他心中充滿了恨,而母親也由于這種偏見的影響而沒有能力給予他愛的力量,使他的人格產生了變異,選擇了一個人與全世界對抗。社會偏見造成了伏地魔父母的家庭悲劇,這個家庭悲劇在伏地魔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從而進一步惡化了社會偏見問題。
哈利選擇感恩母親的犧牲,選擇理解接受父親的不完美,因而在關鍵時刻總能獲得他們的保護。在第三部中,遭遇攝魂怪圍攻時,“呼神護衛”咒語并不熟練的哈利召喚出了一頭牡鹿守護神,成功擊退了攝魂怪。哈利以為那是爸爸為他召喚出的,因為爸爸的守護神是牡鹿,但實際上他的守護神也是牡鹿,是哈利自己憑借心中對父親的崇敬之心成功召喚出了自己的守護神,鄧布利多又一次指點他道:
你認為我們愛過的人會真正離開我們嗎?你不認為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會更清晰地想起他們嗎?你父親活在你的心里,哈利,在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就會格外清晰地顯現出來。否則你怎么會召來那樣一個特別的守護神呢?(Rowling, 1999b:427)
父母的愛長久地保護哈利,哈利對他們的愛則使那份愛的力量在需要的時候迸發。到了第四部伏地魔恢復肉身,哈利面臨生死大劫的時候,哈利的父母的靈魂又一次通過閃回咒出來保護他不受伏地魔傷害。從來沒有感受過愛的伏地魔輕視這種愛的力量,他的選擇是殺害自己的父親和舅舅,反而去采用仇敵的血來使自己復活。而鄧布利多卻選擇了延續哈利母親付出的血的犧牲,把哈利送給了她僅存的姐姐,使血緣的紐帶成為持續保護哈利的力量。哈利在成長的過程中,把這些給予的愛轉化成了自己的愛,因而當他成年后,父母的力量再也無法保護他的時候,他仍然能夠依靠自身愛的力量擊退伏地魔。
在第四部結尾的時候,伏地魔取了哈利的血得以復活,因此不僅打破了不能碰他的魔咒,并且把哈利的一部分也放進了自己體內,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哈利,這也是為什么鄧布利多教授讓哈利學習大腦封閉術來阻止伏地魔的這種控制。哈利沒有學會封閉大腦,但最終還是贏得了戰斗,鄧布利多又一次強調愛的重要性,但這一次已經不是父母給他的愛,而是哈利對教父小天狼星的愛。
關在那個房間里的那種力量,你大量擁有,而伏地魔根本沒有。那種力量促使你昨晚去救小天狼星。那種力量也使你不受伏地魔的控制,因為在一個充滿了他所憎惡的力量的身體里,他是無法近身的。到了最后,你能不能封閉大腦已并不重要。是你的心救了你。(Rowling,2003: 844)
哈利從父母那里接過了愛的旗幟,學會了愛父母、愛親人、愛朋友、愛正義、愛所有人。所以到了第六部的時候鄧布利多又指出了哈利與伏地魔本質的區別。因為他們二人之間的聯系,哈利能夠看到伏地魔的思想、野心和他的蛇語,也能看到伏地魔的威力,但哈利從來沒有接受黑魔法的誘惑,從來沒有顯露過追隨伏地魔的欲望。“簡而言之,是你的愛保護了你!唯有這一種保護才有可能抵御伏地魔那樣的權力的誘惑!雖然經歷了那么多誘惑,那么多痛苦,你依然心地純潔,還像你十一歲時那樣”(511)。
在系列的后幾部中,《哈利·波特》已經超越了兒童個體成長,開始探討社會生活中人的欲望追求與各種力量的博弈。哈利經歷了來自魔法社會的誤解、打擊和誘惑,仍然能夠保持初心,靠的就是以愛的力量凝聚而成的“精神共同體”的力量。視角從社會轉到家庭后,羅琳又一步步將哈利和伏地魔的個人故事重新推進到社會層面,哈利的愛從最平凡的親情開始,包含了友情、愛情與同情,到最后一部時發展到甘愿為整個魔法世界受死的耶穌式大愛。伏地魔則始終孤獨前行,靠恐嚇聚集烏合之眾,最終敗給了靠真心與博愛贏得了小精靈、馬人、巨人、甚至幽靈等所有生靈幫助的哈利。
從社會到家庭再到社會,羅琳始終在關注宏大的社會問題,這也是英雄敘事的本質特點,“神話里的事件不僅僅只影響某個領域的規則,而是要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Dickerson,2006:28),但她同時巧妙地在二者之間插入了一個家庭作為支撐點,使空洞的社會問題有了具體的內容。從這個角度看,《哈利·波特》不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而是一個很具體的家庭教育案例。原生家庭的愛能夠給予一個人力量,缺失這種愛則會毀滅一個人。改變社會問題的希望也在于最小的社會單位,即家庭的力量。奇幻小說的英雄敘事模式主要由20世紀50年代的托爾金發揚光大,而在這之前還有20世紀初期內斯比特開創的家庭魔法,強調家庭的力量,一直是英國兒童文學的傳統。羅琳巧妙地將兩種傳統融合,既關注宏大的社會問題,又通過微觀敘事拉近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探索解決社會偏見問題的出路。普通人往往會認為那些嚴重的社會問題與自己無關,從微觀的家庭視角可以看到,其實它與每個具體的個體息息相關。崔筱認為羅琳創造出偏執的伏地魔這一形象,是為了突出當代社會信仰危機的巨大破壞力,他從不相信救贖,只是一味地追求永世的生命和無盡的權力,為達目的不惜濫殺無辜、靈魂分裂。作者用伏地魔制造魂器的行徑暗喻由于信仰缺失所導致的無知與殘暴,試圖喚醒更多的人重視信仰,讓每個人都認識到:就像能夠驅散攝魂怪的守護神咒語那樣,只有努力相信美好的事情才能幫助自己戰勝恐懼和黑暗(崔筱,2015:96)。這一觀點準確地總結了作品的后現代主義內涵,但關注到作品的微觀敘事后,我們才能找到信仰缺失的原因所在,保持初心的力量源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以愛的力量克服偏見、顛覆獨裁,努力建立和諧共存的美好家園。兩個敘事進程相互補充,既關注到外部世界的矛盾斗爭,又可以反思個體的生存方式,使我們不僅聚焦于問題,更要思考問題的根源與解決辦法。
4 結語
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趨同,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但文化上多元性的訴求也越來越強,“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消解了認同的‘單一性’和‘本真性’”(王寧,2010:98),每一個個體、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期待彰顯自己的獨特性,二者之間形成了強大的張力。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人們渴望新秩序,但是每一個人都要積極參與,都要體現自我價值的新秩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是偉大的英雄,每一個普通的個體都要做出自己的選擇,以博愛的胸懷共建一個承認他者、容忍差異的和諧生態社會,這正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現實意義。申丹教授總結了九種情節發展與隱性進程相互補充的情況,其中一類是針對兒童的童話情節和針對成人的隱性進程,只有看到雙重敘事進程,才能對作品的主題意義、人物形象和創作技巧達到較為全面深入的理解(申丹,2019: 87)。這其實是優秀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好的兒童文學作品必須具備兒童看熱鬧,成人看門道的雙重性。《哈利·波特》系列就是一部“不僅適合少年兒童,更適合成年人”(劉緒源,2018:149)的優秀作品,它的表層敘事為兒童們講述了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英雄歷險故事,隱性進程讓成人們看到了后現代社會普通人的掙扎、努力與選擇。其實《哈利·波特》的讀者群不僅僅限于兒童/成人的簡單劃分,它在不同層面上能夠打動不同的讀者。羅琳的雙重敘事模式極大地豐富了故事的內涵,成功地“將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相融合,并與后現代讀者的閱讀審美需求相適應,從而產生了全球性的轟動效應” (姜淑芹,2008a: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