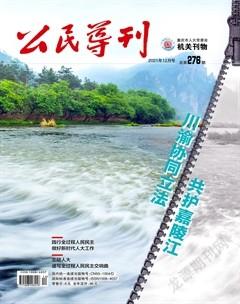嘉陵江保護立法“五部曲”
陳越
“獨泛扁舟映綠楊,嘉陵江水色蒼蒼。行看芳草故鄉遠,坐對落花春日長。”唐代詩人劉滄曾在巴蜀漫游時為嘉陵江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
嘉陵江發源于秦嶺北麓,流經陜西、甘肅、四川,最后在重慶匯入長江,是長江流域面積最大的支流,是川渝兩地共界河流,四川段干流長641公里、流域面積3.58萬平方公里,重慶段干流長152公里、流域面積0.96萬平方公里,是長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和水源涵養地,是沿岸群眾重要的飲用水水源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態環境服務功能。
緣起
協同共護勢在必行
雖然近年來川渝兩地共同開展了水污染聯防聯控,嘉陵江干流水質常年穩定達到Ⅱ類,但部分跨界支流水質達不到水域功能要求,少數支流斷面水質為Ⅳ類,甚至有個別支流斷面水質為Ⅴ類,小溪小溝生態基流斷流也時有發生。
2020年7月23日,川渝兩省市人大常委會簽署《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重慶市人大常委會關于協同助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合作協議》,其中就包括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立法合作事宜。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長江保護法,對協同推進長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作出了明確規定。而嘉陵江是長江上游最重要的支流,生態屏障戰略意義重大。
隨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出臺,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成為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重要內容。
“這些為川渝兩省市人大協同開展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立法提供了指導和遵循。”重慶市人大城環委主任委員屠銳說,開展嘉陵江流域協同立法,是長江保護法在嘉陵江流域的細化、補充和完善,也是兩省市人大常委會助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重要舉措。
破局
找準問題 “小切口”立法
立法工作此后啟動,川渝兩地流域資源稟賦、功能定位、產業布局、保護方法和執法標準等存在差異,統一流域管理標準難度較大,這讓立法者們有些“傷腦筋”。
2020年9月,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在開展立法調研時,市司法局、市生態環境局、市水利局等部門認為:我市已出臺《重慶市水污染防治條例》,對本市行政區域內的江河、湖泊、渠道、水庫等地表水體和地下水體的污染防治作出了規定,是否還需要專門為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立法,應慎重考慮。
隨后,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又向我市嘉陵江流域的11個區征求意見。各區強烈要求對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管理與保護進行立法,并提出了“建立嘉陵江流域聯合河湖長制,定期開展跨界河流聯合巡河工作”“川渝兩地政府建立嘉陵江流域水生態環境保護聯席會議協調機制”等建議。大家認為,開展嘉陵江流域水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是保護好嘉陵江一江碧水的現實需要。
經過前期調研,找準了問題難點,為市人大城環委確定協同立法形式、范圍、方法,提供了思路。
“我們逐條梳理各方的意見建議,發現反映最多的問題是‘聯防聯控’。”屠銳說,這恰是我市現行水生態環境保護立法的弱項。
“可否僅就‘聯防聯控’開展協同立法?”市人大城環委的這一提議,得到了市生態環境局等單位的積極響應。各方面一致贊同圍繞“聯防聯控”進行“小切口”立法。
這一“小切口”立法的想法,得到了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軒的贊同。
敲定
協同立法固化合作經驗
2020年9月中旬,川渝兩省市人大常委會調研組共赴四川省廣安段、南充段、閬中段,首次聯合開展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調研。
通過調研了解到,兩省市及所轄相關地市、區縣、鄉鎮等高度重視聯防聯控,據初步統計,截至目前兩省市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簽訂了60余項關于聯合執法、信息共享以及應對環境突發事件的合作協議,但執行效果參差不齊。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聯防聯控缺少制度保障。上下游各自為政,尤其是跨行政區的河流流域交叉斷面、混流區的流域治理和保護步調不一致。”重慶市人大城環委副主任委員代偉華說。
“要進一步深化流域污染防治聯席會議制度,健全信息共享機制,常態化開展生態環境聯合執法,完善突發事件聯合應對機制等。”四川省人大城環資委副主任委員馮軍回應道,“在相關標準制定中,我們將參考《重慶市水污染防治條例》相關要求,力求兩地達成統一。”
通過此次調研,川渝兩地對開展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的必要性達成共識,一致認為兩地各個層面已經在區域協同上進行了廣泛合作,積累了不少好的經驗做法,需要通過立法加以固化和推廣。
創新
按需制定“決定+條例”
2020年12月8日,川渝兩省市人大常委會調研組再次開展聯合調研,并舉行了座談會。聯合調研組從渝中區朝天門碼頭出發,乘船考察調研重慶市中心城區嘉陵江及長江干流部分區域水生態環境保護情況、廣陽島生態恢復保護情況。
“我市嘉陵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的主要制度是健全的,措施是符合實際的,總體上能夠滿足依法治水要求,不宜再單獨制定嘉陵江流域水生態環境保護條例。但是,嘉陵江流域在我市境內多為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和經濟發展高強度區,加之川渝兩地嘉陵江水系跨界河流多達38條,區域協作勢在必行。”座談會上,屠銳提出自己的觀點,“開展協同立法十分重要和緊迫,但協同形式和途徑應不拘一格。”
放眼全國,既有京津冀關于《機動車和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污染物防治條例》,三省市均以“條例”的形式進行協同立法;也有滬蘇浙三省市《關于促進和保障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以“決定”的形式打破區域壁壘進行協同立法。
屠銳認為,在與四川省協同開展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上,應結合實際,堅持問題導向,突出聯防聯控這一重點,立法體裁可以是決定或條例,需要幾條就定幾條。
對于突出聯防聯控這一重點,馮軍表示贊同。他還建議,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應建立完善區域協同機制,為流域綜合治理和跨區域環保協作提供法治保障。突出加強協作聯動,建立跨區域污染防治聯動協作機制,暢通流域上中下游各級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暢通聯合監測、聯合執法、應急聯動和信息共享通道。
最終,經過溝通協商,兩地人大達成共識:重慶市出臺法規性決定,四川省制定條例。
立法
通過和施行“齊步走”
達成共識后,川渝兩省市人大常委會分別著手起草條例和決定。
四川方面,將條例作為省人大常委會2021年立法計劃制定類項目加快推進。重慶市則將決定列為2021年立法計劃預備項目,由市人大城環委與市生態環境局共同負責起草。
“雖然是預備項目,但考慮到協同立法的特殊性,我們加快了工作節奏。”屠銳介紹,今年3月,重慶市人大城環委牽頭起草了決定初稿,與市生態環境局商議修改完善,并印送四川省人大城環資委征求意見。
今年5月底收到復函,重慶市人大城環委立即會同市人大法制委、市司法局、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市生態環境局等召開部門座談會,結合四川反饋的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草案文本。
今年6月初,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元春率隊前往四川省調研。陳元春表示,通過實地調研,收獲多、體會深。通過召開座談會坦誠交流,加強工作互動與溝通,兩省市人大齊頭并進推動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工作。
“川渝兩地人大協同立法,有利于統籌兩地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相關規劃,統一流域治理和資源保護標準,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共同筑牢長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保護川渝地區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提供堅強的法治保障。”今年7月9日,張軒在合川區調研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工作時指出,要按照環保法、長江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堅持問題導向,摸清具體情況,立足川渝協作和嘉陵江流域的實際,加強分析研究,做好基礎性工作,運用好大數據,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可操作性,真正做到針對問題立法、立法解決問題。
為了讓“決定”和“條例”高質量出臺,川渝兩省市人大常委會就協同立法的各項要點“精雕細琢”。
“鑒于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主要涉及水,且危險廢物轉移、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已有其他法律法規作出具體規定,為此,我市決定(草案)的調整內容以水生態環境為主,具體包括水污染治理、水生態修復、水資源保護等方面。”屠銳說。
四川省人大城環資委在調研論證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將法規的調整范圍進行了擴充,除“三水共治”外,還增加了大氣、固廢、危廢管理等內容。
2021年10月,重慶市人大城環委再赴四川省廣元市,就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立法相關工作進行探討交流,并進一步完善草案文本。
11月25日,《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嘉陵江流域水生態環境協同保護的決定》和《四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條例》同步通過,并將于2022年1月1日起同步開始施行。
接下來,川渝兩省市人大常委會還將協同開展執法檢查、視察、專題調研等活動,推動“條例”和“決定”的貫徹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