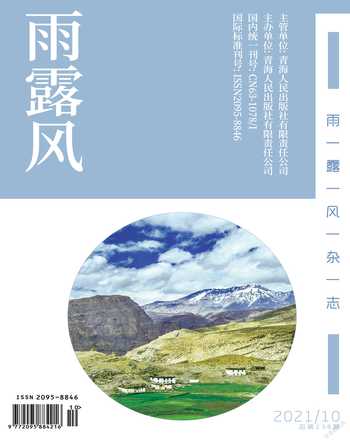黃信堯電影《同學麥娜絲》的空間探賾

摘要:《同學麥娜絲》是中國臺灣導演黃信堯繼《大佛普拉斯》之后的又一力作,改編自導演早期創作的紀錄片《唬爛三小》。影片在保有現實主義創作基調的同時,繼承了前作荒誕的敘事風格,將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并置敘述,對生活的諷刺意味更加濃烈。運用空間批評理論,分析黃信堯作品序列中所體現出的空間互文性,并從視覺和聽覺兩方面探討該影片的空間建構方式。
關鍵詞:空間批評;黃信堯;同學麥娜絲
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形勢影響,臺灣高房價問題日益凸顯。微薄的工資難以企及過高的房價,普通人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在這一背景下,《同學麥娜絲》(2020)講述了四個高中同學中年時期的故事,他們年近四十,安居樂業仍是難以完成的世俗愿望。添仔的導演夢戛然而止,罐頭自殺未遂后偶遇淪落的校花,電風背負巨額房貸艱難度日,閉結終于觸碰到愛情卻不料被當街錯殺。時間和欲望推著人向前,身份認同被擱置,人近中年卻對生活的制裁表現出束手就擒的姿態。
一、黃信堯作品序列的空間互文性
互文性指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系,而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絡[1]。現文本與前文本之間存在共生關系,現文本是對前文本的挪用、改寫、拼貼。《同學麥娜絲》改編自黃信堯早期紀錄片《唬爛三小》(2005),也是劇情片《大佛普拉斯》(2017)的姊妹篇,三部影片在相似和相同的空間構型手法上存在自涉互文性。
《唬爛三小》是黃信堯從1998—2005年拍攝的關于一群高中同學的紀錄片,拍攝該片時,黃信堯和同學們處在25歲到32歲的人生區間里,他們初嘗人生酸楚,開始面對諸如買房、工作、婚姻等現實問題。他們的活動空間涉及茶飲店、出租屋、新房等,包括同學們對話中經常提到的工作城市“臺北”。《同學麥娜絲》完全挪用了《唬爛三小》中人物的活動空間,但是拍攝本片時,導演已過不惑之年,對于這些空間的理解有了變化,因而空間在不同語境之下,形成了意義的再生產。就如“新房”這一空間形象,在《唬爛三小》中,家銘貸款買了新房后覺得人生充滿了希望。《同學麥娜絲》中的電風形象原型是家銘,但電風面對自己的“新房”感受到的只有無盡的壓力和一眼望不到頭的還款期限。新房作為一個表意實踐,兩次出現代表了導演不同時期的個人感悟,映照了不同人生階段的心境。《唬爛三小》以導演好友杰仔的葬禮結束,靈堂里紙扎的公寓和賓士車,寓意著在世之人期望杰仔能在彼岸空間中過上美好生活。高度隱喻性質的空間構型手法在此處已經出現,《同學麥娜絲》中閉結的“紙扎屋”和《大佛普拉斯》中肚財的“飛碟”是對此類手法的沿襲。“飛碟”里到處是肚財抓來的娃娃,貼滿了從雜志上剪下的美女,暗含了肚財對于愛的向往,倒映肚財的精神世界。“紙扎屋”建在鄉間的一座老房子里,沒有真正的使用價值,卻體現了角色們的世俗欲望。這座“紙扎屋”是花園小屋,門前有噴泉和小狗,屋后是白雪皚皚的富士山。屋內家具電器一應俱全,還有添仔想要的劇本和罐頭,想得到的麥娜絲。這既是閉結渴求美好生活的體現,同時以紙扎品形式存在的劇本和麥娜絲又包含了閉結對于好友們的關心,以及導演對于舊友杰仔的懷念。
《唬爛三小》和《大佛普拉斯》作為前文本積極參與了《同學麥娜絲》空間敘事的建構,將導演不同時期的個體經驗融入到了影像文本中,相互關聯又相互解釋。相似的空間構型卻生成了不同的文本意義,在互文中呈現了黃信堯對于生命哲學的思考。《唬爛三小》是青年的迷惘與期待,《大佛普拉斯》表達了對小人物的憐憫,而《同學麥娜絲》在前兩個文本的基礎上講述了中年人的生活殘酷物語,形成了黃信堯前進又回旋的作品序列。
二、多重空間映射生存困境
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被視為批判性后現代主義的先祖 ,其名著《空間的生產》(1974)分析了其三種“空間認識論”:可感知的、物質的第一空間,構想或想象的第二空間和無窮開放、不斷解構與重構的第三空間[2]。《同學麥娜絲》的空間構型被劃分成以“房子”和“城市”為主的第一空間,第二空間是被幸福籠罩的回憶和想象空間,第三空間是對前兩個空間的錯位組合及再生產。
《同學麥娜絲》中的臺中市被高房價和政治因素所裹挾,城市被劃分為兩部分:一是私人空間的“房子”,二是后政治語境中公共空間的“城市”。現代化城市對工具理性的崇拜,致使人的主體性和情感性被忽略。作為第一空間的物質空間成為劃分階級的標志,人逐漸被“房子”這一物理空間所奴役。電風是四位男主中唯一買房的人,也是唯一擁有婚姻和孩子的人。房子已經不僅僅是用于休息的私人空間,而成為人在公共空間中搶占資源的保障。身處后政治語境之中,人人參與政治,城市成為了政治活動的容器。罐頭在戶政事務所從事查戶口工作,通過罐頭的視角呈現了底層邊緣人物生存空間。411號大哥的房子是在火車軌道旁用竹竿和粗布搭建而成的,并沒有所謂的屋頂和墻壁;住在破舊公寓的陳金龍,因為產權糾紛而從一個愛嘮叨的人變成了啞巴,把想說的話都寫在墻壁上。他們成為強權和資本驅趕的對象,同時他們在“房子”中做出無聲的抵抗。罐頭整日騎著機車游走在城市的街道,那里總是有荒蕪的草地和空曠的小路。而在以添仔為代表的權力階層眼中,“城市”必須是熱鬧的、欣欣向榮的景象。添仔在競選過程中,調動各種媒介資源侵占公共空間。巨幅的宣傳海報占領城市的視覺高地,喧鬧的舞獅隊渲染出一派祥和的氣氛。高音喇叭里不停播放宣傳語,轟鳴而過的競選車隊成為了城市里的漫游者,但觀眾目之所及之處盡是蕭條的街景和稀疏的普通百姓。正如福柯所言:“空間是權力實施的手段,權力借助空間的物理性質來發揮作用[3]。”添仔的競選團隊甚至隨意闖入民眾的生活空間,將電風的婚禮和閉結的葬禮作為政治宣傳的舞臺。權力階層對普通民眾私人空間的肆意霸占,與它將底層民眾驅逐出公共空間的行為具有鮮明的諷刺意味。
回憶、想象與夢境構筑了《同學麥娜絲》中的第二空間。片名中的“同學”二字指涉的是充滿青春懵懂、單純美好的學生時代,讓人聯想到的是學校和教室。然而學校與教室并未出現在影片的畫面中,出現的只是麥娜絲從事色情按摩的“黑桃那棟”。麥娜絲是罐頭當年苦苦暗戀的校花,如今罐頭終于有機會得到麥娜絲,但他卻逃走了。正如年少時在腦海中假想自己與麥娜絲之間的聯系一樣,人近中年的罐頭仍然借夢境與心中的校花產生聯結。弗洛伊德認為,“夢的本質是愿望的滿足,是無意識中的被壓抑的欲望通過夢的種種運作,得到象征性的滿足[4]。”罐頭將自己最真實的欲望掩藏在了夢境之中,側面反映出他在現實物質空間中的孤獨。除此之外,導演在影片末尾設置了一個并不存在的想象時空,在那里四個人各有幸福的理由。男人穿著西服,女人身著晚禮裙,他們坐擁豪車,在高檔酒店里觥籌交錯。想象中的替代性補償,是對現實時空的呼應和安撫,也是人物潛意識的體現。
第三空間是對前兩種空間的重組,是理性與非理性共存的空間形態。借由電影的蒙太奇手法,將物質空間、回憶、想象等畫面交錯放置。第三空間是由不斷建構和解構的過程建立起來的,因而影片中有一個重要的人物牽引著觀眾的視角在多重空間中游移,那就是“老李”。老李在影片中出現了四次,分別對應了三個空間。第一次出現是扮演桑拿經理,此時他是在人間討生活的普通百姓。他并不關心罐頭自殺,他只關心罐頭因為自殺而未付清的欠款。第二次出現是以“老李”的身份,此時他是接應亡人通往西方極樂世界的領路人,并在第四次出現時接走了閉結離世的靈魂。第三次出現是以神父的身份,此時他是上蒼的使者。神父所處的臺灣鹽水天主堂的空間形象也頗具形式意味,整個建筑空間是中式風格與天主教文化的雜糅。教堂壁畫全部采用中國畫的手法呈現,隨處可見祥云、仙鶴、二龍戲珠紋等中國古典裝飾紋樣。導演用近景鏡頭強調了處于教堂中心位置的一幅壁畫,這幅畫仿照達·芬奇《最后的晚餐》繪制而成,人物的面孔與穿著、餐具和食物卻都經歷了本土化改造,中西方文化在這一空間內融合自洽,是具有重構性質的空間實踐,建筑空間裝飾的類型雜糅側面呈現了人們精神世界的繁雜。“老李”的三重身份對應了不同的空間,在現實與虛擬中來回切換,道出了人物精神和物質空間的雙重混亂。
三、時間藝術延伸表意空間
音樂是時間藝術,用時間藝術去構筑空間即是一種出位之思。所謂“出位之思”指的是一種表達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也試圖模仿另一種媒介的表達優勢或美學效果。就敘事而言,“出位之思”就表現為跨媒介敘事[5]。音樂始終是黃信堯創作中重要的表意媒介,如《帶水云》(2010)中渾厚的音樂為畫面增添了引人沉思的意味;《唬爛三小》結束時響起了《找愛》,淺吟低唱中讓青春歲月變得悠遠綿長。音樂以其極強的渲染能力,在媒介互滲中參與隱性敘事,將人物和導演的心理空間外化。
《同學麥娜絲》獲得了第57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提名,全片共19首插曲,串聯整部電影的敘事脈絡。器樂在影片的縫隙中補足情感,聲樂與畫面一同闡述人物心理空間。影片伊始,音樂《1比2.35》比畫面先出場,以其俏皮歡快的節奏引出全片,奠定了荒誕的敘事風格;老李出場時的《金童玉女》,詭異空靈之感彌漫開來;到閉結和阿月約會時《阿月閉結》的浪漫抒情;再到阿枝質問添仔是否有外遇時響起頗具戰爭場面的《男性荷爾蒙防備戰》;又如閉結邀請朋友們去他的“紙扎屋”聚會時的《同學》,以聲畫對位的方式反襯出他們內心的憂愁…… 烏克麗麗、貝斯、斑鳩琴、薩克斯風、簫與鼓的聲音在影片中交錯出現,各種音色之間的碰撞充滿怪誕之感。器樂充滿了多義性和模糊性,積極調動觀眾情感,增強了畫面的敘事張力,成為空間塑造的重要元素。與器樂一樣,《同學麥娜絲》的聲樂運用也非常精準。聲樂因歌詞而具有更為明確的所指意義,以其文學性符號作為空間的腳注而存在。《同學麥娜絲》中的配樂出現密度高,且風格多變。時間藝術的非線性流動,在視覺空間的基礎上延伸了表意空間。再如電風跳湖和閉結開車三組長鏡頭所組成的段落,湖水與落日,一冷一熱,一暗一明,正如混沌的人生和宇宙。此時《漏電的插頭》聲音漸起:“春夢留痕坎坷青春,甘愿忍受孤獨的滋味,少年的日子怎樣安排。”全片的情感落腳點是影片最后由黃信堯介紹的歌曲《卡通手槍》,在帶有自嘲口吻的音樂中結束全片。歌詞中出現的如“鐵金剛”“小飛俠”“惡魔黨”等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意象,在時間維度上建構了與影片所表現的中年時空不同的空間場域,擴充了表意空間。又因當下中年生活的失意,使得歌詞中展現的年少光景顯得分外幸福,與現實時空產生強烈反差凸顯了中年人的生存困境。時間藝術用聲色和文學符號參與到了空間塑造的過程中來,延伸了電影的表意空間。
四、結語
人存活于空間之中,處于運動與變化之中。黃信堯在《同學麥娜絲》再次探討了人的來路與歸途,但導演這一次給出的態度與《大佛普拉斯》稍有不同。《大佛普拉斯》是在做加法,是在叩問社會和人心;而《同學麥娜絲》是在做減法,是認同“萬物之始,大道至簡”的理念,傳達出與“混沌”同在的生活態度。整部影片作為中年版的《唬爛三小》更是黃信堯個人意識的集中體現,是對年少時光的無限眷戀。
作者簡介:晁晨晨(1994—),女,漢族,江蘇徐州人,天津工業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為視聽藝術創作。
參考文獻:
〔1〕程錫麟.互文性理論概述[J].外國文學,1996(1):72-78.
〔2〕麥永雄.后現代多維空間與文學間性——德勒茲后結構主義關鍵概念與當代文論的建構[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37-46.
〔3〕汪民安.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J].國外理論動態,2006(1):46-52.
〔4〕曹海峰.精神分析與電影[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06.
〔5〕龍迪勇.“出位之思”與跨媒介敘事[J].文藝理論研究,2019,39(3):184-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