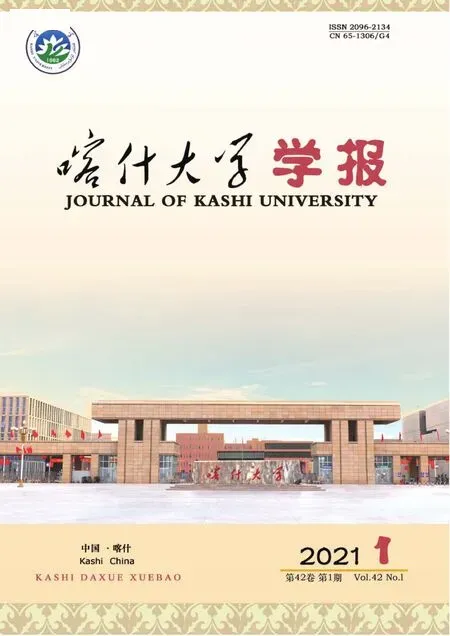“NP+自己”結構中“自己”的話語功能探究
林 青,王夢莉
(喀什大學 中國語言學院,新疆 喀什 844006)
“自己”是由反身代詞“自”和泛指代詞“己”構成的復合詞,“自己”具有這兩個詞的特性,形成了具有反身代詞特性和泛指代詞特性的復合體,[1]程工(1994[2]、1999[1]),楊麗君(2007)[3],李小妮(2018)[4]等學者通過對古漢語中“自”和“己”的考察以及與英語等語言進行對比,認為“自己”是現代漢語中的反身代詞,但從歷時演變以及跨語言的角度來看,“自己”又不完全符合反身代詞的特征。
以往人們對“自己”的研究多是從喬姆斯基的管轄約束理論入手,如胡建華(1998)[5],李京廉(2004)[6],劉禮進(2007[7]、2008[8])等對“自己”一詞的指稱、照應方面進行句法語義的研究,雖然成果較多,但一些語言現象尚未得到較好解釋,如長距離“自己”的指稱、照應、指向性、阻斷性等一系列問題。
與以往人們關注的長距離“自己”不同,本文所關注的是“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這里的“自己”指稱較為明確,也不存在長距離約束等問題,“自己”與“NP”皆具有指稱功能,二者的連用讓人感到贅余,但這一結構卻又常常在日常交際中出現。結合現實語境來看,“NP+自己”結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有兩點問題值得我們思考:(1)從語言經濟性的角度來看,“NP”與“自己”語法功能基本相似,都具有指稱功能,二者連用是否讓人感到贅余?如果贅余,問題是在“NP”還是在“自己”?(2)在“NP+自己”結構中“NP”已經承擔了指稱功能,“自己”的存在有何意義?本文將通過對相關語料的觀察、描寫,從認知語用學的視角對“NP+自己”結構中“自己”的話語功能進行探究,對以上兩個問題進行解答。
本文語料來源于北京大學CCL 語料庫,通過對現代漢語作品中的“自己”一詞進行檢索,共得到8574 條語料,考慮到文章研究內容是“NP+自己”結構中“自己”的話語功能,因此本文從《雷雨》《殘霧》等戲劇中選取了160 條典型語料進行分析研究。本文所談的“自己”僅為“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NP”大多都是人稱代詞和稱謂語。但也有特殊情況,一些文學作品中會使用擬人的修辭手法,這時的“NP”就不一定是人稱代詞了,如:“小樹自己長大了”,“NP”就是“小樹”[9],此類情況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NP+自己”結構
(一)“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
“自己”是現代漢語中的反身代詞,一方面漢語中的“自己”與英語中的反身代詞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另一方面漢語的“自己”又有著英語中反身代詞所不具有的特點:從歷時演變上看,“自己”是由反身代詞“自”和泛指代詞“己”融合而成的,它兼有二者的特性;從跨語言的角度上看“自己”并不完全符合反身代詞指稱或形態的最簡性、與代詞的分布互補性、照應和強調用法重疊這三種特征,“自己”并不屬于純粹的反身代詞。[1]現代漢語中的“自己”可以是“光桿”的自己(見例1)也可以是“復合”的自己(見例2),本文中的“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就屬于后者“復合”的自己,如例(2)中在“自己”前加了第一人稱代詞“我”構成了“我自己”。如:
(1)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殘霧》)
(2)我沒工夫再聽你那一套,連我自己的事還愁不過來呢。(《殘霧》)
(二)“NP+自己”結構中的“NP”
“NP+自己”結構中的“NP”一般是人稱代詞,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復數,如例(3)中的“我”是單數,“你們”是復數,也可以是稱謂語,如例(4)中的“老爺”;當“NP”的所指為無生命事物時,“NP+自己”結構后的動詞具有自動的意義,如“門自己開了”;當“NP”所指為有生命而非人時,“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是一種擬人的修辭手法,如“花自己開了”(這種情況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在一些形態豐富的語言中動詞會通過形態變化來體現這一區別。
(3)你們不明白別的,還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嗎?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會寫文章,登在報紙上!你們自己都常把“大學畢業”掛在嘴邊上!(《殘霧》)
(4)老爺說放在這兒,老爺自己來拿。(《雷雨》)
(三)“NP+自己”結構中“NP”與“自己”
1.“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與NP 指稱一致
在“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與NP 指稱一致。如例(5)“我自己”中的“自己”指的就是第一人稱“我”;例(6)“你自己”中的“自己”指的就是第二人稱“你”;例(7)“她自己”中的“自己”指的就是第三人稱“她”;例(8)“老爺自己”中的“自己”指的就是“老爺”。“自己”與“NP”指稱一致還包括數范疇上的一致,如例(3)第一個“自己”前的NP 是第一人稱單數“我”,這時的“自己”指的也“我”;當第二個“自己”前的NP 是第二人稱復數“你們”,這時的“自己”指的也是“你們”。由于漢語自身的特點,這里的“自己”沒有顯性的形態變化,但依然蘊含了“數”的范疇。
(5)我就忘了現在,(夢幻地)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親,并且忘了我自己。(《雷雨》)
(6)你自己說一遍。(《雷雨》)
(7)大概她是不愿意吧?為著她自己的孩子,她嫁過兩次。(《雷雨》)
(8)這是老爺自己擺的,說什么也不肯搬出去。(《雷雨》)
2.“NP+自己”結構中“自己”無形式上的強制性
“NP+自己”結構中“自己”無形式上的強制性。將以下例(9)中的“自己”刪除即“我負責任”,句法上依然完整,句子字面意也沒有發生實質的改變;將例(10)中的“自己”刪除即“請你放尊重一點”,則與例(9)一樣,句法完整,句子字面意也沒有發生改變,例(11)(12)與例(9)(10)情況一致,不再贅述。
“NP”卻與之相反。如例(9)“我自己負責”,若將“我”省略,即為“自己負責”這時我們無法判斷“自己”指代的是什么,結合語境可以推導出這里的“自己”指的是“我”,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語境關聯下“NP”就可以取消;例(11)省略“NP”之后就成了“自己的東西我可以派人送去,我有一箱子舊衣服,也可以帶去,留著她以後……”顯然這個句子中“自己”語義指向不明。再如例(12)如果將“NP”省略則為“那是自己”,“NP”的省略則會使句子的意義發生改變。
(9)我做的事,我自己負責任。(《雷雨》)
(10)用不著你問。請你自己放尊重一點。(《雷雨》)
(11)她自己的東西我可以派人送去,我有一箱子舊衣服,也可以帶去,留著她以後……(《雷雨》)
(12)那是媽自己。(《雷雨》)
3.“NP”與“自己”皆不贅余
由上一小節可知,“NP+自己”結構中“NP”與“自己”都具有指稱功能且指稱一致,那么在“NP+自己”結構中“NP”與“自己”的作用完全一致嗎?為此需要對“NP”和“自己”是否可以取消進行考察。我們將人稱代詞(“三身兩數”)設為自變量,將“NP+自己”結構中“NP”與“自己”的可取消性視為因變量,為方便論述,在此使用筆者內省的語料。
(13)a 我(們)自己會贏 a’我(們)會贏a”自己會贏
(14)b 你(們)自己會贏 b’你(們)會贏*b”自己會贏
(15)c 他(們)自己會贏 c’他(們)會贏*c”自己會贏
例(13)-(15)中,我們可以發現在“NP+自己”結構中“自己”的取消不會改變句子的句法和語義,如果將“NP”取消僅保留“自己”,當“NP”為第一人稱時,說話人視角和主語視角重合,因此“自己會贏”中的“自己”指的就是第一人稱和說話人的視角,無歧義產生;當“NP”為第二、三人稱時,“自己”則無法單獨承擔指代功能。
由此得知在“NP+自己”結構中,“NP”承擔了主要的指稱功能,“自己”輔助“NP”進行指稱。若“自己”與“NP”的功能相同,“自己”的存在是否贅余?若不贅余“自己”在“NP+自己”結構中有怎樣的作用與價值呢?下文將結合實例進一步對“NP+自己”結構中“自己”的可取消性進行考察。
(16)楊太太自己笑了笑,不再勸留。(《殘霧》)
(16’)楊太太笑了笑,不再勸留。
(17)媽,您為什么不信您自己的女兒?(《雷雨》)
(17’)媽,您為什么不信您的女兒?
例(16)(17)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自己”的取消對句子的句法語義沒有影響,但是取消了“自己”的句子卻缺少了一些說話人的主觀認識、情感和態度。如例(16’)“楊太太笑了笑”句義沒有發生改變,但這只是對“楊太太”表情的一個客觀的描寫,當在“楊太太”后加了“自己”時,則增加了說話人的主觀認識,強調了“笑了笑”的只有“楊太太”一人,暗含了其他人都沒笑的意義;例(17’)“您的女兒”也是領屬意義的客觀表述,但是在“您”后加了“自己”時,凸顯了說話人的主觀情感,強調了“您”與“女兒”之間的領屬關系,表現出了“女兒”希望得到母親信任的強烈情感。
由此可知在“NP+自己”結構中,“NP”與“自己”皆不贅余,“NP”承擔了主要的指稱功能,“自己”在輔助“NP”進行指稱外,還具有一定的話語功能。下面我們將從話語功能的角度對“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進行更深入的考察。
三、“NP+自己”結構中“自己”的話語功能
呂叔湘認為“自己”復指句子時,已經出現的“人”是與“別人”相對的,這種相對符合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個體自我”(individual self)和“顯著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認知對立(Rrewer and Cardner 1996),使用“自己”是為了凸顯與他人的不同,其認知上會有非本體的參照。[10]
吳建明從名詞短語內、小句內和小句外三個形式特征對“自己”的功能進行了描寫,并用分類樹的形式呈現了包含“自己”義庫藏的人稱義庫藏形式結構,他認為“NP+自己”屬于指稱在名詞短語內表示身份,“自己”在小句內、外分別有主語視角、共指、移情等功能。[10]
依據兩位學者關于“自己”及“NP+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結合語料實際考察發現,“NP+自己”結構中的“自己”具有主語視角及移情、反預期標記、焦點標記、主觀性表達這四種話語功能。
(一)“自己”的移情功能及主語視角
吳建明指出由于漢語沒有專門表達主語視角(logo-phoricity)或移情的代詞,“自己”兼為這類表達的載體。[10]“移情”是指言者對自己在句子中所描述的事件或事件參與者的態度;[11]“自己”的使用有助于“NP”的語義指向“主語”,如在“NP1+V+NP2+自己”結構中,當“NP”為第三人稱時,如果將“自己”省略,“NP2”除了指代“主語”外還可能指代“聽話人”,保留“自己”就可以避免“NP2”指代“聽話人”的歧義。下面我們結合實例對“自己”的移情功能及主語視角進行闡釋。
(18)我收拾我自己的東西去。(《雷雨》)
(19)你自己覺得挺不錯,你到家不到兩天,就鬧這么大的亂子,我沒有說你,你還……(《雷雨》)
“自己”具有一定的移情功能。如例(18)所說的言語都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敘述的,所表達出的情感意愿也都是“我的”,如果將句中的“自己”刪除,句子的基本語義不會發生改變,而使用“我自己”強調了收拾的東西是“我的”不是“他人的”,體現出了言者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再如例(19)“覺得挺不錯”的是“你自己”,如果將句中的“自己”刪除,句子的基本語義不會發生改變,“自己”的使用強調了“覺得不錯”的只有“你”,只有站在“你”的角度上看才會覺得挺不錯,體現了言者的態度即“你”覺得這件事情不錯,但與“我”(言者)的認知不符。
“自己”具有一定的主語視角。對比例(18)(19)可以發現說話人的視角和主語的視角是不同的,例(18)中的“自己”指的就是說話人,說話人的視角和主語的視角是相同的;而例(19)的“自己”指的是主語“你”,說話人的視角和主語的視角是不同的。由此可見“自己”表達的是主語視角,而不是說話人的視角,當“NP”為第一人稱時,說話人與主語的視角是重合的,進一步體現了“自己”的主語視角及移情功能。
(二)“自己”的反預期功能
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體現的是說話人的視點或態度,是語言主觀性的表現。[12]人們談到預期或反預期時往往是把某一個詞放到特定的表達式中進行考察,來判斷該詞是否是預期或反預期標記。在這些特定的表達式中,反預期意義通常表現為一種話語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13]通過對語料的觀察,我們發現“NP+自己”中“自己”雖然不能作為反預期標記,但有時也會承擔起反預期的功能。
(20)你回頭告訴太太,說找著雨衣,老爺自己到這兒來穿,還要跟太太說幾句話。(《雷雨》)
(21)可是老爺吩咐,不要四鳳,還是要太太自己拿。(《雷雨》)
(22)王局長剛走,老爺自己在陪著呢。(《雷雨》)
例(20)只說“老爺到這來穿”,會讓人們覺得老爺到太太那穿雨衣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加了“自己”強調了是“老爺”到這來穿,說明了一般情況下老爺不會“到這”穿雨衣,也從側面說明了這與聽話人的預期不同。例(21)如果說“還是要太太拿”不一定是太太本人去拿,太太讓下人去拿也可以理解成是太太拿的,加了“自己”強調了必須是太太本人去拿,之所以要強調“太太自己”是因為這與人們正常的預期是不同的,前面那句“不要四鳳”也是為了強調要太太本人拿,也從側面說明了“太太自己拿”與人們預期是相反的。例(22)也是如此,“自己”強調了“陪著的”只有老爺沒有其他人,這與問話人的預期是不同的,而“王局長剛走”進一步說明了在問話人的預期中,“陪著的”除了老爺至少還有“王局長”。
可以看出,雖然“自己”不是典型的反預期標記,但在特定語境下也會承擔起反預期的功能。
(三)“自己”的焦點標記功能
話語交際中說話人使用“NP+自己”結構往往是為了通過“自己”來強調“NP”,使“NP”成為焦點。
(23)你自己要走這一條路,我有什么辦法?(《雷雨》)
(24)你跟老爺說,說我沒有病,我自己并沒有要請醫生來。(《雷雨》)
例(23)如果沒有“自己”,句子的焦點可能是“你”,也可能是“這一條路”。使用了“自己”就明確了句子的焦點是“你”,而不是“這一條路”,指明了說話人要強調的是“走這一條路的人”,而不是這一條路。例(24)如果沒有“自己”,句子的焦點可能是“我”,也可能是“要請醫生”;使用了“自己”強調了“我”是句子的焦點,指明了句子的重點是“我”的主觀意愿,而不是“要請醫生”。
一般來說,動作和發出動作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句子的焦點,說話人使用“NP+自己”結構使“NP”成為句子焦點,強調了發出動作的人,而非動作本身。
(四)“自己”的主觀性表達功能
“主觀性”是指說話人的語言表達含有說話人“自我”的表現成分,是語言的一種特性。[14]說話人所說的話不一定都具有主觀性,但是說話人使用“NP+自己”結構時,“自己”在一定語言環境下具有了主觀性的表達功能。
(25)我已經想得很透徹,我自己這些天的痛苦,我想你不是不知道,還請你讓我走吧。(《雷雨》)
(26)她現在回到她自己的家里什么都不順眼啦。(《雷雨》)
例(25)“自己”的使用是為了強調“這些天的痛苦”是她獨自一人經受的,在這件事情里痛苦的只有她沒有別人。這種想法不一定與事實相符,或許只是說話人自己主觀的想法。
由“自己”的焦點標記功能可知,說話人使用“NP+自己”結構除了避免歧義外,還有突出動作發出者的目的。如果例(26)改寫為“她現在回到她的家里什么都不順眼啦”,我們可能會把焦點放在“回家”上,也可能把焦點放在“她”上,如果說話人想要強調這個家是“她所擁有的”,就需要使用“自己”來表達出說話人的主觀意愿。由于“自己”的焦點標記功能,說話人可以通過使用“自己”來凸顯“NP”強調發出動作的人,表達了說話人的主觀意愿。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NP+自己”進行結構考察,發現:一是“自己”與NP 指稱一致;二是“NP+自己”結構中“自己”無形式上的強制性;三是“自己”與“NP”都不贅余,“NP”承擔指稱功能,“自己”在協助指稱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話語功能。通過對“NP+自己”結構中“自己”話語功能的考察發現,“自己”具有主語視角及移情、反預期標記、焦點標記、主觀性表達這四種話語功能。
總結前人經驗可知,我們在對“自己”進行研究時,不僅要從句法語義層面出發,同時也要觀照到語用層面,對“自己”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考察,以便我們更加全面地去認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