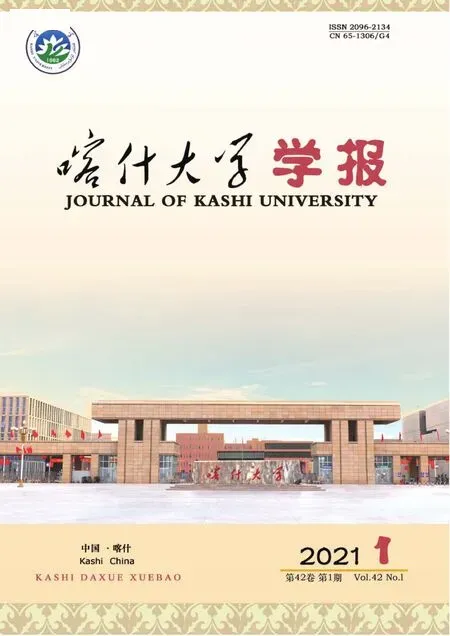內地高校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適應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徐百靈
(喀什大學 人文學院,新疆 喀什 844006)
為解決少數民族地區人口接受優質教育、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問題,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教育政策傾斜,鼓勵少數民族青少年學生到內地教育資源發達的省市接受優質教育,因而,新疆的各族青少年紛紛來到內地求學。但由于新疆少數民族在社會生活習慣、文化傳統等方面與內地社會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進入大學校園后,會面臨文化的適應問題。無論是從人的個體發展,還是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對在內地學習生活的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適應研究都非常緊迫和重要。
一、研究文獻回顧
(一)文化適應與適應的傳播管理
文化適應研究早在20 世紀40 年代就已經在西方開展起來,學者們從不同理論視角研究文化適應,出現了壓力應對和文化學習兩個新的理論視角。壓力應對將文化適應看作是個體體驗壓力、采用策略或適宜的“處置”方法的過程;文化學習理論則認為文化適應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強調對個體進行適宜的干預策略,如進入新環境前的文化準備,到東道國以后的教育以及學習相關社會文化技能等。[1]53
古迪昆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認為,當陌生人進入新環境時,由于不了解東道國的情況,在與東道國國民交流時,就會產生認知上的不確定和行為上的不知所措,因此會引起緊張不安和焦慮,導致文化休克。為了適應他文化,陌生人必需進行有效的傳播,管理其焦慮和不確定性。[2]
在當下的網絡傳播環境中,社交媒體兼具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特點,也是目前網民獲得信息的重要渠道。我國已有學者從跨文化傳播管理的視角,對跨文化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人際交往、社交媒體使用進行了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周瑋的《跨文化傳播視角下國際留學生的人際互動研究》(2015),安然、陳文超《移動社交媒介對留學生的社會支持研究》(2017)等。
(二)社會支持網絡與文化適應
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非常關注社會支持網絡對個體進入新環境后積極適應當地社會的重要性(Searle &Ward,1990)。[3]有少數研究認為,不管是主流社會的支持,還是原文化社會支持都有助于跨文化適應(Ward &Rana-Deuba,2000)。[4]如,一些針對留學生的研究發現,在校園里由同胞組成的學生團體可以給個體提供信息、情感和有形的以及智力性的幫助(CanchuLin,2006)。[5]當然,也有研究表明同胞圈子的群體化傾向是一把雙刃劍,不但有正面效果也有副作用,[6]當個體在得到自己同胞支持的同時,也有可能降低他們與當地人交流的愿望,這種同胞圈子反而阻礙了個體對當地文化的學習適應。
(三)我國跨文化適應研究現狀
我國的跨文化適應研究起步較晚,始于20世紀80 年代。其主要研究的方向也涵蓋了國際上主流研究中的文化適應策略、文化適應階段、壓力應對以及心理健康等,研究方法也基本與國際主流研究相同。我國跨文化適應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旅居者、農民工、少數民族等。對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研究,其主要的研究視角側重于從民族學、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方面展開(張勁梅,2008;湯奪先,2012;張東輝、黃晶晶,2015;安潔、萬明鋼,2011;廖傳景等,2013;胡疊泉,2016;吳日暉,2020;安娜,2020)。
而從傳播學科的視角出發,對少數民族學生文化適應的研究成果相對就比較稀少,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內地求學的藏族中學生,如《伴而不同:跨文化傳播語境下內地西藏班(校)學生的同伴交往研究》。[7]針對新疆少數民族學生在內地的文化傳播與適應研究的研究成果非常匱乏。因此,本論文試圖從人際傳播的角度出發,運用量化與質性研究結合的方法,去呈現和分析在內地求學的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適應情況。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中對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適應狀況的描述包括教育環境的適應,氣候、飲食及生活習俗適應,心理適應等三個方面。
(一)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投放線上問卷390 份,線下問卷300 份,剔除無效問卷26 份,共獲得有效問卷664 份,問卷有效率96.2%。線上問卷主要在內地部分高校的少數民族學生工作QQ 群、少數民族學生交流QQ 群和微信群中發放;線下問卷則通過實地隨機發放的方式在方便抽樣的部分高校里進行發放。
通過問卷調查可以獲得高度概括性的反映少數民族大學生總體狀況的研究數據,再結合有代表性的個體樣本的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來獲得反映個體在具體文化適應情境下的材料。
2.深度訪談
通過深度訪談獲得有效樣本36 個,其中男生13 人,女生23 人;維吾爾族25 人、哈薩克族6 人、柯爾克孜族3 人、回族2 人。受訪個體在內地上學時間從8 個月到12 年不等。
3.觀察法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進行了參與式觀察,分別參與了一些少數民族同學在課余時的集體活動,旁聽并觀察其在公共課程的課堂學習和討論活動中的表現情況。通過參與觀察充分掌握了他們與當地同學老師學習互動方面的情況。
三、研究分析
(一)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適應的基本情況
1.性別、民族、年齡
在664 份樣本中,男性212 人,占31.9%;女性452 人,占68.1%。維吾爾族493 人,占74.2%;哈薩克族95 人,占14.3%;回族22 人,占3.3%;蒙古族20 人,占3%;柯爾克孜族13 人,占2%;其他新疆少數民族共21 人,占3.2%。
樣本年齡大多在18-25 歲(占比92.5%),26-30 歲的有34 人,占總數的5.1%;31 歲以上的14 人,占2.1%;18 歲以下的2 人。由于學習基礎薄弱,再加上語言的障礙,大多數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學習專業課程之前都要進行預科一年的基礎學習,所以他們一般要比同年級的孩子大一到兩歲。
2.受教育情況及生源地
受訪者受教育程度中,本科層次的629 人占,94.7%;碩士研究生9 人占1.4%;博士研究生19 人,占2.9%;其他學歷的人數占1%。來自民語言班的生源占3.3%,來自漢語言班的生源有29.5%,來自雙語班的生源占30.5%,而從內地民族班考入的大學生最多,占總數的36.7%。另外,樣本中有2.4%的人來自牧區,43.3%的人來自鄉村,32.4%的來自縣或縣級市,21.9%的人來自省城或地級市。
3.來內地時長、國語水平狀況
在以往的文化適應研究中認為,個體剛來到新環境時,一般會對周圍的事物感到比較新奇,并有一定的熱情面對新事物,一般來說這一時期會持續1-6 個月。但當個體經歷了一些陌生環境中的困難后(如生活習慣的差異、新環境中與陌生人交往的困難等),會產生一定的焦慮、想家、不滿甚至自卑等心理情緒。在一段時間后,個體逐漸熟悉當地環境,并且學會了新的生存技能,很多人會設法克服困難,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逐漸適應新的環境。本次調研中所獲得的樣本,基本上覆蓋了個體從來到新環境到最終適應新環境這一過程中的所有情況。本研究中所獲得的樣本來內地時間長度分別為:1-6 個月的占6.5%,6-12 個月的占10.3%,1-2 年的占28.4%,3-5 年的占3.2%,6 年以上的占19.4%。
在語言掌握情況中,認為自己國家通用語水平較差的占3.8%,水平一般的占17.6%,水平良好的占40%,優秀的占38.6%。雖然,總體國家通用語水平較好,但在與當地人進行交往、融入所在地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取得良好的學習成績方面,語言水平的高低嚴重影響著這部分大學生的適應程度。
(二)適應壓力應對的基本狀況
本研究適應壓力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級量表來測量樣本個體面對適應中所遇到的壓力時的困難程度,分別為:1=沒有困難、2=有點困難、3=一般困難、4=比較困難、5=非常困難。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適應壓力選項進行因子分析后,得到4 個因子,分別將其命名為交往互動壓力、文化認知壓力、環境適應壓力和心理情緒四個新的變量(見表1)。

表1 文化適應壓力選項因子分析結果
根據統計結果發現,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適應壓力選項測試得分較高的前五項中:取得滿意的學業成績(92%)、應對學習的壓力(82%)、找到自己喜歡吃的食物(70%)、適應大學的教學環境(58%)、應對遇到的偏見(54%),分別屬于適應壓力因子中的環境適應壓力和文化認知壓力。說明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適應中存在著較為一致的困難,且大部分個體在應對內地的生活環境、適應大學教學方式取得良好的學習成績方面存在較大的困難,在文化認知方面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甚至出現相互的誤解。
(二)影響文化適應的因素分析
1.性別、居住時間、國家通用語水平與文化適應
在適應壓力與性別交叉分析中發現,男性與女性在面對適應壓力時,所感受到的適應困難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面對適應中的壓力時,總體上女性好于男性,即女生感受到的壓力要小于男生。見表2。

表2 性別與文化適應壓力均值交叉表
表2 中,在“和內地學生交朋友”(M=1.51/男,M=1.62/女),“讓自己被內地同學理解”(M=1.78/男,M=1.97/女),“應對那些盯著我看的人”(M=1.79/男,M=1.89/女),“覺得自己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M=1.76/男,M=1.8/女),“積極參加團 體活動”(M=1.63/男,M=1.71/女)這五項的均值比較中,女性適應壓力的狀況要略低于男性。在各項適應壓力項目測試中,男性在面對大多數方面的困難時,感受到的壓力均值都高于女生,但在“和內地同學交朋友”“參加團體活動”以及“應對別人的眼光”時,男生所感受的壓力要小于女生。這可能是因為男性更愿意參加體育戶外活動,在感知外界眼光時不如女生那樣敏感。
隨著在內地居住時間的延長,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逐漸適應了當地氣候、飲食、大學的生活環境,在適應大學的教學環境及方法、應對學習的壓力等方面困難越來越少,也能夠正確看待自己的學習成績;包容和接納其他文化及生活方式,越來越能夠從當地人的角度看問題,并能積極地參加團體活動,與內地學生交朋友,適應內地的人際交往規則,逐漸能夠處理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數問題。見表3。

表3 文化適應的影響因素
調研數據也顯示,個體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的水平與來內地的時間長度之間并無相關性,而是與其所交往的漢族及其他各少數民族朋友的數量之間呈正相關,即個體在內地時間越長,使用國家通用語的能力越強,其在內地與人交往的壓力就越小(P=0.000<0.01,P=0.000<0.01)。同時國家通用語水平的高低又對適應內地生活學習環境、提高學習成績、獲得良好的人際溝通起到正向的促進作用(P=0.004 <0.01,P=0.001 <0.01,P=0.000 <0.01)。因此,具有開放的心態并與當地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進而提高自身的語言學習和應用能力都是個體減少適應壓力、提高適應能力的良好途徑。見表4。

表4 國家通用語水平、居住時間、人際關系與適應壓力相關性分析
2.文化交往障礙的自評分析
本研究按照問卷作答選項、人數百分比高低順序統計排列了受訪樣本自評交流受阻的前五項因素(見表5)。在對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的調研中發現,影響大學生與內地學生以及當地人進行交往交流的因素有許多,不同民族的個體在自評文化適應交往障礙的因素時,也有一定的差異,但問卷作答選中率較高且不同民族共同具有的因素是“風俗習慣差異”“個人性格因素”和“沒有共同的愛好”這三個因素。說明新疆各少數民族與內地社會主流文化差異較大,是影響個體間交流的主要因素;個人性格差異和共同愛好的缺乏也是影響少數民族大學生與內地文化個體間交往、交流的重要因素。這在本研究后續的訪談中也得到相應的印證。許多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表示,由于自己的性格比較內向,與內地同學老師交往時不太善于表達自己,或者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往往不是很積極主動地與人交往,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他們與當地人以及同學老師交流的機會,即便有交流也是非常被動的。

表5 文化交往障礙自評表
另外,部分個體反映由于成長環境差異較大,個體之間的生活經歷也有很大不同,在與內地同學相處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大學生經常會感到自己的個人經歷無法被人理解,往往出現“話不投機”“缺少共同話題”的情況,這也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間交流受阻的重要原因。當然,在文化交流受阻的原因中,不同民族個體對交流受阻因素的感知也是有一定差異的,例如,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樣本的統計結果前五項中都顯示出“生活方式”的不同是交流出現障礙的重要因素,但是樣本中回族大學生個體并沒有在前五項中反映出這一影響因素,而哈薩克族和柯爾克孜族大學生則分別在“缺少時間和精力”“缺乏人際交往技巧”兩個選項上出現了較高的選中率。在文化交流受阻的因素的自評中,雖然“語言障礙”選項的作答人數不多,但不同少數民族個體的具體選擇也有較大的差異。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大學生在語言交流和學習應用中更多地受到語言的影響,分別占18.7%和16.8%,這是由于在語言的學習使用上,個體更多地受到本民族語言的影響。在對少數民族個體的訪談中,也有很多個體表示,語言運用的能力給他們的學習和生活交流帶來了很大的障礙。
受訪者SLY(女):我們都是從新疆考過來的,我的國家通用語不好……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學得是維語,我習慣了用維語來思考,然后再翻譯成國家通用語,每次都是這樣的,所以每次都要經歷這個過程。(2017 年11 月19 日)
這種情況多發生在中小學學習經歷是民語言班級或雙語班的學生身上。
通過對高中班級性質與交往互動適應壓力、文化適應壓力以及環境適應壓力進行Pearson 卡方檢驗發現,P 值都小于0.05,對稱度量φ 值都大于0.1,說明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的適應狀況受其高中所在教育經歷的影響較大。
在研究中也發現一些個體過多地依賴本民族的圈子,從而導致個體對國家通用語言的掌握和使用能力下降,進而影響到個體適應大學學習和生活的現象。除此之外,在對家庭所在地類型與適應壓力的交叉分析中發現,原生家庭所在地因素也會在個體進入內地后的人際交往、文化交流以及外部環境適應中產生顯著的影響。見表6。

表6 家庭所在地類型與適應壓力交叉分析
在面對適應中所遇到的困難時,來自農牧區的少數民族青年大學生感到的壓力要比來自農村的大,而城市尤其是省級城市的個體所遇到的文化適應壓力又比來自農村的個體要小。本研究在對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的深度訪談中也獲得了相關的內容。
受訪者ARF (男):這個是我到內地以后才發現,他們不管是在學習語言方面,接受新知識方面,還是學習能力方面都比南疆的孩子要好,能很好地接受或者是學習新技能。
受訪者WRS(男):南疆的父母思想比較傳統一點……他們沒有機會接觸新的思想……比如烏魯木齊的家長很早就把孩子送到補習班學習英語,南疆那邊就沒有那些,連國家通用語都說不好更不要說去學英語了。現在還好一點,以前是九年義務教育,必須上完初中,好多孩子上完初中父母就不讓上了,現在這種情況好多了。(2018 年1 月10 日)
由于歷史地理原因造成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新疆南北疆以及城鄉社會經濟狀況差別較大。反映在教育方面,就出現了南疆農村少數民族學生受教育水平相對較差,在語言掌握運用以及接受新知識方面的能力都較北疆和城市的青少年薄弱的狀況。同時,受到傳統的封閉思想觀念的影響,普通民眾的思想文化水平也都較低,對孩子接受教育以及對受教育程度的認識都較為欠缺。因此,家庭因素在社會結構性因素的作用下,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教育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力。
四、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本研究的數據分析也發現,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的適應與大學生們所獲得的同胞支持網絡相關度并不大(見表7)。這與以往的一些文化適應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即同胞社會支持網絡“可以給個體提供信息、情感和有形的以及智力性的幫助”[5]的結論不同。這可能因為同胞支持網絡在互動溝通、環境適應以及文化知識獲得方面對個體所能提供的幫助并不多,反而會對適應起到一些不利影響。如,過多地與本民族成員待在一起常常會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交流,會減少甚至是削弱對國家通用語言的使用,進而導致語言能力降低,反而不利于個體的文化適應。[6]在對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適應壓力選項的作答統計中也發現,少數民族大學生中“取得滿意的學業成績”“適應大學的學習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多的適應困難。

表7 人際交往與適應壓力相關性分析
(二)結論
1.總體適應狀況良好
在對適應個體的問卷統計后發現,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總體適應狀況良好。比較突出的問題體現在對內地的環境(包括:氣候環境、教育學習環境)以及文化認知的適應上。絕大多數個體都能夠在一段時間后基本適應內地的學習和生活,融入到內地的同學當中。少數民族大學生個體基本都會經歷奧博格(Oberg,1964)在其“文化休克”理論中所論述到的文化適應四階的時間周期,即蜜月期、挫折期、恢復期和適應期。隨著在內地的時間長度增加,與內地同學朋友的交往深入,個體對自己所在環境越來越熟悉,周圍的人際交往越來越順暢,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也不斷地增加,文化適應個體會逐漸從最早的“文化休克”轉向“恢復期”進而達到“文化適應”狀態,完成一個適應周期。
2.適應過程中存在“挫折期”
大多數少數民族個體在經歷整個適應周期完成適應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經歷適應中的困惑期,即所謂的“挫折期”。這些影響適應的因素有:個體的性別因素、教育經歷、來內地時長、家庭因素、語言應用水平、社會支持網絡等因素。其中,國家通用語言掌握水平往往會受到教育經歷的影響,同時,家庭所在地的經濟和教育水平又深深地影響著個體在內地的學習狀況,而個體在內地所感受到的適應壓力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不能適應內地的學習環境。面臨較大的學習壓力,使得個體無法獲得自己以及他人所期望的學習成績,從而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自卑和內疚感同時存在于他們在內地的適應生活中。
3.文化認知失調導致適應壓力的產生
產生適應壓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來自少數民族個體與內地大學生以及本地人之間的文化認知失調。在對個體進行適應中的人際交往互動障礙測量時,個體自測中共同認可的一點便是交往雙方沒有“共同的生活經歷”。由于交往雙方對各自生長環境的了解非常少,生活經驗的感知差異過大,使得文化交往雙方無法很好地理解彼此,甚至產生誤解。所以,良好的人際交往互動會促進個體很好地適應內地的學習生活。這在對個體人際交往對象與文化適應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中也反映出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交往的漢族同學以及其他民族同學越多,其在內地的文化適應中所感知到的適應壓力就越小,適應就越好。見表7。
4.多種因素影響到文化適應
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文化適應的狀況與其教育經歷、家庭狀況、國家通用語言掌握狀況以及在內地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網絡狀況密切相關。對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的結果都顯示出個體的人際交往圈子與其文化適應壓力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如表7 所示,當少數民族大學生個體與內地漢族同學交往人數較多時,其在適應時所遇到的交往互動壓力、文化認知壓力以及環境適應壓力都顯著較少。另外,個體交往的少數民族同學數量較多時,也會在減少交往互動壓力上起到顯著作用。
五、建 議
鑒于以上內容的分析,建議相關的高校管理部門,應在促進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與內地其他各民族學生交往交流的機會方面加強管理;有關教育部門采取措施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加強基層教師隊伍建設,以便從根本上促進解決其適應中的問題。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
(一)促進各民族間相互交流溝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根據調研發現,與內地學生有廣泛而深入交往的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所面臨的語言困難、交流障礙都較少;而長期與同民族個體在一起的少數民族大學生,常常會出現人際交往范圍較為封閉,國家通用語言的使用水平受到影響的情況。以往的研究也發現,過分強調對本民族認同則會弱化個體對其他文化的認同和吸收。各個民族都是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與交融過程中得到發展的。我國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重要途徑。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相互影響、相互吸收、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有機的文化整體。[8]因此,推行少數民族學生與內地各民族學生的混合住宿,加強內地各民族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的交往交流,有助于增進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對內地社會文化的認同,適應內地的社會生活,進而加強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提高大學生媒介素養,發揮新媒體的傳播效果
隨著網絡媒介的發展以及社交媒體的應用,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也非常多地參與到網絡媒介信息的使用和生產中。在訪談中,大多數從內地高中班升入大學的少數民族大學生表示,很多網絡媒介應用是他們進入高校后才接觸到的。因為有一部分學生是在進入大學后才有機會使用手機上網的,所以通過網絡應用滿足適應中的一些生活需要,以及通過網絡建構的社會網絡都要比一般的大學生更晚一些、更加被動一些。如很多受訪者表示自己在內高班時校方不容許使用手機,也有一部分學生受到家庭經濟狀況和出生地的環境影響沒有條件獲得使用網絡的機會,因此,很多人“不會玩網上的很多應用”,包括同齡人愛玩的網絡游戲他們也不知道怎么玩,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數字溝,在與同學舍友交際時他們在交談內容上顯得格格不入。當他們進入大學有機會使用這些工具上網沖浪時,又會在如何選擇、理解、判斷、使用以及傳播那些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新疆少數民族學生在內地文化適應過程中也存在媒介接觸使用上的數字鴻溝。如何縮減數字鴻溝,提高少數民族大學生媒介素養勢在必行。
建議一些相關的機構、媒體、學校發揮新媒體的優勢,建設一些社交媒體公眾號,創作一些以展現各民族優秀文化為內容的形式活潑的文章、短視頻等媒體產品,進行傳播交流,打開各民族學生相互了解和欣賞的通道。同時,還可以在各地內高班以及相關高校開設一些人文和媒介素養教育的課程,以便提高這些大學生們的媒介使用能力和信息鑒別能力,而不是僅僅以培養學習成績合格的少數民族畢業生為目的。這樣才更能讓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融入內地多元豐富的多民族文化之中。
在本研究中還發現,在新媒介使用過程中,許多少數民族大學生非常喜歡看網劇,一些個體還會關注本民族精英人士微博、公眾號以及他們參與的節目等。同族的精英、明星令他們感到親切和自豪,平時有同族成員的網絡信息,一般都會得到很大的關注。如在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問卷調查中顯示,其使用網絡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休閑娛樂,在網上看視頻和下載音樂,大多數人還是喜歡觀看少數民族語言的節目和有本民族成員參與的節目內容。因此,針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平時的媒介使用偏好,老師、輔導員等可以鼓勵學生參與到新媒體內容的生產和傳播中來,在傳承和傳播好本民族的優秀文化的同時,將內地更加多元的、先進的現代文化通過新媒體傳播給家鄉的親朋好友,發揮文化傳播交流橋梁的作用。
(三)加強內地高校新疆籍輔導員的管理隊伍建設
鑒于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生活和成長的特殊經歷,對他們的教育管理工作應該由一些既懂教育規律,又了解新疆少數民族文化生活習慣的輔導員、老師來擔任。因此,內地有條件的大中專院校應聘用一些政治思想過硬,同時又對新疆各民族學生風俗習慣比較了解,善于與學生溝通,具有服務精神的優秀的專職輔導員進行相關的學生服務管理工作,這樣有利于解決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所遇到的文化適應困難,引導他們積極主動地了解當地的社會文化,參與到當地的社會生活實踐中。
(四)進一步提高少數民族大學生在中小學基礎教育層面的教育水平
除了加大對國家通用語的訓練,加強基礎教育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教學質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國家為解決邊遠貧困地區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每年都會從新疆各地招收一批學習成績優秀的中小學生進入內高班和內初班學習。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從新疆各地貧困的農村、山區選拔上來的“尖子生”。在國家政策照顧之下他們獲得了進入擁有優質教育資源的中學、大學學習的機會。但當這些學生進入內地學校學習時,他們普遍反映學習非常吃力,上課很難跟上老師的進度,感覺難以達到與內地同學齡的個體相同的水平。這種情況下,他們總是感到精神壓力、學習壓力較大,與自己期待的學習成績相去甚遠。一些個體出現了沮喪、自卑甚至逃避的心理,非常不利于個體的發展。但由于其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存在學習基礎薄弱、學習能力培養上的缺陷,很難在短時間內補上學習的短板,跟上內地學生的學習成績。即便是一些個體達到內地學生的平均水平,也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因此,提高基礎教育水平,提高新疆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成績,能夠減少個體在內地適應時的學業方面的壓力,消除自卑心理,獲得自信,進而有助于增加其在內地的文化適應能力。